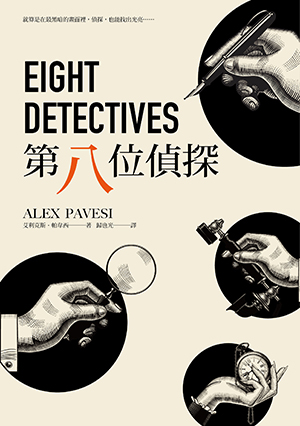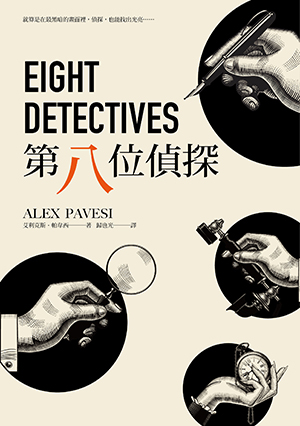內容試閱
她坐下。「聽著,我會幫你脫身,亨利。不難想像你一定有什麼合理的理由殺他。我們都知道,邦尼可以很殘酷,而且魯莽。搞不好最後我甚至能夠原諒你,但如果你想要我為你說謊,你就不該測試我的耐性。為什麼是現在?為什麼用這種手法?」
「梅根,這太瘋狂了。」亨利閉上眼。所有門窗皆被關上,這熱度令人難以忍受。他覺得他們像兩個懸浮在油中的樣本,有人正研究著他們。
「所以你還是堅持你是無辜的囉?天啊,我們已經走過一輪了,亨利,你努力過,但排在走廊的十二盆植物陪審團已判定你有罪。你從頭到尾都在這,你還有什麼好說的?」
他把頭埋入雙掌中。「再讓我想想。」他複習著她的指控,嘴脣無聲蠕動。「快被妳煩死了。」他突兀地伸手從旁邊的地上拿起吉他,撥動剩下的五根弦。「會不會我們吃完午餐回來時他們就躲在樓上了?」他的額頭滿是汗水。「除非是就在我們回來的那個當下,否則他們沒有機會離開。事實上、事實上,我想我找到答案了。」
他又起身。「我想我知道發生什麼事了,梅根。」
她朝他仰起頭──一個表示鼓勵的倒轉點頭。
「梅根,妳這小蜘蛛、妳這不懷好意的蛇。是妳殺死了他。」
梅根看起來完全不為所動。「別傻了。」
「看得出來妳經過一番思考。我們來了,具有相同機會、動機也廣泛得足以涵蓋雙方的兩名嫌疑犯,所以妳只要否認一切,罪責就會歸咎於我。問題的癥結就在於我們之中誰比較會演戲,而我們都知道答案是什麼。」
「如我方才所指出,亨利,你整個下午都坐在這裡看守你的殺戮,所以我怎樣才下得了手?」
「妳只要否認一切,講到喉嚨乾掉就好,沒必要陷害我、假造證據。妳從頭到尾就是打這如意算盤,對吧?警察來了後會發現這裡有兩個外國人跟一具屍體,其中之一是我,既挫敗又講不清楚,試圖主張可能有人頭下腳上爬過天花板以在不被發現的情況下上樓。另一個則是妳,完美自制,否認一切──一朵英國玫瑰奮起對抗粗野男子。我們都知道他們會相信誰,而我還能怎麼說服他們?我在這天殺的國家裡甚至點不了一杯咖啡。」
「這是你的理論,是吧?那我怎麼從你旁邊溜過去,亨利?像你說的在天花板爬行嗎?還是你在剛剛這二十秒內又想出了什麼更具說服力的說法?」
「我沒必要。這問題不對。」他起身走到窗戶旁,這會兒不怕她了。「頂樓確實牢牢上鎖,只能從樓梯出入,也確實我自從午餐後,也自從邦尼上去他房間後整個下午都坐在這,連廁所都沒去上。不過也確實我們剛回來時我走得又熱又一身髒,曾經去梳洗一番。我留下妳獨自在這,就是這裡。我回來時妳不曾移動。我清洗臉、脖子和雙手花了九到十分鐘,這時間太短暫,我幾乎完全忘記。但話說回來,把小刀捅進某人背上要花多長時間?」
「那是幾小時前的事了。」
「三小時前。那妳覺得他死了多久?血都流到整條走廊了。」
「那時候我們才剛進屋,他剛上樓,甚至還沒睡著吧。」
「對,但他很醉,睡不睡根本沒差。他一趴上床就完全無法防備了。」
「所以就這樣,是吧?你指控我謀殺他?」
亨利微笑,為自己的邏輯感到驕傲。「沒錯,我就是。」
「你這可悲、幸災樂禍的傻瓜。他死了,而你想拿來當遊戲?我知道是你幹的,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我也可以問妳相同問題。」
梅根停下,把整件事想過一遍,拿刀的手放鬆了。亨利眺望窗外,透過髒玻璃看見泛著光暈的山丘。他正以他的無畏嘲弄她,這是一種主張他權威的方式。
「我懂你在做什麼了,我現在看得一清二楚。這事關名聲,對吧?我是演員,像這樣的醜聞會毀掉我。就算只是再雞毛蒜皮的懷疑,我的名聲都將破滅。你覺得我的損失會比你大,所以不得不配合?」
他旋過身,被身後的明亮日光晒紅。「妳以為跟妳的職業名聲有關?並不是什麼都跟妳的演藝生涯有關好嗎,梅根。」
她咬住下脣。「不,我也不覺得你會承認,對吧。你首先讓我見識你可以多頑強,然後呢?當你讓我相信我贏不了、我如果不配合就會毀掉我的演藝生涯後,你再提出你的計畫。你會想出某種故事再要求我替你佐證。如果真是這樣,你還是直接跟我說實話比較明智。」
他嘆氣,搖了搖頭。「真不知道妳為什麼一直說這些。跟妳解釋過這場犯罪的各種情況了,但就算是最棒的偵探,面對徹底否認也沒轍。我煩得都快扯光我的頭髮了,事情就是這樣了,不過我不覺得光頭適合我。」
她盯著他。大約有一分鐘的時間兩人都不發一語。最後她終於把刀放在身旁的桌上,刀尖轉到一旁不再對準他。
「好吧。拿起你的吉他接著彈吧。我指控你,你也指控我,顯然我們就是置身這種處境。但如果你以為我是那種會屈服、只因為一個男人說天空是綠色就被說服的女人,那你可是低估我了。」
「如果妳以為妳只要站穩立場、搧搧睫毛,我就會像隻鳥兒般唱歌,妳才是高估了妳自己的魅力。」
「噢,」梅根眨眼,「但我以為你還愛我?」
亨利在她對面的椅子坐下。「我是,所以這才如此令人瘋狂。只要妳承認是妳殺的,我不管如何都會原諒妳。」
「那我們來談談以前沒談過的事。」她又拿起小刀,而他眼中閃過一絲真實的恐懼。「你擁有狂暴的一面,亨利。我看過你喝醉,也看過你只是不喜歡陌生人看我的方式就跟他們打起來,還看過你呼喊、尖叫、砸玻璃。這些你也一概否認嗎?」
他注視地板。「不,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你有見過我那樣嗎?」
「或許沒有,但妳也可以很殘酷。」
「尖牙利嘴殺不了人的。」
他聳肩。「所以我脾氣暴躁。這是妳不想嫁給我的原因嗎?」
「不盡然,但也不算加分就是了。」
「我那時喝了很多酒。」
「你午餐時也喝了很多。」
「不多。沒以前多。」
「顯然夠多了。」
亨利嘆氣。「如果我想殺邦尼,我會用更好的方法。」
「亨利,我知道是你,我們都知道。你到底想說服我相信什麼?我發瘋了?」
「我也可以說一樣的話,不是嗎?」
「不,你不能。」她揮刀刺入她的椅子扶手,刀刺穿墊襯卡在木頭裡。「邦尼在樓上像個水龍頭般滴滴答答,我們卻只是在這裡吵架。要是警察發現我們整個下午在做什麼,他們會怎麼想?」
「真是場惡夢。」
梅根翻白眼。「另一個爛譬喻。」
「好吧,如果我們要這樣度過這下午,那我想要手上有杯酒。想加入嗎?」
「你有病。」
他幫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
半小時過去,什麼也沒改變,他們反覆著這個情況數次,每次都沒有結果。
亨利喝完酒,把空杯捧在眼前,透過酒杯凝視變形、空洞的起居室,手一面左右移動。梅根看著他,不知道他的注意力怎麼會這麼容易分散。
亨利回頭看她。「我要再來一杯然後就結束,妳想加入嗎?」
門窗依然緊閉,起居室內令人窒息,彷彿是一項他們彼此都同意的自我懲罰。
她點頭。「我跟你喝一杯。」
他哼了一聲,走到酒櫃旁,從威士忌長頸瓶倒出兩大杯酒。當然了,酒是溫的。他一手拿起一杯,有節奏地旋了旋,將另一杯遞給她。她看見這分量瞪大了眼,三分之二滿。「最後一杯酒。」他說。
「如果我們都沒有要認罪,」梅根說,「我們應該要討論一下接下來該做什麼。是不是根本沒必要牽扯上警察?沒人知道我們在這,或許我們乾脆趁夜離開就好。」
亨利靜靜啜飲他的酒。他們就這樣在那兒坐了幾分鐘。梅根一手掩著她的杯子,終於舉到嘴邊時,她在酒杯碰到嘴脣前停住。「我怎麼知道你有沒有下毒?」
「我們可以交換。」
她聳肩。這段對話似乎並不值得接續下去。她啜了一小口,「味道不錯。」而他只是用一種令她不安的方式靜靜注視著她。「換個角度來說,為了避免疑慮。」他嘆氣,將自己的酒杯交給她;她接下,也把自己的酒杯給他。
他氣力用盡地坐回椅子上,舉杯。「敬邦尼。」
「敬邦尼。」
威士忌如即將到來的落日那樣橘紅熱烈。亨利又拿起吉他,重新彈起先前那個笨拙的調子。「我們回到起點了。」他嘆氣。
「如我所說,我們需要討論接下來該怎麼辦。」
「妳要我說我們可以就這樣逃跑,假裝自己沒來過?跟上次一樣。那自始至終就是妳的計畫,對吧?」
「你為什麼要這樣對我?」梅根放下酒杯,搖了搖頭。「是因為我取消我們的訂婚嗎?但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啜飲酒漿已成為亨利用來拖延對話的主要手段,然而面對這個問題,他卻認真相對,並點燃一根菸。「那我就再說一次吧,梅根,我還愛妳。」
「很高興知道你還愛我。」她期待地看著他。「你開始覺得頭暈了嗎,亨利?」
剛開始他困惑不解,接著瞥了一眼他的酒杯。他已幾乎喝乾,只剩下最後半吋高度。他伸手想要拿杯子,卻發現左臂幾乎麻痺,姿態詭異又笨拙的手將杯子打落地面,酒杯隨即破碎,在白地磚留下一個棕色圓圈。「妳做了什麼?」
菸從他口中掉落,墜入吉他琴身內,一縷盤繞的煙從琴弦間裊裊上升。她的臉除了些微擔心外不露情感。
「梅根。」
他往前滾下椅子,半邊身體麻痺,吉他彈到一旁。他俯臥白地板,毫無節奏地顫抖,唾液在他下巴前方的地磚上聚積。
「說謊是這樣的,亨利。」她起身聳立他身旁。「一旦開始就無法停止,無論謊言帶你到哪,你都只能跟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