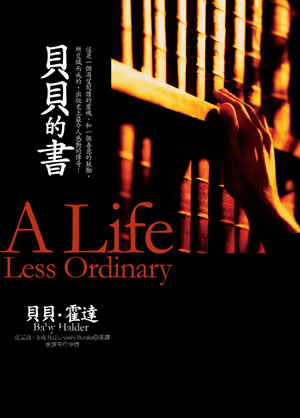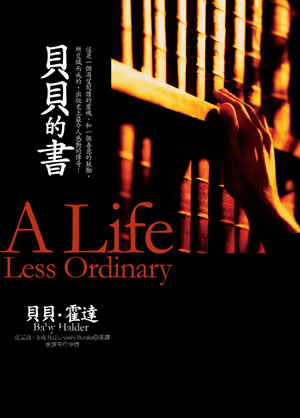內容試閱
當卜拉波德庫瑪,退休的人類學教授、也是文學家卜雷姆羌德的孫子,發現他家裡新來的幫傭心事重重,於是他提供了世上最古老的一種療法:他要求她說一個故事。她總是靜靜的做著她的工作──煮飯洗衣打掃拖地──然後回去做飯給她的三個孩子吃。
說故事對二十九歲的她來說並不困難。有一段時間,還是小孩子的時候,貝貝‧霍達躺在她表妹身邊,一連好幾個晚上,像希拉左德〈註:天方夜譚中說了一千零一夜故事的蘇丹新娘。〉那樣,連續的說著她聽來的一個故事。同樣的,她也有說不完的故事。舉個例子,每次當她撥弄著她四歲那年,母親出走前塞進她手掌心裡的那十派薩〈註:印度錢幣單位,一盧比等於一百派薩。〉時,關於母親和小弟忽然消失不見的那些事情便湧上心頭。或者是他們在喀什米爾的生活,她父親在那裡當過好幾年的兵。甚至讀著歷史課本也會浮現出一個腰上綁著小嬰兒,不向命運低頭,邁力走出人生的母親,就像尚錫的拉妮。〈註:rani of jhansi印度的民族女英雄,王侯尚錫的遺孀,rani即王妃。〉
然而卜拉波德給她的筆記簿和筆卻帶著一份莫名的恐怖。對貝貝霍達來說,就跟最早期的那些男男女女一樣,故事是一些你可以自由交換的東西,而且多半是在睡覺前說的──都是一些狡詐的或者是頭腦簡單的動物,輸家和贏家,國王和王后,安全無慮的遠離內在和外在的混亂,脫離開生活中許多的矛盾和模糊地帶,得到一種不可言喻的淨化。可是她雇主的提議非常不同:『把妳的人生寫出來。』他說。要寫出她的人生!
要用什麼來談她的存在,沒有意思的無聊的存在,有著很多的暴力欺凌,那樣的無趣單調,不時的因為絕望到了頂點而奮起的存在?她父親,一名退休的技工兼司機,帶她從喀什米爾到摩悉達巴到度加波。一個沒有母親的孩子,毫無疑異的忍受著暴虐成性的父親和後母,再加上一個大她十四歲、完全不在乎她的丈夫,這樣生活到了有一天,她帶著三個孩子搭上一班開往人生地不熟的德里的火車。在德里,她的作為就像那些為了逃避貧窮和酗酒男人的婦女一樣:她接下薪水很差的幫傭工作,有時跟孩子們在冰凍的寒夜裡露宿街頭。貝貝以她一貫逆來順受的習慣接下了她雇主交代的這份『任務』,前面幾頁寫得好辛苦,彷彿當它是忙碌的一天中多出來的一件差事。說起來真的很難為情。不寫筆記簿已經將近二十年,她都忘了那些字的拼法了。更糟的是,她的孩子搞不懂為什麼寫筆記簿的是她──而不是他們。可是最後證明卜拉波德是對的。這些字開始發揮了它們的魔力。
一生與文字為伴,工作閒暇都少不了它,卜拉波德當然知道它的價值。事實上,就在他第一次發現她替那些書撣灰塵的時候,兩手的動作變得出奇的緩慢,他當下就決定要讓她使用那間書房了。她從書架上取下的第一本書是泰思莉瑪‧納斯林的《我的少女時代》。那感覺就像是在讀她自己的人生。書裡寫的是一個作者的憤怒,在貧窮社會中生為一個女人的屈辱。所有被壓抑的、因此而迫使貝貝爬上火車來到一個陌生目的地的種種情緒,突然之間都有了一種全新的意義。
在工作的空檔和安頓孩子們就寢之後的深夜裡,她都手不釋卷的讀著。其他的書一本一本的緊接在後面:阿夏普娜戴維、馬哈斯威塔戴維和菩達代古哈的小說。這些書使得貝貝從呆滯的冬眠中驚醒,但是單單靠閱讀不夠刺激她開始寫作。如果從一九六○年代中期才浸淫在寫作中的卜拉波德,和他另外兩位朋友──阿修塞克撒利亞與拉密須戈司瓦米──沒有催促她,貝貝永遠都不會發現她會成為一個作家。
《貝貝的書》是一本輕薄短小的書,由貝貝孩提時候開始到她十二歲又十一個月結婚為止;從流亡邁入成年以後的生活,為了對付一個既不體貼又不識字的丈夫和幾乎是獨力撫養三個孩子的壓力,她吃盡了苦頭,直到登上開往德里附近發里達巴的火車;最後是描述她如何努力討生活,以及她作家天分的意外發現。
這是一本很有趣的書,多半以第一人稱來寫,卻常常在最關鍵的時刻轉成了第三人稱,彷彿她在本覺上意識到,要適切的傳達這些情緒爆點,唯一的方法就是遠離自己的旁白。這都要歸功於卜拉波德〈他把原來孟加拉文的草稿翻譯成北印度文〉,他選擇不加任何潤飾,只是把一些亂了次序的時間做了些許調整,其餘都由貝貝以她最原來的聲音娓娓道來。貝貝這本回憶錄最引人注意的一點就是她的自我描繪:在這本頁數不多的書裡看到了她驚人的改變,從一個不更事,處處被動,心甘情願的屈服在生活當中的女人,變成一個能夠把生命中所有壓抑痛苦的回憶生動記載下來的作家。
這份回憶錄以一種平常老套的方式展開,貝貝跟著家人住在亞穆、喀什米爾和答爾豪塞,她父親是職業軍人。她簡單的描述著雪景、鮮花,甚至山間的彩虹。但是從一開始就很明顯的看出,這不是一個談美麗的花朵和彩虹的傳統小女孩,而是一個有著現實的成人心境的成人聲音。受盡凌虐的她,以平淡冷漠的態度敘述家人所面對的苦難,他們搬到摩悉達巴去投靠父親,後來卻遭他遺棄任由他們自生自滅。四歲的貝貝什麼也想不起,成年的貝貝用孩子的率直把他們的生存方式赤裸裸的寫出來:她母親情急的想要賺錢養家,而自尊又使她羞於出去找工作或是倚賴親友們的救濟,她把挫折感全部發洩在孩子們的身上;偶爾虛應一下故事就走的父親,最後在長輩的壓力之下放棄工作回來了。一個回了家成天繃著臉的男人,一個孩子們避之唯恐不及的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