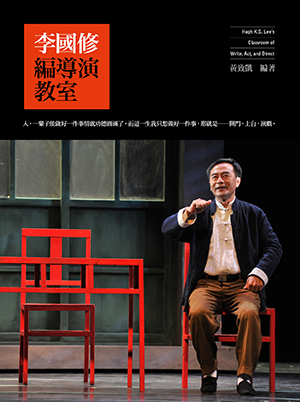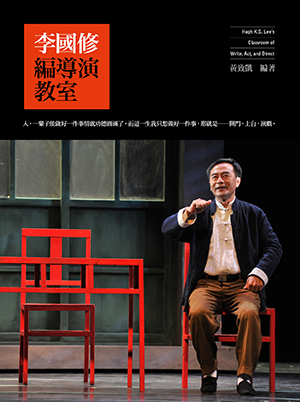內容試閱
【編者序】
把你訓練成我的對手
黃致凱
「我要把你訓練成我的對手,在劇場的擂台上較勁。」國修老師對每個課堂上的學生都這麼說。
2002年,還在就讀臺大戲劇系三年級的我,對畢業後的出路感到徬徨,因為我是第一屆的學生,毫無學長姊的前例可循。
就在大三下學期,國修老師受系主任彭鏡禧之邀,來臺大開了「導演實務」的選修課程。想修那門課不是在網路選課系統用滑鼠點一點就好了,他的要求如下:繳交自傳一千五百字、過去作品DVD、未來導演學習計畫一千字、現場呈現十分鐘戲劇片段、口試──由於門檻嚴苛,近乎研究所入學推甄的標準,最後只有七個人來報名,他硬生生只錄取了三個,我是其中之一。
那學期的課程讓對未來茫然的我大開眼界,與其說國修老師像是大海中的一根漂流木,我更覺得他像是一艘準備遠航的大輪船,順手把我撈上甲板──國修老師對劇場的熱情會把人燙傷,從他的身上我感受到,原來劇場不只可以是一份職業,還可以是一份志業。
學期結束後,修師說:「你如果還想學,就來屏風吧!」那年的暑假,我成為了屏風的見習生。我坐在排練場最角落的位置,每天除了掃地、拖地、倒煙灰缸之外,就是「看」。我看著導演和演員透過排練把角色的形狀雕塑出來;我參加所有的設計與技術會議,了解場景調度的原理。在整整看了一年兩齣戲製作之後,我才有資格當助理。或許是這份熱情與傻勁打動了他,2005年我正式磕頭拜師,成為入門弟子。
劇場界都知道國修老師是編、導、演三絕,但他除了創作之外,在戲劇教育上,可說是提攜後進,不遺餘力。除了屏風內部的演員訓練,我跟著他在北藝大戲劇研究所、臺大戲劇系、靜宜中文系、臺南大學戲劇創作與運用學系……等校系開設專業課程,陪著他走南闖北,貼身學習他的思想。他是一位胸襟開闊的藝術家,熱於分享他的創作經驗,他從不留一手,學生隨便問一個問題,他就可以回答兩個小時。
修師常說,他對人生有三個重要信念:「一求溫飽、二求安定、三求傳承」。他對我的要求極其嚴苛,跟隨在他身邊十一年,他從來沒有稱讚過我一句,準確地說是「一個字也沒有過」,因為他做京劇戲鞋父親從沒稱讚過他,「你做好是你應該的。」國修老師用他父親的教育理念來訓誨我、提點我,指正我,他說:「你錯了就是對了,因為創作和人生一樣,錯中學,做中學」。2010年我以魯凱族巴冷公主傳說為主題,編導了臺北市花博的開幕典禮指定演出《百合戀》,並創下連演一百九十六場的空前紀錄。最終場演出時,國修老師坐在我身旁,他沒有向我祝賀,而是一如往常的跟我分析:「你舞台構圖的能力還是不足,右舞台的山洞應該還要再高一點,劇場整體視覺才會有高低的層次……」我何其有幸遇到了一位嚴師,演出到了最後一場,他還在給我筆記。我慢慢從國修老師嚴謹的劇場教育與生活教育中去感受到某種被父親管教、被父親影響的感覺。我終於理解過去中國人為什麼要叫「老師」作「師父」,因為老師就是另一個父親。
國修老師在多年前,早有將他的教學講義出版的念頭,但因自身要兼顧創作與劇團經營,一路延宕至今。去年三月我和毓棠師姊協力完成《李國修戲劇作品集》的出版後,修師便要求我著手整理他的創作思想,並指示我以第一人稱來撰寫,盡可能地還原他的口吻,與課堂上所表述的戲劇觀念,於是我便戰戰兢兢地開始進行這多達十八萬字的龐大寫作計畫。
《李國修編導演教室》有別於一般的戲劇理論,書中提出的創作觀念,都是經過作品不斷地實踐,從失敗的經驗中檢討,慢慢累積形成的論述,因此這本書可說是一本劇場實戰的寶典。我盡可能地把修師的創作旅程、作品範例、生活小故事等,作為講義的內容佐證,務必使修師的創作思想能清楚的傳達。
2013年6月19日,我打給老師:「楔子和表演課的前兩堂,我寫好了,你要不要看一下?」「你印出來拿到醫院給我。」老師平靜地說,我當下直覺不妙,連夜沒睡,又趕了一萬多字,就為了能讓他多看一些。翌日,我下臺中去醫院探視他,打開房門時,他立即精神炯炯地從床上坐起,要我把這本書已經完成的篇章一字一句讀給他聽,然後他一如往常的告訴我文章結構哪裡有問題,哪裡需要補充作品的範例,他生龍活虎的樣貌,讓我數度彷彿置身在排練場或課堂。
國修老師曾說:「我願意死在舞台上。」我眼中的他,是真真切切地在體現對戲劇的熱愛。這本書是他從事劇場近四十年的心血結晶,從不藏私的他一直希望透過思想的傳遞,可以有步驟、有技巧地讓創作者學習掌握編、導、演的技巧,把每一個劇場後進,訓練成他的對手,在擂台上互相較勁,為這片土地說出更多動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