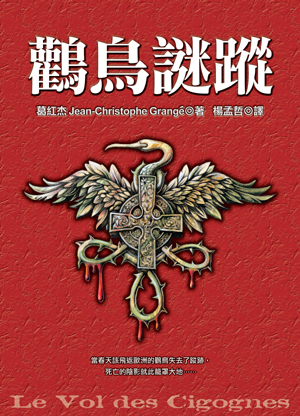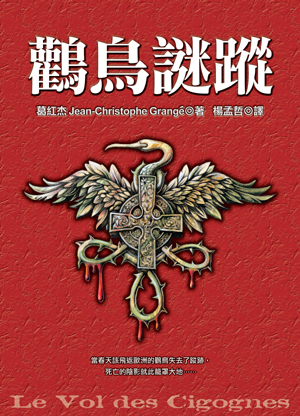內容試閱
外面的拂曉投射出金屬般的陰影,並以灰色的光芒照亮沉睡中的街道。
我並未遵守交通號誌地穿越蒙特市,驅車直接前往波姆的家。不知道為什麼,一想到對這位鳥類學家展開調查這件事,我就感到相當害怕。我打算消毀和我相關的所有文件,並以匿名的方式,把錢退還給APCE,而不要把警方牽扯到這件事情裡面。不留痕跡,就沒有煩惱。
我低調地把車子停在距離木屋一百公尺遠的地方。我首先確認了房子的大門並沒有上閂,然後回到車子裡,找出一張軟塑膠分類書卡。我把書卡插到門片和門框之間,撥了撥門鎖,試著把塑膠片塞到卡榫下面。最後,我利用肩膀的力量,沒有發出任何聲音地把門推開。我闖進了已故的波姆先生家裡。在一片昏暗當中,房子裡面看起來十分簡陋,而且更為封閉。這裡已經成了一棟死人的房子。
我走到位於地下室的辦公室,毫無困難就找到擺在顯眼處,標示著『路易‧安提尤斯』的檔案。檔案裡面夾著銀行匯款的收據、機票的帳單、租賃的合約。我也看到了波姆根據奈莉‧布雷斯勒的談話,針對我這個人所做的筆記:
『路易‧安提尤斯,三十二歲,十歲那一年被布雷斯勒夫婦收養。聰明、傑出、敏感,但是懶散、缺乏夢想。小心任用。擺脫不掉那一場意外留下的創傷。局部記憶缺失。』
所以,對布雷斯勒夫婦來說,經過了這麼多年,我仍然是一個有問題的案例──精神狀況不穩定。我翻過那一頁,後面已經沒有其他的文件。奈莉並沒有提到任何關於我那一場悲劇的詳情。也好。我拿了這份文件,然後繼續翻尋。我在抽屜裡挖出了『鸛鳥』的文件。和馬克斯在第一天為我準備的那一份很相似,裡面包括了聯絡人和各種資訊。我全部一起帶走。
是該離去的時候了。然而,受到某種難以解釋的好奇心驅使,我繼續漫無目的四處翻尋。在一個大約和人一樣高的鐵櫃上面,我發現了上千份關於鳥類研究的檔案。緊緊豎立排在一起的文件,呈現出各種不同的顏色。波姆曾跟我解釋過各種顏色的意義,每個事件、每樣資訊都有特別的顏色──紅色:雌性,藍色:雄性,綠色:候鳥,粉紅色:觸電意外,黃色:疾病,黑色:死亡……所以波姆只要朝文件堆看一眼,就可以依據研究的主題,找到相關的檔案。
我突然出現一個念頭:我查閱了失蹤的鸛鳥名單,然後在抽屜裡找出其中幾份檔案。波姆使用的是一種難以理解的編碼用語。我只發現一件事:失蹤的全都是年齡超過七歲的成鳥。我拿走這些檔案,開始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竊賊,而一股難以拒絕的衝動,讓我繼續徹底地在辦公室裡翻箱倒篋。我現在尋找的是一份病歷資料。『波姆是由行家動的刀』,瓦黑爾如是說。他是在什麼地方接受移植手術?是什麼人動的刀?我什麼東西都沒找到。
一無所獲的情況下,我於是著手搜尋隔壁一間陋室。這是馬克斯‧波姆自己動手焊接套環、收藏鳥類家應用工具的地方。工作檯上面擺著幾副望遠鏡、攝影濾鏡、許許多多的套環,以及其他各種器材。我還發現了一些外科手術所使用的工具:繃帶、皮下注射器、夾板,和殺菌的材料。馬克斯‧波姆生前應該也扮演過業餘獸醫的角色。在我的眼中,這個老人的世界似乎顯得越來越孤獨了,完全圍繞著一些難以理解的迷戀。最後,我把一切東西整理歸位之後,回到一樓。
我迅速穿過大廳、接客室,和廚房。除了一些瑞士傳統的小擺設、廢紙和舊報紙之外,什麼都沒有。我上樓去看房間。一共有三間。我第一次造訪留宿的那一間,一直都維持同樣的中性調子:小小的一張床、拘謹的家具。波姆的房間則散發著一股發霉和悲傷的氣味:凋零了的顏色,而家具則不知為什麼原因地堆疊在一起。我任何一個角落都不放過:衣櫥、寫字檯、五斗櫃。每一件家具裡面幾乎都空無一物。我看了看床和地毯下面、拉開壁紙的角落。什麼東西都沒有,除了幾張收在一只衣櫃下面,拍攝了一個女人的舊相片。我看了一眼,那是一名瘦小、五官模糊、輪廓看起來十分脆弱的女人,在熱帶的背景下所拍攝的相片。肯定是波姆太太。在幾張年代看起來較新近的相片上面──七○年代之後的色調──她看起來大約四十來歲。我前往最後一個房間,看到了同樣的陳舊,此外並沒有再發現其他的東西。我一邊走下狹窄的樓梯,一邊拍掉衣服沾上的灰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