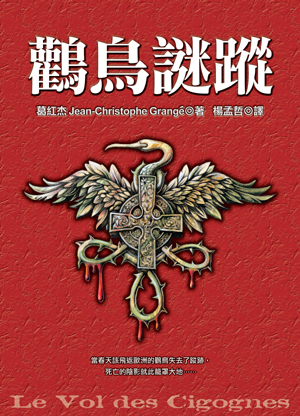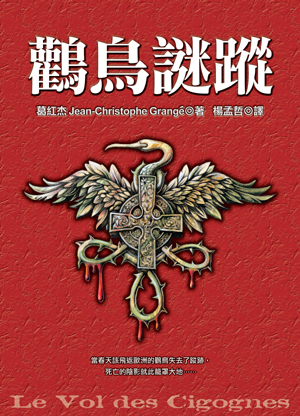內容試閱
透過窗戶,可以看到天色已經逐漸明亮。一片金黃色的光芒拂過家具和不知為了什麼原因,擺在大廳四個角落的講台。我坐在其中一只上面。這個房子裡顯然還少了許多東西:馬克斯‧波姆的病歷資料(一場移植心臟手術應該會留下許多處方箋、掃描圖、心電圖……)、旅行家的生命中常常看得到的紀念品──非洲來的小玩意兒、中東的地毯、打獵的成果……職業生涯留下的痕跡等──我甚至沒看到退休的文件,也沒有銀行的收支紀錄,或稅捐扣繳憑單。我假設波姆應該是希望和自己的過去一刀兩斷,所以才會這麼做。只是,房子應該還是有個收藏東西的地方才是。
我看了看手錶:七點十五分。如果這案子已進入司法調查程序,警方應該很快就會出現,就算他們只是來貼一張封條。我十分不情願地站起來,朝著門口走去。我拉開大門之後,突然想到那些台階。那些擺在大廳裡的講台本身就是非常理想的藏物地點。我回到大廳,敲了敲講台的側面。全部中空。我衝到地下室,在那間陋室裡找到幾件工具,然後立刻回到大廳。我花了二十分鐘,在損害最小的情況下,撬開波姆擺在客廳的七個台階。我找到三個密封、覆蓋著灰塵、沒有任何標記的牛皮紙袋。
我回到車子裡,驅車登上蒙特市上方的丘陵地,尋找一個隱密的地點。十公里之後,我轉進一條偏遠的道路,把車子停在一個仍沾滿朝露的樹林裡。我打開第一個牛皮紙袋的時候,雙手顫抖個不停。
第一個袋子裡裝的是伊涵‧波姆的病歷文件。一九四二年出生於日內瓦,原名伊涵‧佛潔,一九七七年八月因為癌細胞擴散,病逝於洛桑的貝弗醫院。文件裡面只有幾張X光片、圖表、處方箋,和一張發到馬克斯‧波姆住所的電報,裡面附有死亡證明、伊涵的主治醫師李耳波恩大夫的弔唁信。我看了信封一眼,上面寫著馬克斯‧波姆在一九七七年的地址:中非共和國,班吉市,波卡薩大街六十六號。我的心臟快速地跳動。中非共合國是波姆在非洲的最後一個地址。中非呀,這個因為出現了一位在位短暫的暴君──瘋狂的波卡薩皇帝──而可悲地舉世聞名的國家;這個酷熱、潮濕,隱藏在非洲心臟地區的鮮活叢林──一直也隱藏在我往日記憶的最深處。
我搖開車窗,呼吸著外面的空氣,然後繼續翻閱那一份資料夾。我找到其他幾張柔弱的波姆太太的相片,但是還有幾張是馬克斯‧波姆和一名大約十三歲年輕男孩的合照,而男孩的面貌和我們這位鳥類學家神似得驚人。同樣地矮胖結實、修剪成平頭的金髮、棕色的眼睛、野獸般粗壯的脖子。不過他的眼神裡散發著某種朦朧,和波姆的僵直徹底不同。這些相片明顯地攝於同一個時代──七○年代。家中成員都到齊了:父親、母親、兒子。但波姆為什麼要將這些平凡的相片藏在講台下?還有,他的兒子現在身在何方?
第二個牛皮紙袋裡面只有一張胸腔的X光片,沒有日期、沒有姓名、沒有注解。唯一能夠確定的是,昏暗的影像裡呈現的是一顆心臟。心臟中間可以看到一個明淨、微小,輪廓十分清楚的斑點。我沒有辦法分辨那是影像的瑕疵,還是心臟中間嵌了一小顆明淨的石塊。我想起馬克斯‧波姆的移植手術。這一張相片呈現的肯定是他的兩顆心臟之一。第一顆還是第二顆?我小心翼翼地將X光片收回去。
最後,我打開第三個牛皮紙袋──當場目瞪口呆地僵住了。出現在我眼前的是一幕幕最慘絕人寰的影像。黑白相片裡宛如呈現著人類屠宰場:小孩的屍體以鉤子高高掛起──木偶般一動也不動的屍塊,手臂和生殖器的部位一片血肉模糊;一張張唇部撕裂、眼眶空洞的面孔;手臂、腿腳,四散的肢體被攤在肉舖一般的檯面上。沾著斑斑暗褐血漬的頭顱滾動在長桌上,用他們的眼睛盯著你看。所有的屍體,沒有一具例外,全部都是黑種人。
這個令人作嘔的地方並不是一個單純的屍窟,因為四周的牆上鋪了類似診所或太平間一樣的白色磁磚,閃亮的外科手術器材也處處可見。看起來倒像是一個毫無人性的實驗室,或人神共憤的用刑室。一個可怕魔頭進行恐怖活動的祕密巢穴。我下了車子,胸口被一種噁心的感覺壓迫。我就這樣站著,在早晨清新的空氣裡度過了漫長的幾分鐘。我不時再瞥那些相片一眼,試著進到實際的情境,習慣那些畫面,為自己勾勒出一個較清晰的輪廓。但是我辦不到。殘忍的畫面、影像的顆粒,都為這一隊屍骸大軍帶來一種虛幻的印象。什麼人會幹下這麼可怕的事?為了什麼理由?
我回到車子裡,把三個牛皮紙袋封好,並發誓短時間內不再開啟。我發動車子,淚水盈眶地駛往下面的蒙特市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