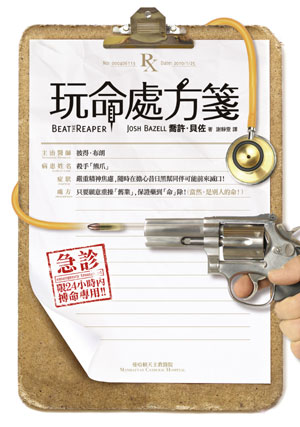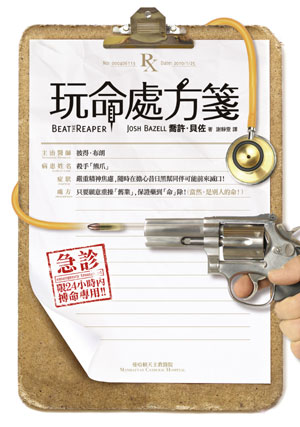內容試閱
「病房區真是個他媽的惡夢。」艾克法在我終於現身接班的時候說。他是跟我同單位的實習醫師,「病房區真是個他媽的惡夢」這句話對實習醫師來說,就等於一般民眾的「哈囉」。
艾克法是拿J-Card交換學生簽證的埃及人。J-Cards指的是外國醫學院的畢業生,他們要是沒辦法逗住院醫師主任開心,簽證就會被撤銷。另一種適合他們的稱呼就是「奴隸」。他遞給我一份目前患者的列印資料──他自己也有一份,不過他那張畫滿記號又皺巴巴的──對我從頭到尾說明一遍,像是南側的八○九號房怎樣又怎樣、大腸造口術發炎如何又如何,和有個定期來做化療的三十七歲女人的情形。這樣這樣,那樣那樣,即使你有意願聽,也不可能跟得上。
反之,我往後靠著護士站的桌子,這一來提醒我,刷手褲內袋還裝著一把手槍。
我得把槍藏起來才行,可是帶鎖儲櫃室離這裡有四層樓遠。也許我該把槍藏在護士休息室的教科書後面,不然就塞在值班室的床底下。其實放哪兒都沒關係,只要我精神夠集中,事後還記得自己擺在哪裡就好。
最後艾克法停下來,問我:「懂了吧?」
「懂了,」我說:「回家補點眠吧!」
「多謝。」艾克法說。
艾克法不會回家,也不會去補眠的。接下來,他要替我們的住院醫師主任諾登思克醫師處理保險文件,至少得花四小時。
只是「回家補點眠吧」對實習醫師來說,就等於是「再見」。
清晨五點半去巡診通常會這樣:至少會有幾個病人告訴你,要是你們這些混帳別再每四小時就把他們吵醒一次、追問他們感覺怎樣,他們就會覺得通體舒暢。其他人會把這種感受藏在心裡,轉而抱怨某某人一直偷走他們的MP3或是藥什麼的。不管怎樣,你會粗略地檢查一下這個病人,特別留神看有沒有「醫源性的」(醫師引起的)或是「源於醫院的」(院內感染的)疾病──這兩種加起來是美國的第八大主要死因──然後你就溜之大吉。
當你一大早去巡診,有時會遇到的狀況是:完全沒人抱怨。
那絕對不是好徵兆。
我進去的第五或第六間病房是杜克.莫斯比的,他馬上就成了我目前最不討厭的病人。他是九十歲的黑人男性,因為糖尿病併發症而入院,現在的病症還包括雙腳壞死。他是二次世界大戰在特戰隊服役的十位美國黑人之一,一九四四年從柯帝茲堡集中營(Colditz)逃出來。兩個星期以前,他從曼哈頓天主教醫院的這間病房逃走,全身上下只穿內褲──在一月耶,所以才引發壞死。糖尿病會搞壞你的血液循環,即使穿了鞋子也一樣。謝天謝地,當時值班的是艾克法。
莫斯比病房門邊的床上──他原本是用這張床,後來病房事務員認定要是他跟門口多隔五呎的話,逃走的機會比較低──有個我不認識的白人肥男。他留著金色短鬍鬚,髮型前短後長,五十五歲。他醒著,身體側躺,燈還亮著。我稍早查電腦的時候,他的「主要疾病」(直接引用這位病患的話,就會讓他看來像個白癡)只說是「屁股痛」。
「你屁股痛啊?」我問他。
「嗯,」他咬緊牙關說:「現在連肩膀也痛起來了。」
「我們先從屁股開始,什麼時候痛起來的?」
「我已經講過了,病歷上有。」
可能有吧,反正也是在紙本的病歷上。既然紙本病歷是病人唯一能索取的東西,而且法官可以拿來傳喚某人出庭作證,所以醫務人員沒什麼動力把字寫清楚。屁股男的病歷內容看來就像小孩畫的某種海浪。
至於他的電腦病歷呢(這是非正式的,誰想給我什麼資料都隨他),「主訴:屁股痛」。除此之外只寫著:「是nuts?或是坐骨神經痛?」我連這裡的「nuts」代表的是「睪丸」或「瘋狂」都不清楚。
「我知道,」我說:「不過如果你再說一遍,有時會有好處。」
雖然他不吃這一套,可是他又能怎樣?
「我的屁股痛起來,然後愈來愈痛,」他開始忿忿不平地說:「大概有兩個禮拜了,最後我就到急診室來了。」
「你因為屁股痛而掛急診?那一定痛得要命。」
「媽的,痛得我死去活來。」
「現在也是嗎?」我看看這傢伙的止痛點滴,注射了那麼多的氫嗎啡酮,就算用削胡蘿蔔器來剝他手上的皮,應該都不會有感覺吧!
「現在也是,我可沒有藥癮。媽的,現在連肩膀也在痛。」
「哪裡?」
他指著接近右鎖骨中間的一個點。我可不會把那裡當肩膀,算了,隨他。
外表看不出什麼。「這樣會痛嗎?」我問,一面輕戳一下那個地方。男人放聲尖叫。
「誰啊?」杜克.莫斯比從另一張床上質問。
我把簾子拉開,好讓莫斯比看到我。「長官,就我啊!」
「別叫我長官啦──」他說。我又放下簾子。
我低頭看看屁股男的生命徵象紀錄表:體溫華氏九十八點六度,血壓一百二/八十,呼吸頻率十八,脈搏六十。一切完全正常,就跟莫斯比病歷上的沒兩樣,也跟我今天早上在病房區看過的每個病人的一模一樣。我像他老媽一樣摸摸他的額頭,火燒似的燙。
幹。
「我要替你安排一些斷層掃描。」我告訴他。「最近有沒有看到護士過來?」
「昨天晚上以後就沒有了。」他說。
「幹!」我大聲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