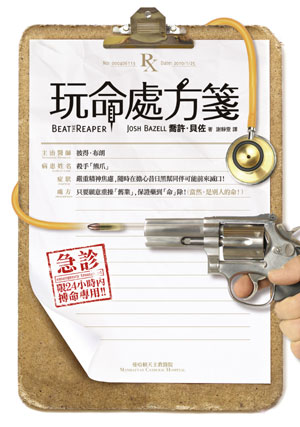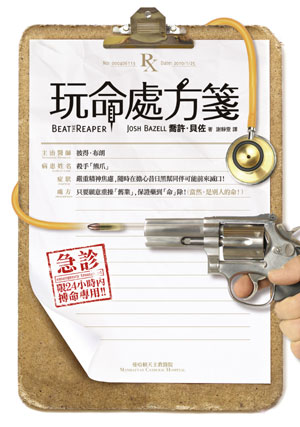內容試閱
想也知道,從這裡算起的第五間病房有個女人翹辮子了,臉上一副魂飛魄散的模樣,生命徵象表寫的也是:「體溫華氏九十八點六度,血壓一百二/八十,呼吸頻率十八,脈搏六十。」即使她的血液根本都集中在背部底層,看來好像在兩吋深的藍色墨水池裡躺了好一陣子。
為了讓自己鎮定下來,我去找兩位護士長幹架。一位是臃腫的牙買加裔女人,她正忙著寫檢查結果;另一個是愛爾蘭裔的醜老太婆,她正在網上樂逍遙。她們兩個我都認識,也挺喜歡的。我喜歡牙買加裔那位,因為她有時會帶吃的來;喜歡愛爾蘭裔那個,因為她老把自己的大鬍子剃成山羊鬍。她這麼做,等於是對全世界宣告操你的,我還真不知道有什麼更猛的手段。
「不是我們的問題。」等我一股腦兒抱怨完以後,愛爾蘭人就說:「而且我們也沒辦法啊!誰叫值夜班的是那群拉脫維亞來的賤貨,她們現在可能把那女人的手機拿去外頭叫賣了。」
「把她們炒掉嘛!」我說。
這句話逗得兩位護士長笑呵呵。「現在護理人手有點缺,」牙買加人說:「怕你沒注意到。」
我注意到了。我們顯然把加勒比海、菲律賓和南亞的每個護士都用光了,現在已經深入東歐挖人去了。等尼采的姊姊在巴拉圭成立的白人優越主義團體再次從叢林裡現身時,至少那些成員的工作都有著落了。
「哼,我才不要寫死亡診斷書咧!」我說。
「了不起。去害那個巴基斯坦人吧,嗯?」愛爾蘭人說,她的臉簡直就要貼在電腦螢幕上了。
「艾克法是埃及人,」我說:「不行,我才不要留給他弄,我要留給妳們的拉脫維亞壞蛋來弄。Stat(這是statim──馬上辦、立刻處理的縮寫,雖然沒縮多少就是了)。」
牙買加人感傷地搖搖頭。「這樣也沒辦法把那位女士救回來,」她說:「你要他們弄死亡診斷書,他們只會發出緊急呼救(若你想假裝不知道有人已經死了,那就發出緊急呼救)。」
「我管他去死。」
「潘妮拉,妳呢?」牙買加人說。
「我才不管。」愛爾蘭人說。「蠢貨。」她壓低嗓子追加。
從牙買加女人的反應看來,她知道愛爾蘭女人罵蠢貨時,指的是我而不是她。
「反正叫他們弄就是了。」我離開時說。
我覺得舒坦多了。
即使才做那麼點事,我就得以稍微喘口氣了。我半小時前嚼掉魔術方,怕魔術方太久才會生效,又配上我在實驗衣裡的信封找到的右旋安非他命,結果弄得我很難集中精神。我的精神爆衝得有點太猛了。
我真愛右旋安非他命。藥丸是盾形的,中間有一道垂直線條,所以看來就像女陰。
可是即使光是吃右旋安非他命,有時也會讓人很難集中心思或目光。配上魔術方,周圍的東西就會模糊混沌起來。
我到住院醫師的值班室想放鬆一下,也許再吞點我藏在床框裡的苯二氮類藥物。
不過,我一打開門,就知道黑漆漆的房裡有人,因為整個房間淨是口臭與體臭味。
「艾克法嗎?」雖然知道不會是他,我還是這麼叫。艾克法的體味,我到踏進墳墓都會記得,現在的味道更糟,比杜克.莫斯比的腳還臭。
「老兄,我不是。」擺了上下舖的那個角落裡傳來虛弱的聲音。
「那你他媽的是誰?」我低吼。
「外科鬼魂。」那個聲音說。
「你在醫學值班室裡幹嘛?」
「老兄,我……我需要找個地方睡一下。」
他的意思是「沒人找得到我的地方」。
好極了。這傢伙不只把值班室燻得臭兮兮,還占去了唯一可用的那張床。上舖鋪滿了一九七八到一九八六年的每一期男性色情雜誌《是的》,根據經驗,我知道要把雜誌搬開,實在太麻煩了。
既然房間未來好一陣子都會臭得無法使用,我考慮讓他待下來,可是我吃下的魔術方還在作用,況且總是可以威嚇一下。
「我給你五分鐘滾出去,」我跟他說:「要是超過時間,我就拿一瓶尿倒在你頭上。」
我離開的時候,隨手打開了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