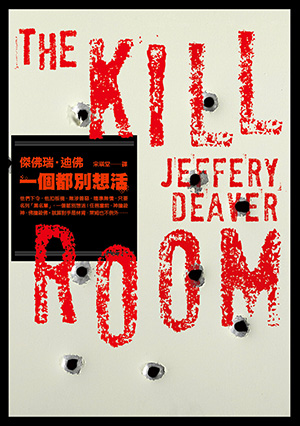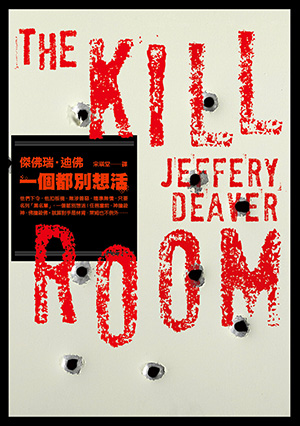「他到底出發了沒?」林肯‧萊姆問,不掩煩躁的心情。
「醫院那邊有事,」湯瑪斯如此回應,他在走廊或廚房或某處。「他被耽擱了,走得開的時候,他會來電告知。」
「有事。」哼,很具體嘛,「『醫院有事。』」
「他是這麼告訴我的啊,沒錯。」
「他是醫生,醫生應該講究精準,而且應該準時。」
「他是醫生,」湯瑪斯回應,「這表示他碰到緊急狀況,要他處理。」
「那他怎麼不說『緊急狀況』?他說的是『有事』。我的手術排在五月二十六號。我可不想被拖延,反正離現在太遠了,他幹嘛不能提前手術?」
萊姆坐在名為「風暴箭」的電動輪椅上,這時移向電腦顯示幕,停在艾米莉亞‧莎克斯坐的籐椅旁。莎克斯穿黑牛仔褲,上身是黑色的無袖T,纖細的金項鏈垂吊著一顆鑽石加一顆珍珠,時辰還早,春曦從東窗射入,若即若離地斜照紅髮,盤得妥貼的頭髮以白鑞髮夾固定,萊姆把注意力轉回螢幕,瀏覽著兇殺案的現場報告,他剛為紐約市警局偵破這件刑案。
「快辦完了,」她說。
這裡是萊姆家,位於曼哈頓中央公園以西的一棟城市屋,兩人坐在起居室裡。在特威德老大當道的十九世紀中葉,據推斷這裡應是會客室,氣氛靜肅,如今被萊姆改裝為設備一應俱全的刑事化驗室,充滿檢驗證物的設備和儀器、電腦和電線,滿地爬的電線令萊姆的輪椅無處不顛簸,但他唯有肩膀以上才感受得到。
「醫生遲到了,」萊姆對莎克斯嘟囔。這話是畫蛇添足,因為莎克斯坐在十英尺外,聽得見他和湯瑪斯的對話,他只是心情煩躁,多唸幾句才舒服,他謹慎將右手臂移向觸控板,讀完報告的最後幾段。「好。」
「要不要我寄出?」
他點頭,莎克斯按鍵,整份六十五頁的加密文件進入網路空間,最後抵達六十英里外的皇后區紐約市警局刑事檢驗設施,即將成為泰‧威廉斯案的起訴主軸。
「完成了。」
完成了……只剩出庭作證,本案的主嫌是毒梟,曾教唆多名十二、三歲小孩在東紐約與哈林區殺人。萊姆和莎克斯循線採集細小的微物證據和壓痕,加以分析,從被指使人的鞋子,查到曼哈頓一家店面的地板,查到一輛凌志轎車的地毯,查到布魯克林區一家餐廳,最後指向威廉斯的住處。
證人遇害時,黑幫老大威廉斯不在場,也沒摸過兇槍,也沒有證據指出他教唆殺人,而年幼的槍手更不敢拱出老大。然而,再多的阻礙也難不倒檢方:萊姆和莎克斯已牽出一條證據線,從刑案現場連結到威廉斯的巢穴。
他勢必在監獄裡度完餘生。
萊姆的左手臂被束在輪椅上,無法動作,這時莎克斯一手放在他左手臂上,從她白皮膚下依稀可見的手筋,萊姆看得出她握一握他的手臂。高挑的莎克斯站起來,伸伸懶腰,兩人大清早就忙著趕這份報告,她五點起床,他比她晚一些。
萊姆留意到,她走向桌子拿咖啡杯時蹙眉,最近她髖骨和膝關節炎痛得厲害,萊姆因脊椎受損而四肢癱瘓,當時的傷勢據描述是重大無比,但他卻連片刻的苦痛也沒嘗到。
無論是誰,肉身終將多多少少令人失望,他想著。即使是目前大致安康如意的人,也會被天際的烏雲影響到心情,他憐憫那些已提心吊膽等候健康走下坡的運動健將、俊男美女、年輕人。
儘管如此,諷刺的是,對林肯‧萊姆而言,他的情況正好相反,受傷之初,他深陷十八層地獄,但拜日新月異的脊椎手術之賜,再加上他奮戰不懈的態度,潛心做復健,追求高風險的實驗療程,他的病情已見起色。
想到這裡,他又氣醫生遲到,萊姆的手術日將至,醫生今天的約診是來評估他的狀況。
雙音式電鈴響起。
「我去開。」湯瑪斯喊。
這棟房子當然為殘障人士調整過,萊姆透過電腦看得見門外人,也能互相交談,開不開門的決定在他手上。(他不愛會客,如果看護湯瑪斯不搶先一步,來人常常會被他趕走,有時口氣很兇。)
「誰啊?先過濾一下。」
不可能是貝靈頓醫師,因為醫生說過,耽誤他行程的「事」一忙完,他會馬上來電告知。萊姆沒心情見其他客人。
看護有無過濾來人都不重要了,因為隆恩‧塞利托已走進起居室。
「老林,你在家啊。」
瞎猜也猜得中。
矮胖的塞利托警探直奔點心和咖啡的托盤。
「想吃新鮮一點的嗎?」湯瑪斯問。苗條的看護兼助理湯瑪斯穿著平整的白襯衫和深色長褲,結著碎花藍領帶,今天的袖口鏈是黑檀木或縞瑪瑙。
「不用了,謝啦,湯瑪斯,嗨,艾米莉亞。」
「嗨,隆恩,瑞秋好嗎?」
「很好。她最近迷上皮拉提斯了,怪詞一個,運動之類的東西。」塞利托照老習慣,穿著皺巴巴的褐色西裝,粉藍色襯衫也皺巴巴,今天結的條紋紅領帶卻一反常態,平直得像一片被刨過的木板。萊姆推測,是他最近收到的禮物,是女友瑞秋送的吧?現在是五月──沒有節慶假日,也許是生日禮物,萊姆不知道塞利托的生日,也不清楚多數人的生日。
塞利托啜飲著咖啡,騷擾著丹麥麵包,只咬兩口,他永遠在節食。
萊姆和他幾年前是同事,兩人是搭檔,意外發生之後,讓萊姆重新振作起來的最大功臣是塞利托,塞利托對他不哄不誘,而是強迫他起而行,叫他再開始辦案。(更確切的說法是,叫萊姆好好坐著,重回工作崗位。)儘管兩人交情如此深,塞利托找他絕不是想串門子,他是重案組的一級警探,辦公室位於警察廣場一號的大樓,萊姆受聘協辦的案件通常由他主導,塞利托登門必定有好兆頭。
「怎樣?」萊姆上下打量他。「有好消息給我嗎,隆恩?碰到引人入勝的刑案嗎?耐人尋味嗎?」
塞利托小口吃吃喝喝著,「我只知道我接到高層的電話,他們問你有沒有空,我告訴他們,你辦威廉斯的案子快結束了,然後長官叫我趕快過來見某某人,他們就快來了。」
「『某某人』?『他們』?」萊姆尖酸問,「不明不白的,跟耽擱我醫生的『事』有得比,這種籠統語好像會傳染,像流行性感冒。」
「喂,老林,我只知道這麼多。」
萊姆朝莎克斯使眼色,眼神諷刺,「咦,這件事,怎麼沒人打電話通知我?有人通知妳嗎,莎克斯?」
「一通也沒。」
塞利托說,「喔,是因為有另一件事。」
「哪件?」
「總之是機密啦,不保密不行。」
萊姆想想,也好,至少朝耐人尋味邁出了一步。
兩位外形迥異的客人進起居室,萊姆望向他們。
其中一人是五十幾歲的中年男子,姿態像軍人,穿著不是訂做的西裝──從肩部看得出,西裝是接近黑色的海軍藍。他臉上無鬚,下巴下面吊著一團肉,皮膚日曬過,短髮近似陸戰隊,萊姆心想,肯定是警界高官。
另一位是三十出頭的女子,體形逼近肥碩,但不算臃腫,還差一點。她的金髮缺乏光澤,頂著一九六○年代的髮梢外翹式古板頭,被髮膠噴得硬邦邦,她的臉色蒼白,原因是肉色的粉餅撲得太起勁了,萊姆看不出她臉上有任何青春痘或痘疤,猜想粉餅是愛美的抉擇。她的黑眼珠深邃如槍口,不施眼影,不畫眼線,在粉白臉的襯托下更顯突兀。她的薄唇也無色,而且乾燥,據萊姆評估,這張嘴綻放微笑的情形不常見。
她的眼睛會挑東西看,停在儀器、窗戶、萊姆上,然後以雷射光一個個定睛凝視,直到對象被看透或被她認定無關緊要,目光才轉開。她的套裝是深灰色,也不是名牌貨,三顆黑色塑膠釦全釦得緊緊的,排列微微歪斜,令萊姆懷疑她該不會是挑中完全合身的套裝後,嫌鈕釦顏色太顯著,所以自行找釦子換上。矮跟黑皮鞋的高度不太均勻,而且最近用液體鞋油掩飾過磨痕。
明白了,萊姆心想,他自信認得她在哪裡高就,因此,萊姆更加好奇。
塞利托指著中年人說,「老林,這位是比爾‧麥爾士。」
中年人點點頭。「隊長,久仰了,很榮幸認識你。」幾年前,萊姆因殘障而自紐約市警局退休,當時官拜隊長,麥爾士喊他的官銜,證實萊姆的猜測無誤:他果然是警界高官,而且相當資深。
萊姆操作電動輪椅向前,伸出手,高官注意到他伸手的動作不自然,遲疑一下,然後才和萊姆握手,萊姆也留意到另一現象:莎克斯微微怔了一怔,她認為社交場合的動作能省則省,不喜歡萊姆用手,但萊姆就是憋不住。四肢癱瘓了十年,他努力違抗命運之神,值得驕傲的勝仗屈指可數,不用白不用。
更何況,玩具豈有擺著不玩的道理?
麥爾士介紹另一位神秘的「某某人」,她名叫南絲‧蘿若。
「我是林肯。」他說。再度握手,這次對方的手勁似乎比較強,萊姆心想,但他當然無法判定,能動並不代表知覺也恢復了。
蘿若犀利的目光投向萊姆的濃密棕髮、豐滿的鼻梁、敏銳的黑眼,除了「哈囉」別不多說。
「妳嘛,」他說,「是助理檢察官。」地檢署助理檢察官。
萊姆的這份推斷有一半是猜測……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