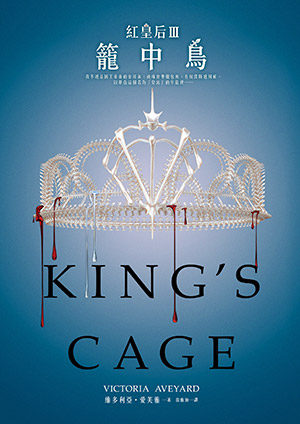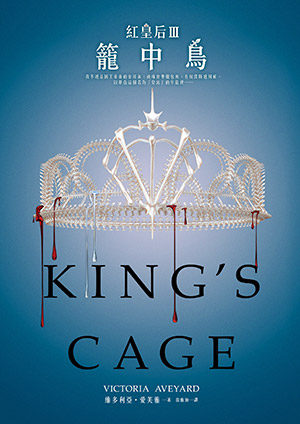內容試閱
我們一踏上蒼火宮的階梯、回到宮殿的入口,他便把我的鎖鏈交給其中一名亞芬門脈的警衛。真奇怪,他一直這麼堅持要把我抓回來,堅持要把我放在他的牢籠中,但是卻沒多看我一眼,就把我的鎖鏈丟給了別人。就是個孬種。我暗自忖度。若不是為了作秀,他連看我一眼都做不到。
「你有遵守承諾嗎?」我問道,只覺得快要窒息。這麼多天沒說話,我的聲音聽起來好沙啞。「你是信守承諾的人嗎?」
他沒有回答我。
整個宮廷裡的人都跟上我們的腳步,隊伍縝密,按照複雜的位階排成。只有我不在其中,我是國王身後的第一人,就走在他身後幾步遠,原本皇后該在的位置,但我跟皇后這個身分的距離可說是天差地別。
我瞥了一眼身材比較高大的那個獄卒,希望能從他的盲目忠誠之中,再看到一點什麼別的也好。他身著白色制服,質地厚重、防彈,拉鍊拉到頸子上。雙手戴著閃閃發亮的手套,不是絲質,是塑料製成的──橡膠材質。我不禁打了個冷顫。即便已經有了屏蔽的能力,面對我,亞芬家的人也不願冒險。如果我真的能掙脫他們從不間斷的監視,擠出那麼點電光火花,那雙手套也能保護他們的雙手,讓他們繼續用項圈和鎖鏈限制住我、把我關在牢籠裡。這個大個子亞芬家的人不跟我四目相交,他的視線直盯前方,專注思緒地緊抿著嘴。另一人也一樣,跟他的兄弟或表親一人一邊,完美地包夾著我。兩人光溜溜的頭皮發著光,我想起路卡斯˙薩摩斯。我那親切的警衛,我的朋友,那個因為我的存在、因為我利用了他而被殺頭的人。那時是我走了運,卡爾派給我這麼一個正直的銀血人來看守我這個囚犯。而現在我意識到,我仍很幸運,冷漠的警衛比較不會讓我再開殺戒時覺得有所愧疚。
因為不論如何,他們終究難逃一死。如果我要逃脫,如果我想要重獲我的閃電,他們就是第一個阻礙。剩下的人就那些,大抵就是馬凡的哨兵人、遍布在宮廷中的警衛和官員,當然還有馬凡本人。除非他已經成了一具死屍,否則我是不會離開的──要不就是留下我的遺體也行。
我想過要殺他。把我的鎖鏈勒在他的頸子上,猛力地把他的生命擠出體外。想像這畫面能讓我暫時不去注意自己踏在這蒼白大理石地板上的每一個腳步、經過的每一道鍍了金的高聳牆面、每一座高掛火焰雕飾的水晶吊燈,其實全都在往宮廷更深處前進這件事。這地方就跟我記憶中一樣富麗、一樣冰冷。這是一座用黃金鎖和鑽石柱打造成的監獄。至少我不用再面對那最暴力、最危險的典獄長。那個皇后已經死了。只不過光是想到她,仍足以讓我打冷顫。亞樂拉˙莫蘭達斯,她的影子像鬼魂一樣穿過我的腦海。她曾強行進入我的記憶之中,現在她成了我眾多記憶之一。
一個身著盔甲的身影走進了我的視線之中,繞過我的警衛,把自己安置在國王與我之間。他的腳步配合著我們,像是一個堅定的守護者,雖然他身上沒有穿著哨兵人的袍子或面具也一樣。我想他大概發現了我想勒死馬凡的念頭吧。我緊咬嘴唇,準備好要迎接悄語者尖銳的攻擊帶來的刺痛。
但是那痛楚並沒有發生,他不是莫蘭達斯門脈的一分子。他的盔甲是黑曜岩的色澤,一頭銀色的髮絲,皮膚像月光一樣白皙。他的雙眼,當他回頭看我的時候──他的視線空洞洞的,只有一片漆黑。
托勒瑪斯。
我露出牙齒向前一衝,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有這個行為,但我也不在乎。只要能留下我的咬痕就好了,不知道銀色的血嚐起來跟紅色的血是否一樣滋味。
但我是不會知道了。
我的項圈被用力向後一拽,力道之大,我撞上地面時連脊椎都疼痛不已。再用力一點,我的脖子可能就斷了。大理石撞上腦門的瞬間,整個世界天旋地轉,但這力量還不足以讓我起不了身。我吃力地掙扎,瞇起眼睛看著托勒瑪斯穿著盔甲的雙腿,轉過來面對我。我再次往他撲過去,項圈也再次把我往後拉。
「夠了。」馬凡咬牙切齒地說道。
他站在我身旁,阻止我繼續可悲地試著對托勒瑪斯進行復仇。整個移動中的隊伍也都停了下來,不少人湊上前來,想看看我這發瘋的紅血老鼠做無謂掙扎的情景。
項圈似乎變得更緊了,我上氣不接下氣地伸手抓自己的喉嚨。
馬凡看著金屬項圈慢慢收緊,「伊凡喬琳,我說夠了。」
痛歸痛,我還是回頭看站在我身後的伊凡喬琳,她一手拳頭在身旁緊握著,視線跟馬凡一樣,停在我的項圈上頭。視線一動,項圈就跟著拉扯。我的項圈一定跟她的心跳同步了。
「讓我把項圈拿掉,」她說道,我以為自己聽錯了。「讓我在這裡把她的項圈拿掉,解散她的警衛,我會在這裡解決她,我不在乎有沒有什麼閃電。」
他們視我為野獸,我就用這模樣對她齜牙咧嘴地說道,「試試看啊。」我全心全意地希望馬凡會答應她。就算我滿身是傷、能力又被屏蔽了好幾天,還有我這麼多年來比這個磁能者女孩低下的身分,我還是想要她提出的條件成真。我打敗過她一次,我可以再做一次。至少,這也是一次機會,是我唯一的指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