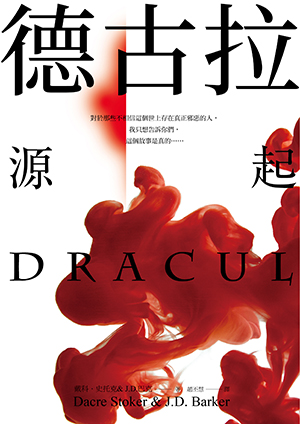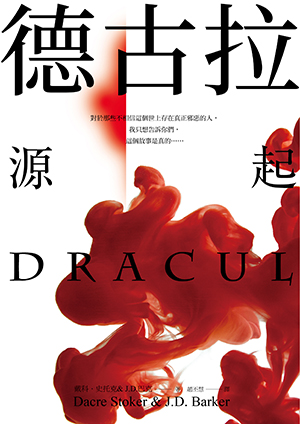內容試閱
我經常回想愛倫.柯榮的美。七歲的我不曾想過這種事,可是成人後我卻無法否認她的魅力,她的皮膚亮澤,如新雪般潔白無瑕,找不到一顆痣,看不到一條細紋,連眼周或嘴角都沒有。她一笑,皓齒令人豔羨。我們經常拿她的年齡開玩笑── 她以及我們大家。她在一八四七年來到我們家,就在我出生前幾週── 就在卡格倫小姐因健康問題而離開後,她說她雙手的關節炎讓她沒辦法照顧孩子。卡格倫小姐照顧過松利和瑪蒂妲,原以為可以再待個一年,讓媽能夠找到接替她的人,她提早離開的時間也真不湊巧,爸大多數時間在城堡裡,因為饑荒開始了,而媽挺個大肚子壓根不適合面試新人。愛倫就在這時出現了── 只靠口耳相傳,她聽說了雇傭的機會,就來到了我們的家門口,只拎著一個小袋子。她自稱十五歲,是孤兒,在前雇主家照顧孩子五年── 一男一女,分別是五歲和六歲── 不幸他們全家人都在上個月死於霍亂,前雇主的太太是助產士,愛倫說她協助過幾十位產婦分娩,她願意暫時以勞力換取住宿和微薄的薪水,至少等到我出生後,讓媽有時間復元,爸跟媽沒有別的人選,所以歡迎愛倫.柯榮進入我們家,而她立刻就變成了不可或缺的好幫手。
我在一八四七年十一月出生,生產並不順利。胎位不正,臍帶纏住了我的脖子;接生的人是我父親的表親,一位都柏林的優秀醫師,他相信我是死胎,因為我沒發出一點聲音,愛德華.亞歷山大.史托克表叔宣佈在我的藍色皮膚下聽不到心跳,可是愛倫一口咬定我沒死,把我從他手上搶過來,幫我吹氣,吹了差不多三分鐘,我才終於咳出聲,加入了生者的世界。媽跟爸訝異極了,愛德華表叔說簡直是奇蹟,媽後來告訴我她很確定我胎死腹中,因為我幾乎不動;已經生過兩個孩子的她有實際經驗可供參考,所以覺得很肯定。因此,她沒讓爸挑名字,一直到我開始呼吸,確證沒死,她才同意了亞伯拉罕這個名字(跟我爸一樣),這才把我抱進懷裡。
往後的年月裡,媽跟我說愛倫保姆那晚形容枯槁── 彷彿是她自己生產,而且耗盡了全身的力氣,我被穩穩當當放在我媽身邊之後,愛倫立刻回她的房間,將近兩天沒現身,讓爸很沮喪,他在門口哄了她好幾個小時,因為他需要人幫忙照顧孩子和媽,那兩天愛倫保姆成了隱形人,第三天她終於現身,隻字不提隱居不出的事,只是又回頭忙家務,爸如果找得到幫手,早開除她了。
我出生後的頭三天,健康每況愈下,爸很怕我活不過另一晚,我的呼吸短促,會被口水嗆到。我到現在還沒哭過,眼睛對周遭的刺激不起反應,我不肯吸奶、不肯進食。愛倫把我的小床搬進了她的房間,清醒的時刻都在照顧我,禁止別人來看我── 她說我需要休息,他們雖不情願,仍然聽從了。在我生出後第五天,約莫凌晨兩點,我的哭聲第一次響徹屋宇,連松利和瑪蒂妲都吵醒了,他們也跟著哭了起來。爸把媽攙扶到愛倫的門前,她打開了門,而襁褓中的我躺在她的懷裡,人人都知道危險期過了,我活下來了。媽說愛倫在那一刻老了好多,比在我出生後的模樣更憔悴,把我交給媽之後,愛倫.柯榮直接走下樓梯,走出了大門,沒入夜色,整整兩天沒回來。
等她終於回來,她又恢復了青春的模樣,臉頰紅潤,藍色眼睛炯炯有神,唇邊掛著笑容。這一次爸沒有責備她離開,因為她一走我的狀況就惡化了,而他知道她能夠像前兩次一樣幫助我,他把我的小床又搬進了她的臥室,愛倫鎖上了門,房間裡只有我們兩個。等她再開門,我的健康會改善,而她則一臉病容。這種模式在我剛出生的那幾年一再重複,重複了幾十次── 她會把我照顧到恢復健康,然後消失幾天,再回來時精力充沛,再次接手。她緊閉的房門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她從未透露,爸跟媽也不問,可是她的眼睛卻說了出來── 她在健康最佳時眼珠是深藍色的,而在她離開前不久眼珠是淡灰色的。
我瞪著現在是灰色的眼珠,知道她沒多久就會離開。
「也許你應該留意你自己的健康,而不是忙著想像我眼睛的顏色。我的眼睛顏色會變是因為我穿的衣服,要是我穿紅色的,說不定會跟奈斯比先生在酒館裡泡了一晚一樣,變得火紅色的?」
「妳很快就要走了,對不對?」
瑪蒂妲一聽見精神就來了。「不要,保姆,妳不能走!妳答應要讓我幫妳畫像的!」
「可是妳已經畫過幾十張── 」
「妳答應了。」她使性子。
愛倫走過去,一指拂過她的臉頰。「我只去一天,最多兩天。我不是每次都會回來嗎?到時候我再讓妳幫我畫另一張像。我不在的時候,我需要妳照顧妳弟弟,幫妳母親的忙,她現在忙著照顧理查寶寶,妳覺得我不在的時候妳能管好這個家嗎?」
瑪蒂妲不甘不願地點頭。
「那就好,我最好下樓去準備晚餐了。」她又把冷冰冰的手放在我的額頭 。「要是你再不好,我就得把你的愛德華表叔叫來了。」
一聽見這話,我的胃就打結,可是我沒作聲。
我的發燒惡化了。那晚第九個小時,我的身體痛得要命,床單都被汗水浸濕了。媽坐在我身邊,腿上擺著一盆水,用濕布擦拭我額頭上的一層汗,我不知在何時抗拒她。我好冷,濕布感覺像冰塊,我兩手亂揮,趕走她,松利和爸進來,按住我,壓制住我的手腳。我的呻吟聲在整棟屋子裡迴盪,發自喉嚨的聲音比較像是受傷的動物,而不是兒童。
我聽見走廊那邊愛倫保姆的房間裡傳來理查寶寶的哭喊,媽叫瑪蒂妲過去看看。我記得她抗議,只是忘了她抗議什麼。她不想離開我,可是媽堅持。她被禁止把寶寶抱進我的房間,怕會感染了我的病。我想我們都知道這點很不合理── 我病了許多年,也沒傳染給家裡的人──但我們似乎都同意最好還是不要冒著害嬰兒感染的風險。
瑪蒂妲從我的房間衝出去,我聽見爸在咒罵愛倫保姆幾個小時前請假。他們依賴她,而此時此刻更是需要她,然而她卻走了,只有她自己知道理由。在我發高燒的心裡,瑪蒂妲給我看的畫像發出了光芒:幾十個模糊的女人融為一體,酷似愛倫保姆,但是不到一秒,就又碎裂,變回陌生人的畫像,年齡不一,相貌各異,全不相同,也全部相同。她們的眼睛從鉛筆素描的黑白色到唯有油彩能畫出的最鮮豔的藍,透過旋轉的黑暗面紗凝視我。我能聽見保姆的聲音,可是她的聲音好遙遠,彷彿是在港口那邊尖叫,而叫聲被霧吞沒。然後,她的臉孔近在咫尺,她飽滿的紅唇在動,卻沒發出聲音。一會兒,媽回來了,用冰冷的濕布把這一切都擦掉,我想把她揮開,可是我的胳臂不聽使喚。一切歸於漆黑,我覺得像墜入了井裡,上頭的世界消失,我被大地吞噬,我的背著火,高速衝入地獄。我聽見媽喊我的名字,可是我離家太遠了,我知道要是她知道我已經離家了,我會挨罵,所以我一聲不吭,只是閉上眼睛,等待著落入深淵的撞擊。我覺得活生生被推入自殺塚裡就是這種感覺。我等待著令人窒息的土壤,擺好姿勢等著死在它的一片污穢之下,成為蛆蟲的大餐。
「布拉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