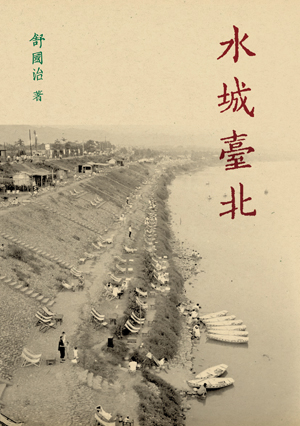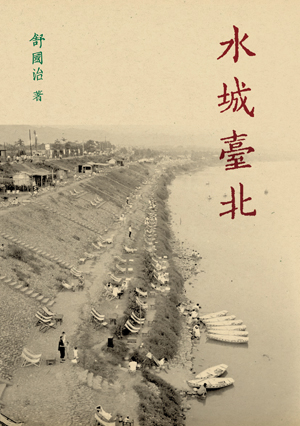內容試閱
〈永和───無中生有之鎮〉
在某一個特殊的年代(像是離亂剛歇、不興不止),會結凝出某一襲特殊的氣氛(像是波盪不定,卻又安寧不見有動靜),而將這種種呈現在一個特殊的邊搭地方(像是倉皇劃出、不城不鄉);這樣的年代往往短暫,如同權宜,一個不注意,竟自逝去了,而這樣的氣氛與地方也頓時見不著了。
曾經有這樣一個地方,我小時親眼見過。它的時光永遠都像是下午;安靜緩慢、所有人都在睡午覺的下午。它的佈局永遠都是彎曲狹窄的一條條不知通往哪裏的巷子;兩旁的牆與牆後的房、樹、與瓦都像是為了圈圍成這些引領人至無覓處的長而彎仄的巷子。它的顏色,永遠都是灰。它的人,永遠只是零零落落,才出現又消失,並且動作很慢,不發出什麼聲音,總像是穿著睡衣、趿著拖鞋,沒特要上哪兒去的模樣。倘站在巷口,只像是目送偶一滑過的賣大餅饅頭的自行車。
真有這樣的一處天堂,在六十年代,叫「永和鎮」。
馬路上的公共汽車或公路局班車皆是舊舊的,揚起的灰塵飄落在尤加利樹的蒼舊葉子上。尤加利樹,那個年代所習用暫時為街路形廓打上樁子之象徵,透露出這裏實是新劃區。而灰塵,與此鎮的本質色根,灰色,來自河邊無盡的沙洲。
這裏見不到根深柢固的大樹(台北市其實也極少),及樹後的莊嚴古廟宏殿(如台北龍山寺,大甲鎮瀾宮),見不到舊家園林(如板橋林家花園,新竹鄭用錫北郭園),見不到豪門巨賈(如迪化街,貴德街那種西洋樓),甚至沒有頗具規模的眷村(如台北的成功新村,四四東、南、西村)。這裏也沒有良田萬頃、阡陌處處,沒有茶山層層、水牛徜徉林野。沒有。有的只是野竹叢,此一撮,彼一撮;只是番薯地,零散的菜畦,疏落的葡萄園,水溝邊的絲瓜棚而已。當然,還有人家,在遺忘的年代間雜建於那些凌亂的角落,用的只是粗簡材料的人家;以是在這裏看不到工整成形的日式宿舍。
是的,人家。便因這些乍然出現的一戶又一戶人家,使永和之所以成形為永和。六十年代,在台北,任何人都有幾個朋友住在永和,每個小孩都有一二同學家住那裏。太多的北部人都知悉它的一二名聲,說什麼永和出豆漿、出皮鞋、出美女,甚至說出彈子房、出竹聯幫。
它像是演員金永祥慢推著二十八吋腳踏車在永安市場買菜的那種小鎮。像是江明、馮海這種不算大紅而又樸素自持的六十年代小生可以卜居的小鎮。像是武俠小說家高庸構思奇情打鬥聊寄閒愁的荒澀小地方。也像是電台主持人包國良穿著汗衫站在安樂路家巷口的家居閒景。作家侯榕生在文化路,陳紀瀅、王藍在竹林路,皆能幽幽的享受收音機傳出的京戲聲。這裏太過粗簡平淡,以是即使有將軍(抗日名將吉星文住在潭墘里)、國大代表等卜居,卻看不見官宅大院的霸嚴氣象。這裏太零散,牆面太斑駁,牆角太生雜草,以是最沒有階級,最小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