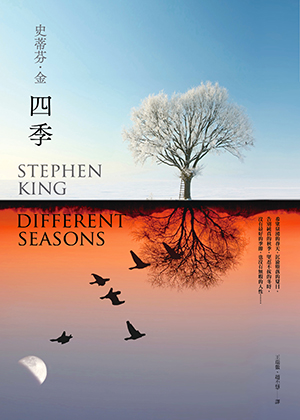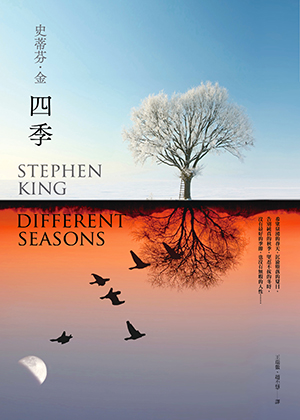內容試閱
一九四八年,安迪剛來裘山時是三十歲。他是個外表整潔的小個子,有著沙褐色頭髮、小而靈巧的雙手、臉上戴著金邊眼鏡。他的手指甲總是剪得很短,而且總是很乾淨。對一個男人留下這印象有點怪,不過在我眼中這就是安迪,他永遠給人一種應該打上領帶的感覺。入獄前,他是一家波蘭大銀行信託部的副經理。以他的年紀來說,這算是一份好差事,尤其當你考慮銀行多半很保守的時候。再加上當你北上來到新英格蘭六州,這保守還得乘上十倍,因為這裡的人不會輕易把錢交給別人,除非這人又禿又跛,不停扯著褲管來讓自己看來收斂端正些。而安迪,他是因為謀殺妻子和她的情夫進來的。
相信我之前說過,監獄裡的每個人都是無辜的。當然,他們也讀那本聖典,就像電視上那些宗教狂熱分子讀《啟示錄》一樣虔誠。他們全是鐵石心腸的法官、無能的律師、警方陷害或狗屎運的受害者。他們也讀經文,但是你可以在他們臉上看見不一樣的經文。多數罪犯都是對自己或別人沒有好處的低等人,他們的最大厄運就是被他們的母親生下來。
在裘山這麼多年來,當人家告訴我他是無辜而我真心相信的,只有不到十個人,安迪.杜法蘭正是其中一個,雖說我是經過多年才確信他的無辜。如果一九四七到四八年,波特蘭最高法院如火如荼審理這案子的期間,我也在陪審團席的話,我肯定也會投票判他有罪。
那是非常轟動的一個案子,是那種具備所有要素的煽情案件。一個交遊廣闊的美女(死了),一個當地的運動好手(也死了),以及被告席上的傑出年輕實業家。這些,再加上報紙暗指的各種醜聞,檢察單位認為這案子非常簡單明瞭,而審理之所以拖了那麼長一段時間,完全是因為負責本案的地方檢察官計畫去參選眾議員,他希望普羅大眾能多看看他那張臉。他開庭時有如一場華麗的法律馬戲表演,儘管氣溫在零度以下,還是有不少人在清晨四點跑去排隊,等著入席旁聽。
安迪不曾抗辯的檢察官的起訴犯罪事實如下:他有一個妻子,琳達.柯林斯.杜法蘭;一九四七年她表示想到法爾茅斯山鄉村俱樂部去學高爾夫球;她確實上了四個月的高爾夫球課;她的指導教練是法爾茅斯山高爾夫球專家葛倫.昆汀;一九四七年八月底,安迪得知妻子和昆汀暗通款曲;一九四七年九月十日,安迪和琳達.杜法蘭發生激烈爭吵,兩人爭論的起因是她的不忠。
他作證說,琳達坦承她很高興他發現了。「偷偷摸摸,」她說,「真的很痛苦。」她告訴安迪,她打算到雷諾去申請快速離婚。安迪對她說,到雷諾免談,在地獄見面倒是可以。接著她離家,到昆汀位在高爾夫球場附近的出租小別墅去和他一起過夜。次日早晨,清潔婦發現兩人陳屍床上,分別身中四槍。
最後這個事實對安迪尤其不利。在開場陳述和結辯時,那位懷有政治抱負的檢察官都針對這點作了盡情發揮。「安迪.杜法蘭,」他說,「並不是一個試圖向出軌妻子進行熱血報復的屈辱丈夫。」「如果是這樣,」檢察官說,「就算不能被寬恕,也該得到諒解,但他的做法是一種更加冷酷的報復類型。」「想想看!」檢察官的聲音在法庭中迴盪,「四槍加四槍!不是六槍,而是八槍!他一直射擊到彈匣空了……然後停下來填裝子彈,然後再對著兩人繼續開槍!他四槍,她四槍。」波特蘭《太陽報》發出怒吼,波士頓《紀事報》則封他為「無差別殺手」。
路易斯頓市懷斯當舖的一名職員作證說,就在雙人謀殺案發生前兩天,他賣了一把六發子彈容量的點三八特種軍警型手槍給安迪.杜法蘭。一名鄉村俱樂部的酒保作證說,九月十日晚上七點左右安迪進來,在二十分鐘內灌下三杯純威士忌,而當他從酒吧凳子上站起來時,他告訴酒保,他準備前往葛倫.昆汀的房子,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看報紙就知道了。另一名距離昆汀別墅大約一哩距離的漢迪-皮克商店的店員在法庭上說,安迪在同一天晚上八點四十五分左右來到店裡,他買了香菸、三夸脫啤酒和一些擦碗巾。郡法醫作證說,昆汀和杜法蘭女士的遇害時間是在九月十日晚上十一點到十一日凌晨兩點之間。司法部長辦公室負責這案子的警探作證,距離小別墅不到七十碼的地方有個路邊休息區,九月十一日下午,警方從這塊區域得到三件物證:第一件,兩只空的一夸特裝納拉甘塞特啤酒瓶(上面有被告指紋);第二件,十二個菸蒂(全都是Kool薄荷菸,被告喜好的品牌);第三件,一組車輪胎紋(和被告那輛一九四七年普利茅斯車的胎紋和磨耗情況完全相符)的翻印石膏模。
昆汀的小別墅客廳沙發上攤著四條擦碗巾,上頭有好幾個被子彈貫穿的破孔,以及火藥灼痕。警探推測(受到安迪律師的激烈抗議),兇手用布巾裹住行兇手槍的槍口,來降低槍擊的聲響。
安迪.杜法蘭站上被告席為自己辯護,氣定神閒、不帶感情地描述事情經過。他說他早在七月底就開始聽聞關於他妻子和葛倫.昆汀之間那些令人傷心的流言。到了八月底,他實在太難受了,於是著手調查了一下,並在一個琳達原定在高爾夫球課結束後到波特蘭去購物的晚上,跟蹤她和昆汀來到昆汀那棟租來的兩層樓別墅(無可避免地被報紙稱為「愛巢」)。他把車停在路邊休息區,而三小時後,昆汀開車送她回鄉村俱樂部去取她的車。
「你是否要告訴庭上,當時你開著你那輛全新的普利茅斯轎車跟蹤你的妻子?」交叉詢問時,檢察官問他。
「那晚我和一位朋友交換車子。」安迪說。在陪審團眼中,這種冷靜招認自己是如何用盡心計去刺探的態度,對他毫無幫助。
把朋友的車子歸還、拿回自己的車子後,他回到家中。琳達正在床上看書,他問她波特蘭之行如何?她回答說十分有趣,不過她沒發現中意的東西,因此什麼都沒買。「就在這時,我打定了主意。」安迪告訴屏氣凝神的聽眾,說話口吻依然那麼冷靜、淡漠,就像他在整個出庭作證期間的表現一樣。
「從當時一直到你妻子被殺害那晚之間的十七天當中,你的心境如何?」安迪的律師問他。
「我非常痛苦。」安迪冷漠而平靜地說。他敘述著他曾經考慮自殺,甚至在九月八日那天到路易斯頓去買了一把槍,口氣像在背誦一張購物清單。
接著他的律師請他告訴陪審團,案發當晚,他在妻子出門去和葛倫.昆汀會面之後做了些什麼。安迪如實說出……而他給人的印象糟透了。
我認識他將近三十年,我可以告訴你,我這輩子沒見過比他更沉著冷靜的人。做了好事他不會大聲嚷嚷,做了壞事他則是絕口不提。要是他曾經有過心靈的暗夜──如同詩人聖十字若望和其他作家的形容──你也絕不會發現。他是那種一旦決定自殺,就會不留隻字片語地去做,但是會先把所有身後事都安排妥當之後才去執行的人。如果當時他在證人席上落淚,或者聲音哽咽、態度變得猶豫,甚至開始對著那位有意進軍國會的檢察官大吼,我不相信他會像最後結果那樣被判處無期徒刑。就算被判刑,也應該會在一九五四年得到假釋。問題是,他像錄音機那樣敘述他的案情,彷彿在對陪審團說:事情就這樣了,要不要採信隨便你們。結果他們沒有採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