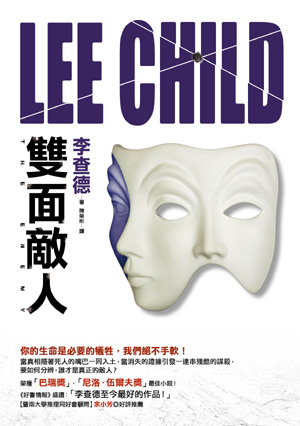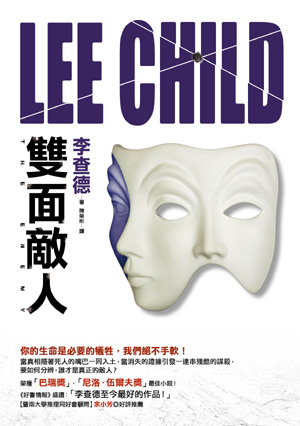內容試閱
這就是心臟病發作嗎?當肯恩.克拉瑪停止呼吸、意識陷入一片死寂之際,也許這句話就是他的遺言,在臨終前他心頭浮現的是一陣恐慌。他玩火玩過頭了,不管就哪方面來講都是這樣,他自己也心知肚明。他不該來這是非之地,不該跟這個人在一起,也不該把這原本應該藏好的東西帶在身上。但他本來已經確認自己安全無虞,在這遊戲裡穩操勝券、占盡上風。他臉上可能露出一絲微笑──直到胸口的重重一擊把他打垮。接下來局勢完全逆轉,原本的勝利變成一場災難,他沒有時間補救任何事情了。
致命的心臟病到底給人什麼感覺?沒有人知道,因為病發的人都死了。醫護人員的說法是:細胞壞死、血液凝固、缺氧致死以及堵塞的血管。他們猜想:心臟會迅速跳動,但卻沒有用,或者連心臟都已經動不了了。他們用的字眼通常是心肌梗塞或心室顫動,但這些對我們來講都沒有意義。其實他們只要說一句話就好了:「反正就是癱倒然後死掉。」肯恩.克拉瑪一定是這樣,他剛剛癱倒死去,許多祕密隨他逝去,但是他留下的麻煩幾乎把我害死。
我自己待在一個借用的辦公室裡。牆上有鐘,只有時針跟分針,沒有秒針,是個不會滴答作響的電子鐘,它靜的就像這房裡的死寂一樣。我故意看著分針,它並未移動。
我等待著。
針動了,它往前跳動六度,這小幅的移動充滿了機械的精準度。它彈了一下,稍稍抖動之後又恢復停滯。
一分鐘了。
過了一分,還有一分。
再六十秒就到了。
我盯著看,時鐘停滯的時間似乎好久好久,然後分針又跳動了六度。又過了一分鐘,已是午夜時分,一九八九年變成了一九九○年。
我把椅子往後推,在桌後站起身來。電話鈴響,我猜是打來祝我新年快樂的。但卻不是,是個警察打來的,因為在他轄區裡有個軍人,死在距離部隊三十哩外的汽車旅館裡。
他說:「我要找憲兵執勤軍官。」
我又在桌子後坐下。
我說:「我就是。」
「這裡死了一個你們的人。」
「我們的人?」
他說:「是個軍人。」
「哪裡?」
「鎮上的汽車旅館。」
我問:「怎麼死的?」
那傢伙說:「很有可能是心臟病。」
我頓了一下,把陸軍的制式桌曆從十二月三十一日翻到一月一日。
我說:「沒有疑點嗎?」
「看不出來。」
「你看過死於心臟病的屍體?」
「多得是。」
我說:「好,打給部隊的指揮部。」我把號碼給了他,我說:「新年快樂。」
他說:「你不需要來一趟嗎?」
我說:「不需要。」說完就把電話掛掉。
我不需要去。像陸軍這種龐大的組織,人數比達拉斯小一點,比底特律多一點,說到「公事公辦」的精神,則是跟前兩者都一樣。目前軍隊總員額是男女加起來總共九十三萬人,他們的組成可以說就是美國全體國民的縮影。美國國民每年的死亡率大概是千分之八點六五,而在沒有戰事爆發的情況之下,軍人的死亡率並不高於或低於一般民眾。整體而言,他們比一般人口年輕,體能狀況也較好,但是他們抽的菸和喝的酒都較多,吃得較差同時壓力較大,訓練時還必須做各種危險的事,所以他們的壽命跟一般人差不多,死亡率也沒多少差別。就目前的兵力,如果用這種死亡率來計算,一年裡每天會有二十二個軍人死掉,死因包括意外、自殺、心臟病、癌症、中風、肺病以及肝腎衰竭等等,跟底特律或達拉斯的市民沒什麼兩樣。所以我不需要去一趟──我是個憲兵,不是個禮儀師。
分針又動了,它往前跳動,彈回來後又停滯下來。現在是午夜過了三分。電話又響了,這次是祝我新年快樂的人──我辦公室外面那位中士。
她說:「新年快樂。」
我說:「也祝福妳。妳不能起身探頭進來就好了嗎?」
「那你不也可以探頭出來嗎?」
「剛剛我在講電話。」
「誰打來的?」
我說:「沒什麼事,只是有人沒辦法活到九○年代。」
「要喝咖啡嗎?」
我說:「當然好。為什麼不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