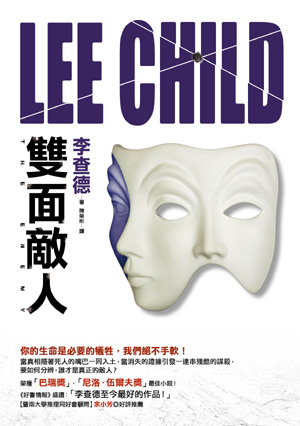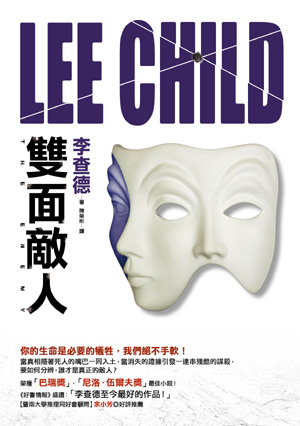內容試閱
我又把電話放下。當時我已經進部隊六年多了,陸軍的咖啡是讓我樂意繼續服役的原因之一。無疑的,那是世上最棒的咖啡。陸軍的士官們,同樣也是最棒的。像這位女中士,她的故鄉是北喬治亞州的山區。我才認識她兩天,知道她離營時都住在北卡羅萊納州一處不毛之地的拖車公園裡。她有個小男嬰,她把他的一切都告訴我,但沒提過她有個丈夫。她全身都是骨頭與肌腱,身體就像啄木鳥的嘴一樣堅硬,但是她喜歡我。我看得出來,因為她幫我倒咖啡,如果有人不喜歡你,是不會幫你倒咖啡的。他們只會在背後捅你一刀。她開了我的門走進來,拿著兩個馬克杯,我們一人一杯。
我又說了一次:「新年快樂。」
她把兩杯咖啡都擺在我桌上。
她說:「真的會快樂嗎?」
我說:「好像沒什麼值得不快樂的理由。」
「柏林圍牆塌了一半,我在電視轉播上看到的,大家瘋狂慶祝著。」
「很高興這世界上還有人在某個角落慶祝。」
「人很多,一大群唱歌跳舞的人。」
「剛剛我沒看到這則新聞。」
「那是六小時前的事了,因為時差。」
「人可能還沒散呢。」
「很多人帶了大榔頭去。」
「那是政府開放的,那半邊是個自由的城市,四十五年來我們一直把它保持在這種狀態。」
「很快我們就沒有敵人了。」
我嘗一口咖啡,熱熱的黑咖啡,世間極品。
我說:「我們贏了,那不是好事嗎?」
「如果你是靠美國政府吃飯的人,可不是個好消息。」
她跟我一樣都穿著標準的叢林迷彩戰鬥服,袖子平整地往上捲。她的憲兵臂章戴得服服貼貼,我想她在內側用了安全別針固定臂章。靴子也微微發亮。
我問她:「妳有沙漠迷彩裝嗎?」
她說:「沒待過沙漠。」
「上面的紋路被改過了,加了一個個棕色的色塊,花了五年時間研究才改的。步兵那些傢伙說那叫做巧克力條。那紋路不好,以後一定會改回來的。但是他們又要花五年時間才能想通這一點。」
「所以呢?」
「如果軍方高層要花五年才搞定迷彩裝紋路修改的事,那麼裁軍這件事要花他們多久時間?到時候搞不好妳兒子都已經大學畢業了,所以妳就別擔心了。」
她說:「嗯。」但口氣裡還是不相信我。她接著說:「你覺得他是一塊讀大學的料?」
「我沒見過他。」
她不發一語。
我說:「陸軍討厭改變,而且我們永遠不缺敵人。」
她還是不發一語。我的電話又響起,她趨前幫我接電話,聽了大概十一秒之後才把話筒交給我。
她說:「長官,是蓋伯上校,人在華盛頓。」
她把自己的馬克杯拿走後就離開房間了。蓋伯上校是我最上頭的老闆,儘管人還不錯,但他不太可能在跨年夜的午夜零點八分打電話,只是為了跟我說新年快樂,他不是那種人。有些高官會做這種事,一到假日特別來勁,就像自己是個小男孩似的。但是里昂.蓋伯完全沒想過嘗試這種事,對其他人都不可能,對我就更不用說了。即使他知道我在這裡,也不會這麼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