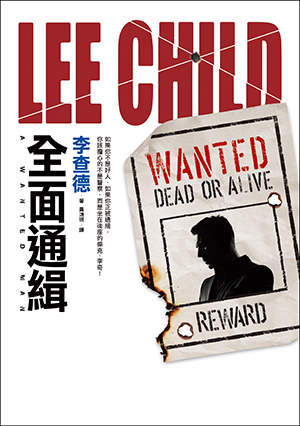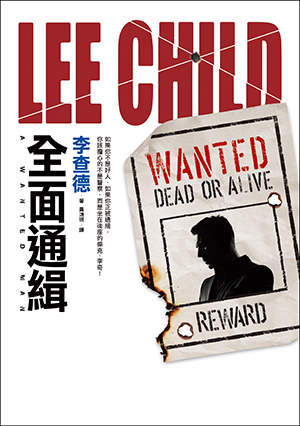內容試閱
2
那輛車在他前方三十英呎處停下。車子掛的是本地車牌,大小適中,美國車,暗色系烤漆。是雪佛蘭,李奇心想,烤漆顏色可能是深藍、灰或黑,在水銀燈下很難判斷,暗色系金屬在夜晚總是具備隱匿性。
車上有三個人,前座兩男,後座一女。兩人轉身面對後座,似乎在進行盛大的三方會談,感覺很有民主精神。我們該不該載這個老兄一趟呢?這讓李奇覺得這三人似乎不是很熟。如果他們是好友,應該可以靠直覺做出決定。他們也許是職場上的同事,彼此沒有上下關係,接下來要共進退一段時間,對彼此立場過度誇張地尊重,尤其重視女性的權益,她是少數派。
李奇看到女人點點頭,也解讀了她的唇語:好。兩個男人轉身回頭面向前方,車子前進了。它在李奇身旁停下,副駕駛座的窗戶與李奇的臀部切齊。車窗降下。李奇彎下腰去,感覺到暖氣撲面而來。這輛車的空調正常得很,他百分之百確定。
坐副駕駛座的男人問:「先生,您今晚要去哪呢?」
李奇當過十三年憲兵,接著靠臨機應變討生活,也差不多十三年了。他在這兩段時期內都是靠「保有適度的謹慎與戒心」才存活下來,五感隨時開放。先前他幾乎都是靠嗅覺決定自己要不要搭便車。有沒有聞到啤酒、大麻、波本威士忌呢?不過此刻他什麼也聞不到,因為鼻樑在不久前斷了,血塊與腫脹的組織堵住鼻腔。也許他的隔膜已產生永久性的偏移,此後再也聞不到氣味的可能性著實存在,他感覺得到。
在這種情境下,觸覺不在選項之中,味覺也不在,就算像個瞎子亂抓、亂舔一通,他也掌握不到什麼情報。如此一來,他就只剩視覺和聽覺可以倚靠了。他聽著副駕駛座上的男人以中性的口吻說話,腔調沒有方言色彩,抑揚頓挫的語調透露出他受過良好的教育,整個人散發出握有權力、有管理經驗的氣質。這三個人的手都很柔嫩、沒長繭、肌肉並不發達,頭髮修剪整齊,膚色並不黝黑。大多時間都像待在室內,坐辦公室的。不是公司中位階最高的三個人,但也遠離基層了。他們看起來四十多歲,人生可能已過了一半,不過職涯已剩不到一半。以陸軍來譬喻的話,他們就像中校,確實有一番成就,但不是超級巨星。
每個人都穿黑褲、藍色丹寧上衣,感覺像制服。上衣看起來又新又廉價,剛拿出包裝袋不久,皺皺的。李奇猜他們剛參加完凝聚團隊向心力的那種活動,大企業愛玩的鳥把戲:叫幾個中階主管離開他們服務的辦公室,飛到荒郊野外集合,給他們幾件衣服穿,再指派幾個任務。也許他們手忙腳亂後可以激發出了一點冒險精神,所以才決定載他。也許他們之後還會進行同儕評比,所以才費心地進行三方會談。團隊需要團隊工作,團隊工作需要意見一致,而意見一致不能在受迫的情況下達成,況且性別議題總是很敏感。事實上,李奇發現那名女性沒坐在副駕駛座或駕駛座時有些意外。不過,「叫三人當中的一個女性開車」有可能被視為一種貶低,就像端咖啡一樣。
他們踩在一片地雷原上。
「我要往東走。」李奇說。
「到愛荷華?」副駕駛座上的男人問。
「通過愛荷華,我要一路到維吉尼亞去。」
「上來吧,」男人說:「我們載你一段路。」
女人坐在副駕駛座後方,所以李奇必須繞過車尾,從駕駛座那一側上車。他在後座椅墊上調整好坐姿,關上門。女人有點害羞地向他點頭示好,也許是有點戒心吧。可能是因為他的鼻樑害的,或是他的外表。
駕駛座上的男人透過後照鏡瞄了他一眼,接著開上匝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