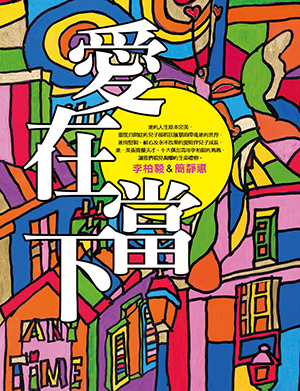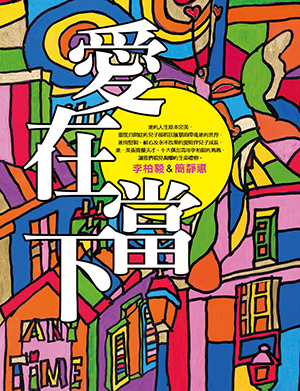內容試閱
●當他們長大成年
我經常思索一個問題,究竟是自閉症的人辛苦,還是他們的家人?
那一天,我一直提心吊膽的事終於發生,柏毅不見了。
他去板橋台藝大上課,正在等車回家時,伴讀臨時接到電話,稍稍移動了位置講話,柏毅一轉頭沒看到人,也不懂得問,不懂得找,或者留在原地等待,他的直覺雷達告訴他,走,自己走回家去。
他就開始走,從板橋走到華翠大橋,從艋舺大道走到中華路,從中華路走到仁愛路,最後走回家。從下午走到天黑,走了五個小時,二十多公里路。
我這一頭,一接到伴讀的電話,就立刻報警,親朋好友總動員,聽說廣播電台播出了這一則「明星第三代」的新聞。
那五個小時,對我來說就像五個世紀的煎熬,我禱告,禱告,再禱告,只祈求柏毅平安。
當他走到店裡,出現在我面前那一刻,我忍了五個小時的淚如暴雨狂洩。
我問他怎麼認得路?
「上帝帶我回家。」他說。
那晚半夜我甚至接到恐嚇電話,說你的兒子在我手上,拿贖金來。
我怎麼能夠不保護柏毅呢?
會有一天,我再也不能保護他,在這一天來臨之前,我必須盡可能訓練他獨立的能力,為他找到可信任也愛他的「保母」,但不會讓他孤獨一個人走下去。
沒有人可以替代母親,母親終究不是神。
我必須趁著還有力氣,還走得動的時候,多帶他到處去玩,去看,去嘗試,我喜歡看他開心的樣子,笑的樣子,為換取那樣純潔無邪的笑容,我願意付出一切所有。我是單純的媽媽,當每一個人都反對,說這樣不行那樣不對時,我還是傻傻地做,傻傻地往前走,我相信單純的力量,會獲得神的眷顧。
但我不知道柏毅還能畫幾年,不知道明年他還是不是有名,有沒有人邀他展畫,我只知道,不管他會不會畫,是不是藝術家,有沒有人欣賞他的畫,我永遠是他的母親,對他的愛是無條件的。
全世界都一樣,自閉症的家人,都有山高海深的苦,盼望不到天明的辛酸,但我們仍然各自努力。當我們絕望,說要放棄的時候,其實是在求救,尋找支撐下去的力量。
《Far from the tree》一書中提到一個故事,一個母親為了訓練自閉症兒子,她日復一日,把自己修練成為大學生、研究生都必須來跟她學習的專家,當她把兒子訓練到終於能夠上學,交給學校後,便倒下了,檢查之下,發現癌細胞已經擴散全身。她在病床上接受作者採訪。
美國有一個統計,兒童非自然死亡案件中,有一半是父母所為,這一半中的一半,他們的孩子有自閉症。
真相很殘酷,但不能不面對。
很多電影或電視劇裡都喜歡穿插一個自閉症角色,但這似乎不能增加社會大眾對自閉症的了解,最負面的狀況是帶動「正常人」去模仿自閉症,引起滿場大樂。
自閉紀錄片更逼近真實。
林正盛的紀錄片《一閃一閃亮晶晶》,紀錄柏毅在內,四個有繪畫天賦的自閉症孩子和他們的家庭,一年多的拍攝,長時間的接觸,林正盛導演丟出一個另類思考:
「這些特別的孩子和大多數號稱正常人所規範建構的這個世界,存在著怎樣的關係呢?難道只因為他們是那麼的不同,那麼的異於我們為數眾多的正常人,因而我們就以習以為常的行為模式、社會生活方式去要求他們,說是『為他們好』的教導他們,要他們融入我們正常人建構規範起來的生活方式。」
「然而,是否可能一不小心就同時導正了他們與生特有的言語、行為、思考、感情表達方式,導正掉了屬於他們跟這個世界特有的互動方式,最終導正掉的是他們對自己生命存在的價值……無法以他們與生俱來特有的生命狀態,去煥發出他們的生命光采。」
林導演看到的比較是高功能自閉症。
沈可尚《遙遠星球的孩子》深入自閉症患者內心孤獨的世界,讓觀眾正視自閉症患者難以和外界溝通,經常被誤解的問題,獲得二○一三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的《築巢人》則延續自閉症議題,把鏡頭轉向照顧者,自閉症者的父親,它呈現自閉症患者的黑暗面,片中三十歲的陳立夫,他有蒐物癖,收集各種廢紙、磚瓦和蜂巢,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自言自語,憤怒時會拍桌子,對父親爆粗口,甚至暴力相向。六十歲的父親陳鴻棟,一開始他決定以「家庭的溫暖」盡父親的責任,但經常力不從心,心力交瘁,「我終究不是有那種偉大性格的人」,「我們終究是一般人」,「我可不可以放棄」,這些都是他面對鏡頭說的話。
沈可尚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他因此沒有辦法在片尾時配上溫馨的音樂,給一個感人的結局。
每一天我們都要面對新的挑戰,都在戰鬥。
我們需要更多的同理心,更多的理解,以及更多的資源,一條讓自閉症的孩子在長大後,可以繼續走下去的路。
希望每一天,我與所有自閉症者的父母,我們都要微笑著醒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