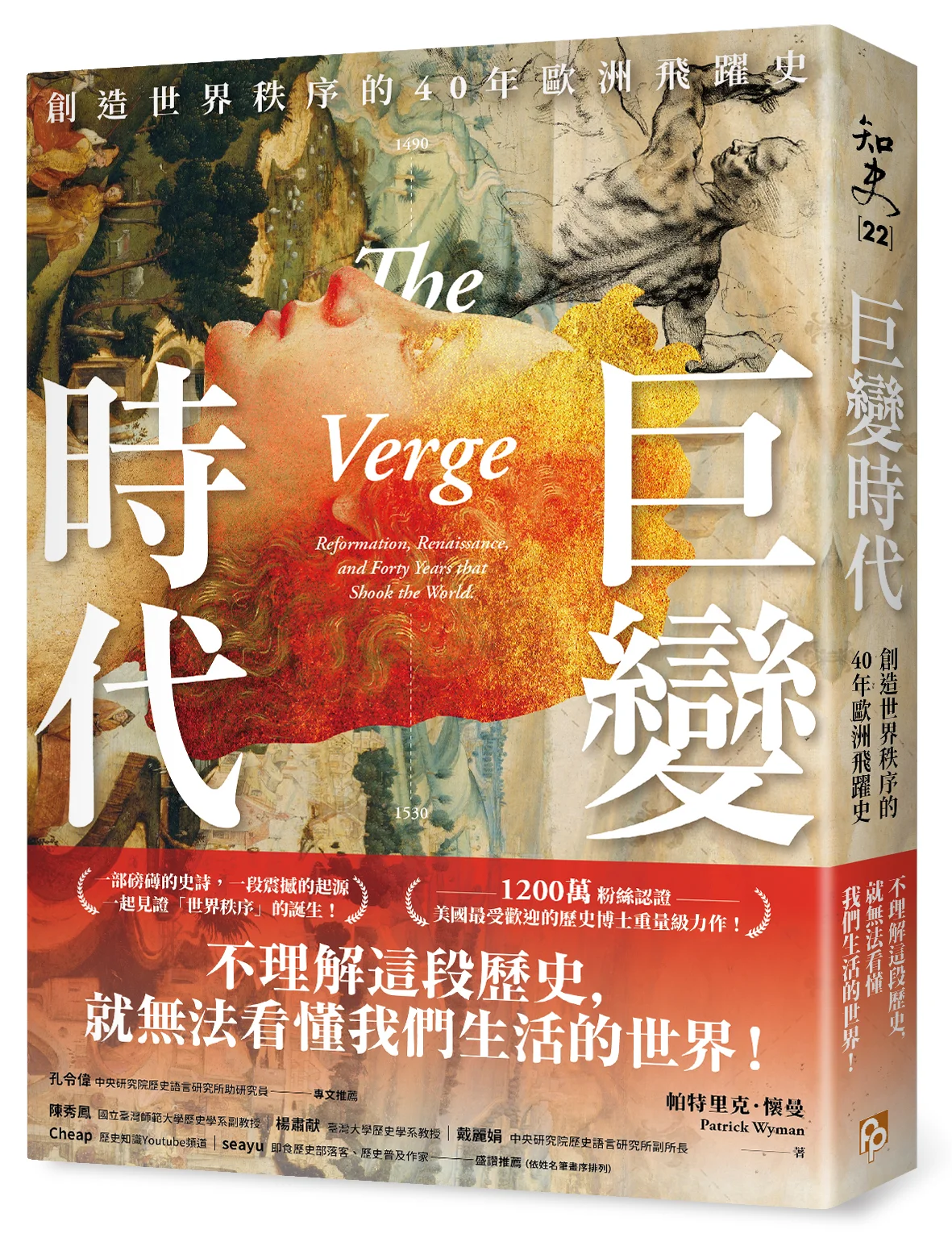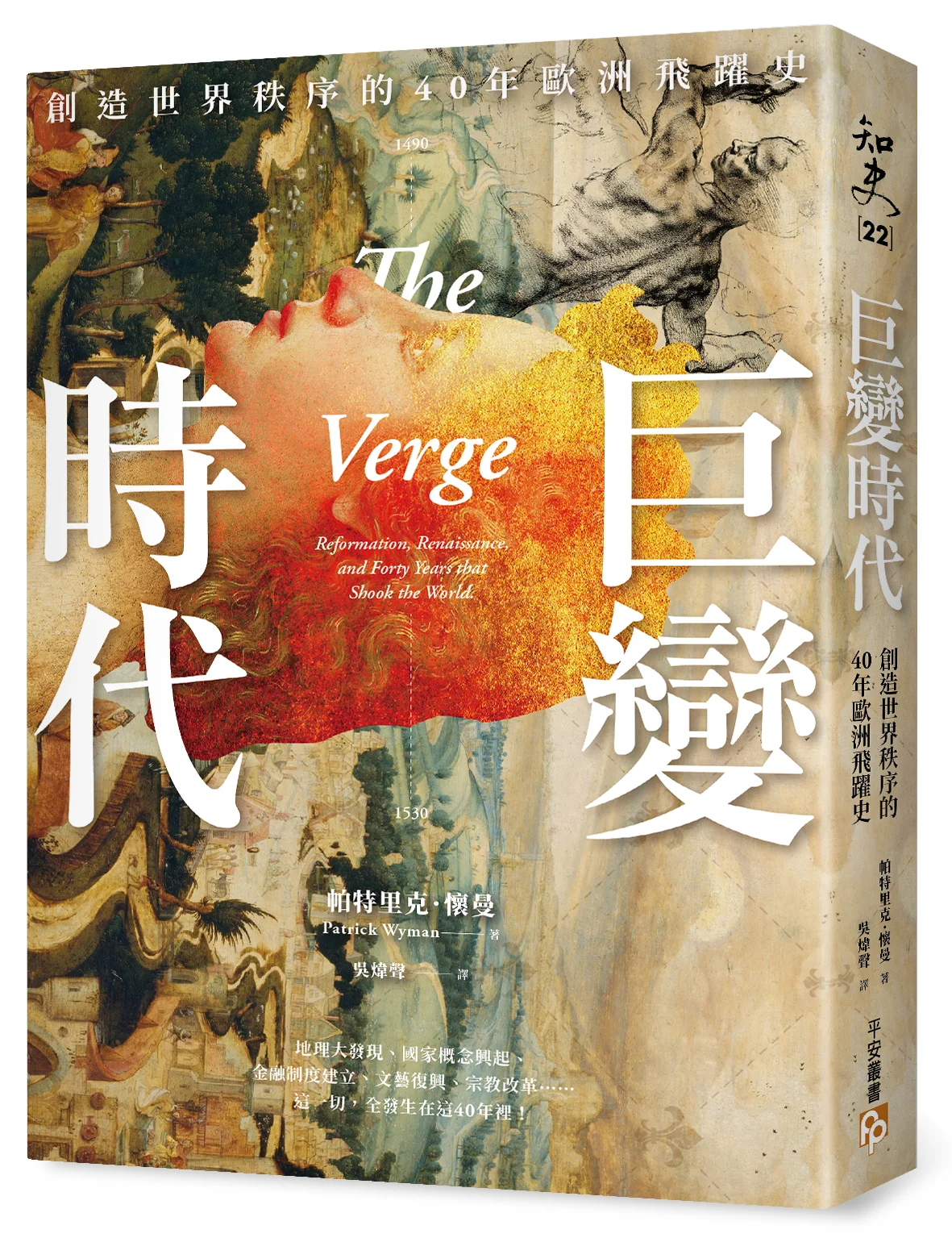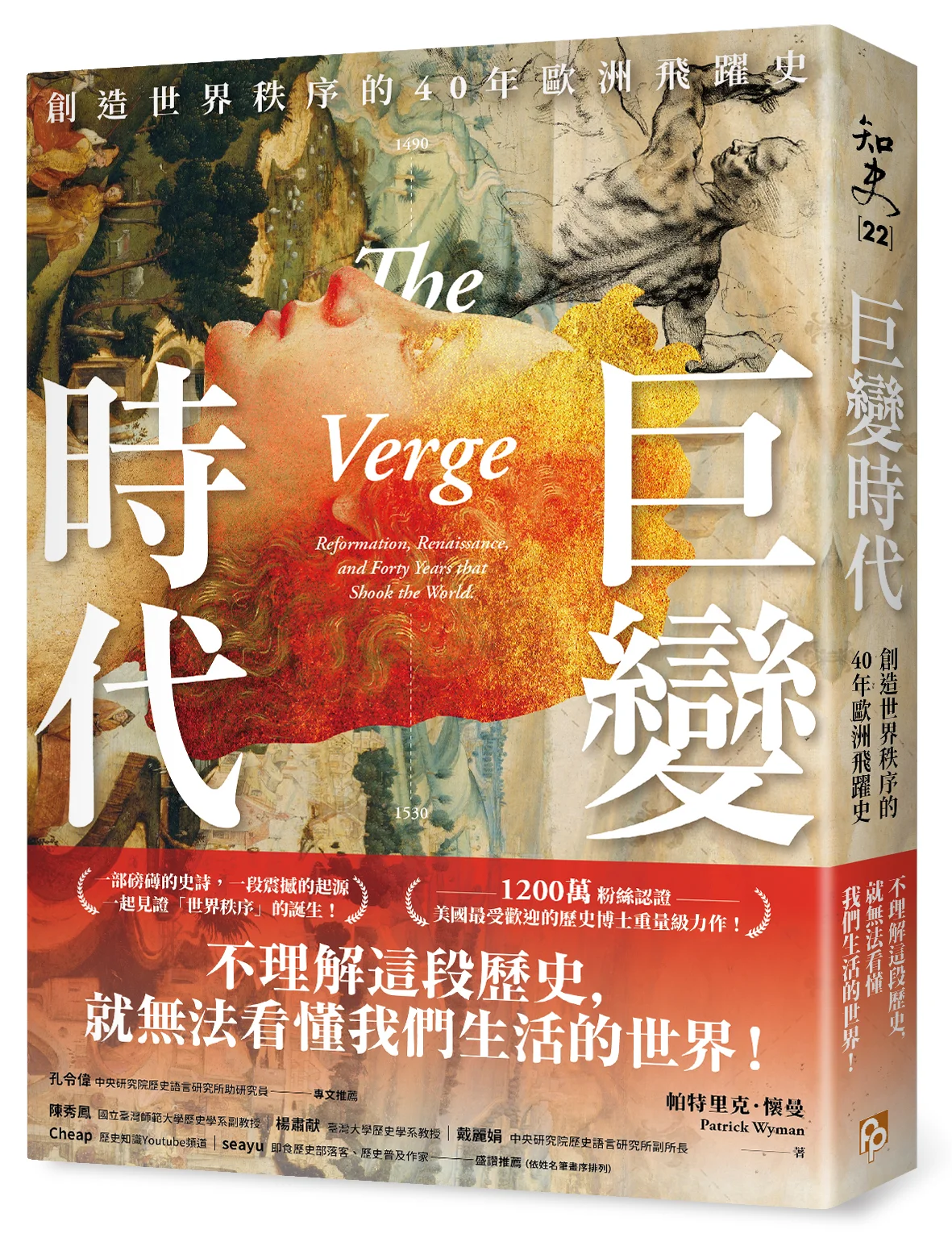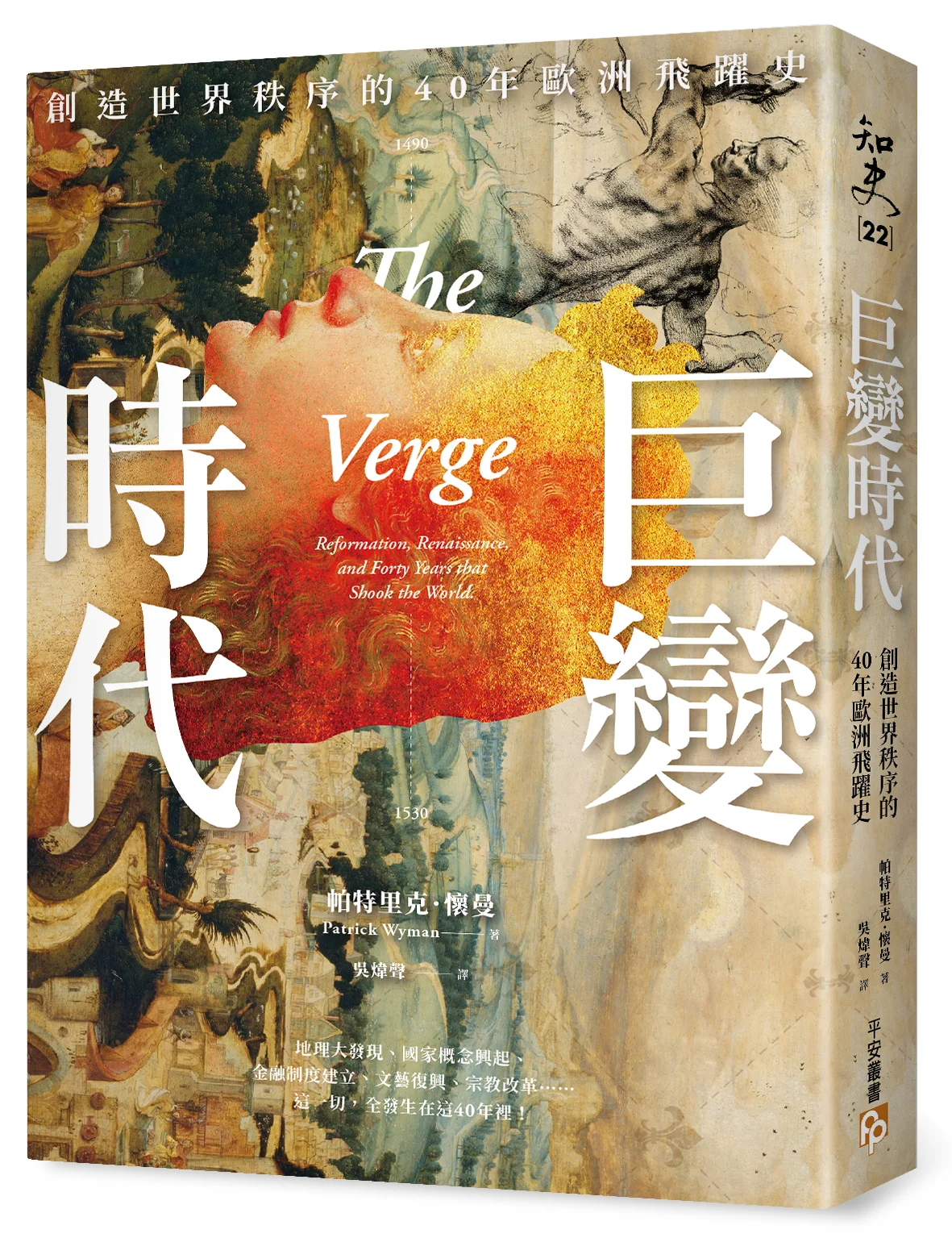內容試閱
入夜之後,火焰照亮了羅馬,顯現駭人的恐怖場景。聖伯多祿大殿(St. Peter’s Basilica,又譯聖彼得大教堂)的高壇周邊屍骨堆疊,枕骸遍地。一群西班牙士兵在城內逮到了一名威尼斯居民,便一片一片拔掉他的指甲,逼那人說出他將寶物藏匿於何處。還有居民見到士兵闖入家裡,嚇得開窗跳樓逃命。一群西班牙士兵從某間廢棄的商店中發現戰利品,但不願意跟另一批德意志僱傭兵分享,德意志人便立即將西班牙士兵反鎖在店內,然後放一把火,將店鋪燒個精光。水溝裡混雜著鮮血和泥土,戰士一發現目標,就踩著成堆的屍體前行,不斷四處掠奪。
黎明終於來臨,日光照亮了羅馬,但見城內燒殺搶奪,血腥暴力處處橫行。
德意志僱傭兵中同情路德信徒的兵丁並未放棄宗教清算的機會。一群人看見某位年長牧師拒絕讓一個傻瓜領聖餐,便衝上去宰了他。另有一批人拖著一位親帝國的紅衣主教穿過街道,即便這位主教曾不斷與教宗發生爭執,支持他們名義上的僱主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有個人還是趁機毆打了他。其他人則踐踏聖餅。路德派火繩槍手以聖物為標靶,用鉛彈射擊華麗的聖骨盒和作成木乃伊的聖人神聖頭顱。他們掠奪城內的眾多教堂,四處搜刮財寶,並將作古已久的死人遺骨傾倒在街道上,骨駭堆積如山。聖伯多祿大殿的眾教宗陵墓被撬開,腐爛的軀體被扔到剛死難者的屍身之間,這些亡者還流淌著鮮血,染紅基督教世界最神聖之地的瓷磚。騎兵最後將聖伯多祿大殿當作馬?。基督教世界有兩件最神聖的聖物,一是聖安德肋宗徒(Saint Andrew)的頭顱,二是聖婦勿樂尼加(Saint Veronica)的白帕,這兩件東西都被扔進陰溝。僱傭兵還到各處修道院搜刮數個世紀以來信眾虔誠捐贈的寶物。
教宗克勉七世曾特派葡萄牙大使去謀求和平投降,結果大使的宮殿也慘遭洗劫,他被拖到街道上剝掉衣物,最後只剩下馬褲。立誓過貞潔生活的修女慘遭販賣,一人僅值一枚硬幣。四處搶劫者放過銀行家,尤其是德意志人,因為他們可以給囚犯貸款,讓他們贖身。即便兵丁洗劫,局勢混亂,金錢的轉帳與交易仍不可或缺。
瘋狂燒殺搶奪三日之後,剩餘的帝國指揮官開始管控麾下的兵將。有數千人死亡;估計死者介於四千到四萬不等,真實數字可能落在中間。受傷人數更多。城內每個家庭的女性幾乎都慘遭姦淫,連羅馬精英家庭的婦女也難逃毒手。
某位評註者寫道:「景象十分慘烈,地獄都沒那麼恐怖。」基督教世界的萬般財富如今都落到一群卑劣饑渴且欲求不滿的僱傭軍手裡。教宗克勉七世只能躲藏在聖天使城堡,眼睜睜看著自己淪落而悲痛萬分:他不再是基督教界呼風喚雨人物之一,很快就會成為皇帝的俘虜而任其擺佈。
這場肆無忌憚的恐怖暴行是如何發生的?為何成千上萬的士兵要洗劫教堂、囚禁人犯加以折磨、掠奪房屋和宮殿,並且犯下強姦、謀殺和其他令人髮指的罪行,只為了讓全世界最神聖且最富有的城市垮台?
羅馬之劫(Sack of Rome)似乎難以想像,完全顛倒是非,搞得世界天翻地覆。羅馬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重鎮,更是歐洲的文化與宗教中心。錢財從歐陸各地流入教宗的金庫。在斯堪地那維亞簡陋的木造教堂與法國高聳的哥德式大教堂所收取的什一稅(tithe) 最終都運往羅馬。現在教宗被貶低了,財富被卑微的士兵侵占,城市不再宏偉壯闊,舉目所見,屍橫遍野。
這是一波波動亂遽變的高潮,匯聚眾多毀天滅地的過程之後所導致的苦果。由於航海探險,那位大使才得以代表富有的葡萄牙國王,查理五世皇帝仰賴新大陸(New World)的財源,方能集結軍隊出征。此外,各國國力逐漸提升,能投入愈來愈多的資金,軍隊火力也日漸強大,戰爭因此改觀,破壞力愈來愈強,規模逐漸擴大,持續的時日也愈長。印刷機顛覆了訊息世界,傳播足以激怒眾多德意志士兵的路德教派思想,而這一切並非巧合。
在短暫的四十載(相較之下,這僅是一眨眼的時間),歐洲便爆發危機。大約在一四九○年,亦即羅馬淪陷前四十年,歐洲僵固落後,猶如一潭死水。按照歐洲的標準,巴黎、倫敦、巴塞隆納與威尼斯都令人印象深刻,但當時尋訪人類最高成就的異域遊客會更想前往君士坦丁堡或北京旅行;若想反其道而行,則會去體驗特諾奇蒂特蘭(Tenochtitlan) 、印度德里、開羅或中亞撒馬爾罕(Samarkand)等城市的魅力。
與此同時,歐洲獨處一隅,乃是歐亞大陸邊緣的前哨站,屬於經濟和政治的邊緣地區,與生機蓬勃、不斷擴張的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或歷史悠久的中國明朝相比,則顯得平庸落伍。任何有理智的賭徒都不會下注去賭歐洲是全球龐大殖民帝國的起源地,更不會認為歐洲將興起工業化,於後續數百年徹底翻轉世界經濟。然而,到了二十世紀初期,歐洲及其直系後代美國以前所未見的方式主宰了國際事務。到了一五二七年,當神聖羅馬帝國士兵在羅馬掠奪戰利品,那個未來已經開始形成。
大分流
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的現象將西歐從邊緣地區轉變為世界秩序的絕對中心。在荷蘭和不列顛 帶頭下(亦即大分流之前的小分流﹝Little Divergence﹞),歐洲首先艱辛且緩慢超越最強悍的競爭者,爾後瞬間爆發活力,於技術成就、政治權力和經濟生產層面遠遠拋開對手。歐洲崛起之後衝擊全球,主導了過去半個千禧年的歷史進程。倘若不研究這些過程,便無法全盤理解我們的世界:時至二十一世紀,從貿易和經濟發展模式到體育和娛樂,處處可見殖民主義與歐洲霸權遺留的影響。
只要回顧一四九○年的歷史,絕對料想不到未來局勢會如此轉變。試想當年的歐洲:克里斯托弗.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經驗豐富,多年馳騁大西洋海疆,戮力朝西航行,付出無數心血,最終卻付諸東流。馬丁.路德當時七歲,難以想像他日後將讓基督教世界徹底分裂。印刷術剛問世,人們在西歐各地大量印刷書籍,數量之眾,等同於專業抄寫員製作的手抄本。數個世紀以降,人們偏好構築薄壁城堡以自衛,然火藥發明之後,攻守易位,圍城之軍不再弱勢,這類城堡遂日漸過時。話雖如此,全副武裝的重騎兵仍能主宰戰場。法蘭西國王查理八世(Charles VIII)於一四九四年揮師進攻義大利,但其規模相較於一個世紀前英法百年戰爭(Hundred Years’ War)的諸多戰役,落差並未太大。
羅馬之劫的前四十載,戰爭規模和強度急劇上升,戰事拖得愈來愈久,廝殺也益發慘烈,簡直駭人聽聞。義大利半島和歐洲各地,烽火連天,戰事延綿,幾無寧日,而一五二七年,亦即羅馬遭洗劫當年,乃是兵燹連年的第三十三個年頭。軍隊更為龐大,武器更為先進,所耗軍費更大幅上揚。征戰各國為此開發出更複雜的有效工具來整合資源。各國探索大西洋時,起初躊躇謹慎,只讓幾艘小船沿著西非海岸巡航,試圖獵取黃金、象牙和奴隸,爾後大刀闊斧,派遣整支艦隊,前往印度洋探險,同時整軍經武,派部隊征服剛發現的美洲。約翰尼斯.古騰堡(Johannes Gutenberg)於七十五年前發明了印刷機,此時這種機械裝置已無處不在,大量印刷各種文件,尤其是宗教宣傳品。
到了一五二七年,導致大分流的道路已露出端倪。哪怕只是一道淡淡的輪廓,尚需不短時日方能顯現,但未來世界的雛形卻逐漸清晰起來。
為何是歐洲?何時發生於歐洲?歷代鑽研歷史、政治學、社會學和經濟學的學者,念茲在茲的,便是這兩個問題。有些人曾云,真正的變革只伴隨著十九世紀初的工業革命而發生。在此之前,根據每項有意義的指標來評斷,中國與歐洲皆旗鼓相當。其他人則指出,西歐隨處可開採煤礦,歐洲各國更大肆於海外掠奪資源,犧牲了別處的利益,歐洲方能迅速崛起。
有人更進一步追溯到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認為歐洲能快速崛起,乃是具備高超的軍事技術,同時經濟實力雄厚,足以對外發動戰爭。其他說法還包括西歐(尤其是不列顛和荷蘭)具備獨特的創新文化,足以改進體制、發展政治和創造技術。對於其他觀察者而言,大分流之起源可追溯至中世紀,甚至更早的時期,能從雜亂無章的歐洲文化特徵、原型資本主義(proto-capitalist)的醞釀環境或資源分配中找到其濫觴。「深度分流」(deep divergence)思想學派提出一種更讓人信服的解釋,強調其他地區都沒有多極國家體系(multipolar state system):歐洲分崩離析,內部衝突幾乎不斷,各國隨時都在競爭,遂能在這段期間有所發展。
這些解釋和論點確有值得參考之處。直到工業革命興起,不列顛與印度和中國同等發達的地區相比,其生活水準與工資才出現分歧。然而,反過來說,工業化也絕非一朝一夕便可促成。工業發展必須基於更深的根源,問題是這些根源要追溯到多麼遙遠的年代。
本書為這兩個問題提供了一個答案,說得更準確一些,是從略微不同的角度去構建和理解它們,並非著眼於單一變數,譬如特定的創新或資源,而是探討一段波折叢生的關鍵時期,亦即一四九○年到一五三○年的四十個年頭。這段時期彈指即逝,不及人壽,但西歐卻從落後的邊緣地區搖身一變,躍升為世界強權,這一切都得歸功於一連串驚心動魄的轉變。
這些劇變並非單一過程或變數所導致,而是數個過程或變數交織影響所造成。遠航異域探險、國家擴張、火藥殺伐的戰爭、印刷機的普及、貿易與金融擴張,以及這些舉措的積累後造成的後果,比如宗教動盪、暴力橫生和全球擴張,各類因素,林林種種,複雜難測,彼此碰撞,相互作用。每一項發展皆影響深遠,而各種發展又急遽交融,遂能引爆局勢。這段時期雖然短暫,卻大幅改變了全球歷史的進程,替類似於現今世界的後續局勢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