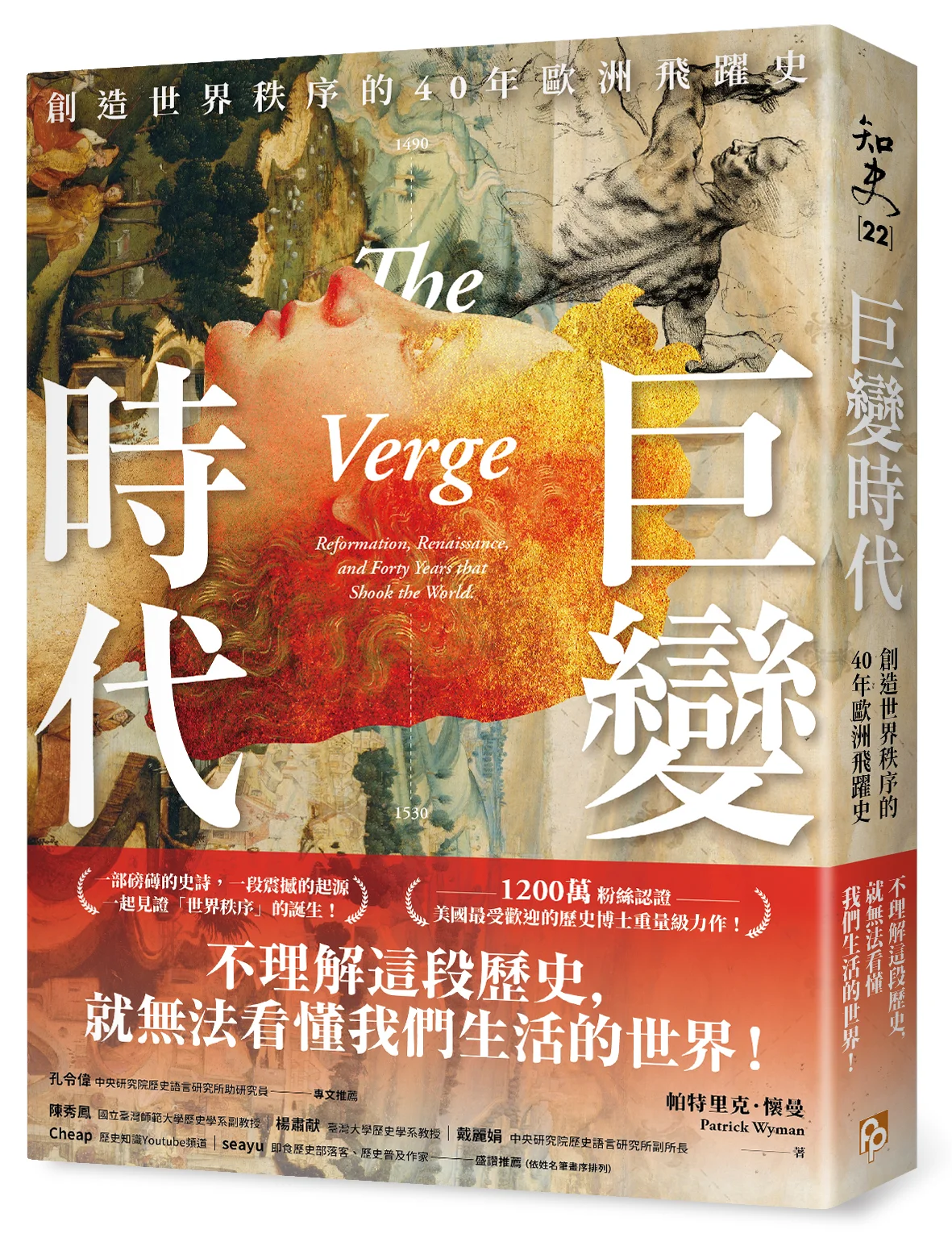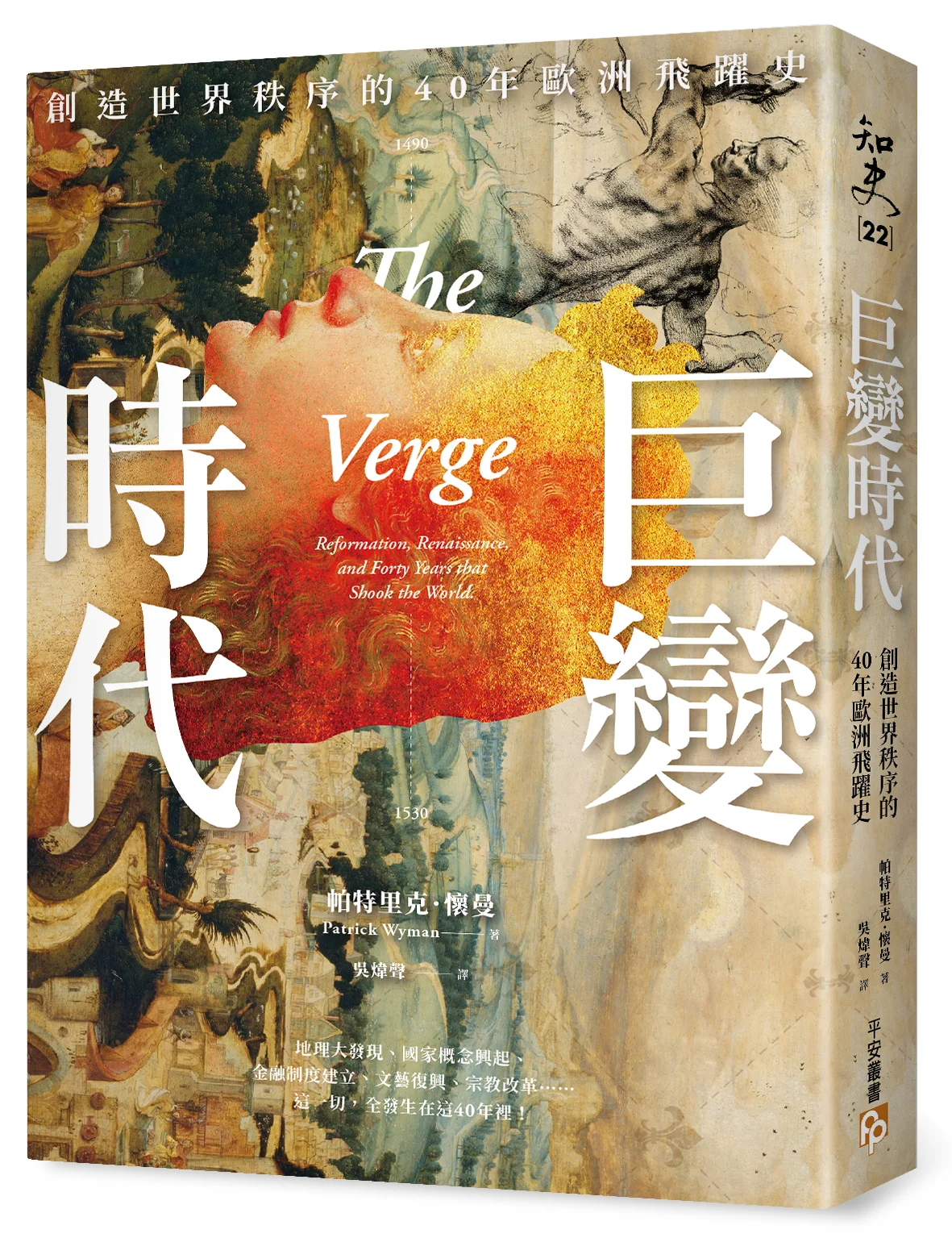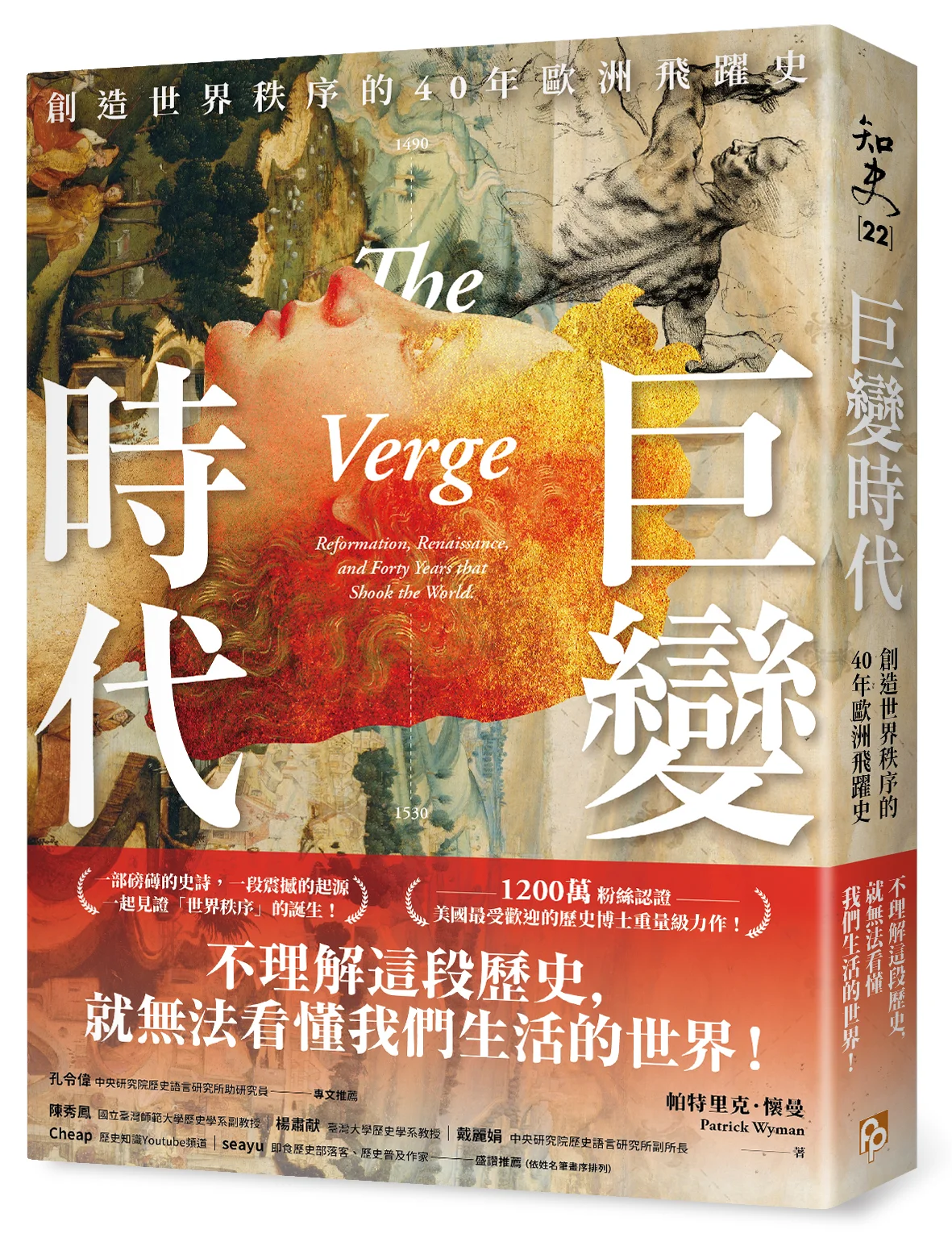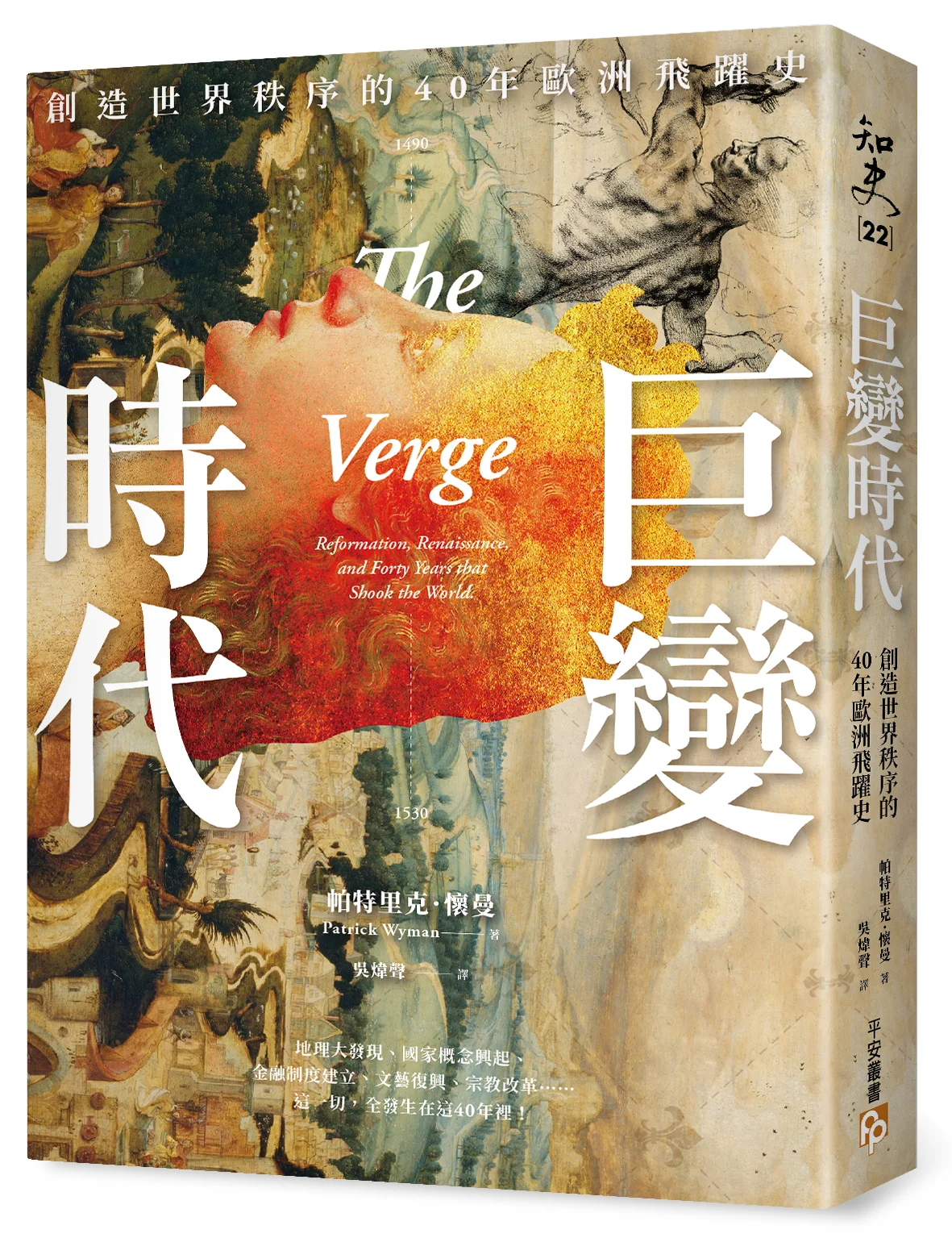內容試閱
經濟制度
這趨勢些截然不同,好比印刷機的普及和僱傭軍的使用,它們之所以能結合在一起,乃是人們對信貸、債務、貸款和投資抱持一套特殊的態度。歐洲人根據這些態度來運用資本(capital),亦即使用他們的資產。我們可以將歐洲人運用資本的方式視為經濟制度(economic institutions)。
在最基本的層面上,此處的「制度」是指對特定行業規則的普遍共識。從更廣泛的角度而言,制度超越了規則,延伸至驅使人們以特定方式行事的系統、信仰、規範和組織。制度讓人遵守規則,使規則持續下去,並且調整規則,以便有利於使用規則的人。制度有好有壞,能有益處,也能有壞處,一切都取決於具體情況。倘若在政治上表示忠誠,便以此冀望可獲得恩賜和關照(這也算是一種制度框架),如此便可能結黨營私,讓政府無能腐敗。人們在市場的行事方式、他們對交易抱持何種假設,以及企業和家庭如何互動:制度皆能影響這些事情。
放諸更廣的歐亞標準,西歐在這個時期開始時並非特別富裕。由於黑死病(Black Death,爆發於十四世紀中葉,爾後疫情反覆出現)肆虐,加之氣候更為寒冷且更難以預測,災難接二連三,歐洲人口從十四世紀初期的高峰減少了多達一半。金條供不應求。兵燹戰禍頻生,每爆發一次,便肆虐歐陸數十載,英法百年戰爭便是一例。十五世紀下半葉,主要王國幾乎深陷內亂之中。歐洲礙於這一切災禍,連續一百多年經濟萎靡不振。
到了十六世紀初期,情況開始好轉,但只是好轉而已。人口是前現代經濟增長的基礎,此時歐洲各地的人口逐漸增加。貿易又再次興盛。儘管如此,這些都算不上經濟優勢,更別說是未來主導全球的指標。
然而,歐洲此刻確實擁有一套經濟制度,非常適合用來推動每一項足以影響未來時代的主要進程,比如:出海探索、國家成長、火藥戰爭、印刷術,以及隨之而來的後果。這些皆是極其昂貴和資金密集的流程與技術,初期便需要投入大筆資金,爾後甚至需要更多金錢來持續推動。
要讓一艘船艦或整批艦隊出航大西洋探險,初期得耗費鉅資,打造船艦、供應物品,以及召募船員。在這段時期,各國無法壓榨百姓來獲取必要資金,因此需要借貸以及仰賴未來稅入的預付錢銀。借這些貸款主要用來支付規模日益龐大的火藥戰爭。戰爭是一門生意,初期花費主要由私人承包商承擔,他們靠賒欠來招兵買馬和供應軍需。印刷文件與發動戰爭或派船前往印度相比,只能算是小兒科,但也得花不少錢去添購活字、印刷機和紙張,還得具備操作機器的專業知識,方能印刷出文本,賺取銀兩。
同樣的機制和情況隨處可見,無論是投資印刷企業的成功威尼斯商人,還是象徵性付些訂金來購入羊毛的英格蘭商人,或是抵押土地去支付僱傭長矛兵簽約金的奧地利提羅爾(Tyrolean)貴族,亦或籌集現金支付熱那亞冒險家前往未知世界探險的一批西班牙貴族和投機分子,甚至是從奧格斯堡(Augsburg)銀行家借來令人瞠目結舌的大筆資金賄賂買票而當選神聖羅馬帝國皇帝(Holy Roman Emperor)的某位君王。債權人都希望能拿回借貸的資金,而根據交易的類型,若非投資能獲取報酬,便是可以收取利息。
表面上看似乎明顯不過,但其實需要一系列關於金錢和信貸本質相互關聯的假設、交易雙方對彼此的極大信心,以及足以落實交易條款的廣泛框架。債權人與債務人或投資者之間的信任,交易各方與正式和非正式當局彼此的信任,足以強制執行正式合約或非正式協議:歐洲人彼此信任借貸的交易結果,方能籌集款項,推動前述耗費鉅資的進程。這不同於相信保證有利潤的投資。借貸就有風險,投資新技術和風險事業難免會落空。然而,在這種情況下,有夠多的人相信這些共同的假設,認為它們會奏效,資本方能持續流動。
對這段時期至關重要的經濟制度與我們現今所想的不甚相同。當時的信用主要關乎個人,因此更加仰賴聲譽,而非無關個人或純屬數字的信譽衡量標準。茲舉數例,好比親屬關係、聯姻、種族和共同出身,這些皆可決定某人的信貸能力。正式體制和公共執法與一種更為私密和私人的債務關係緊密相連,金錢只屬於其中一部分;它更像是對個人、公司甚至整個社區價值的道德判斷。反之亦然,因為償付能力足以證明人的道德和社會價值。
為何發生於那時?
在十五世紀末期,這些並非歐洲全然創新的制度。其實,數個世紀以來,在更先進的商業地區和城市,好比義大利北部和低地國家(Low Countries) 的大貿易中心,人們深刻理解何謂信貸和投資,而這些地區正是建立於這些基礎之上。歐洲人也並非全球唯一會集中資本、利用複雜組織形式進行貿易或為各種名目的提供貸款的人。這些措施已經存在數個世紀之久,雖然它們曾在數千年之中出現、消失,然後又再次出現。從羅馬到中國,從公元前一世紀到中世紀末期,人類想方設法經商貿易,運用直接資本去拓展業務。以此來看,十五世紀的歐洲人並非獨特出眾,無人能出其右。
然而,有幾件事是不同的。首先,這些經濟制度在西歐幾乎無處不在。不少人群往來密集的通訊、流動和貿易樞紐帶將這個地區緊密聯繫起來。貨物、人員和思想(包括影響信貸取得與運用的經濟制度)都能藉由四通八達的網絡向外流動和傳播。
很難說這些制度是否確實傳播出去,從某個地方傳揚至另一個地方,或者各地情況類似,於是採納類似方案去解決相同的問題。術語和細節會根據地區和行業而異。某些地區流通的低價值硬幣多於其他地區,表示當地民眾平時較少使用信貸。這些差異擴大了不同社會間的落差:義大利中部佛羅倫斯(Florence)的梅迪奇家族(Medici)銀行家籌組公司(從而籌措資本)的方式迥異於波羅的海(Baltic)漢薩同盟(Hanseatic)商人,或者奧格斯堡富格爾家族(Fugger)商人資本家。一群熱那亞金融家曾借錢給卡斯提爾(Castile)女王,以她皇冠上的珠寶作為擔保,這種做法有別於德意志貴族透過賒賬去募集一小批長矛兵作戰。
話雖如此,從購買啤酒和麵包的卑賤農民到承保國家財政的銀行家,這些百姓或商賈無不了解提供貸款和投資的原則。他們對於抵押、擔保品、風險和報酬的最基本假設是一致的。整個西歐的制度框架以類似方式運作,因為數個世紀以來,這種體制早已傳遍各地,深入社會各個階層,下至販夫走卒,上至王公貴族,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其次,這些制度在歐洲各地廣為傳播(或四處被人發明)是有充分道理的。這些制度在十六世紀時出現爆炸性的增長,而之前的十四世紀末期和十五世紀是它們的發展關鍵時期,因為當時鑄幣嚴重短缺。僅僅因為缺少硬幣,鑄幣廠只好關門,貨幣兌換商倒閉,商品也賣不出去。
這並非一個短暫的插曲;「金銀大短缺」(Great Bullion Famine)是十五世紀中葉經濟困頓的時期,而短缺窘境持續了數十年。白銀當時是多數歐洲企業來往交易的媒介,但礙於礦產枯竭,加上歐洲對東方的貿易逆差甚大,因此白銀尤其稀缺。歐洲出口品(主要為布料)的價值遠低於進口商品。唯一可以購買歐洲精英想要的香料、絲綢和其他奢侈品的有價物質無非是金塊/金條、黃金和白銀。從短期來看,鑄幣短缺會嚴重影響獲得信貸的機會,尤其會衝擊高端的經濟層面。沒有了硬幣,就沒人能確定投資能有成果或別人能償還貸款。結果,在整個十五世紀中葉,歐洲經濟陷入嚴重的蕭條。
然而,從長遠來看,商行企業依舊熬過這段日子。由於鑄幣短缺,歐洲人便改變對貨幣和信貸的看法。人們採用幾乎不用鑄幣的交易方式,因為這種做法早已行之數個世紀,他們如今顯得更為自在嫻熟。到了十五世紀末期,鑄幣確實增加了,但這些體制卻沒有消失;它們反而讓新流通的白銀和黃金增加了效果,創造了更多的信貸,使其流向西歐的經濟體。
第三,時機很重要。例如,這些制度並不比印度古吉拉特(Gujarat)商人集中資本或中國福建農民對土地的估價方式優越多少,只是它們特別適合那個特定時期。它們很有效率,將資金導入一連串資本密集的過程。每個過程皆已存在許久,但注入它們的資本金額卻在短時間內增長了幾個量級。當投資者認為可以從中獲利,錢就會跟著錢流動。一旦國家財政豐厚,讓貸款人認為有利可圖,此時統治階層便可借更多的錢,如此一來,其他統治者也被迫依樣畫葫蘆。當商賈沿著西非海岸航行,帶回了黃金和奴隸,其他投資者也會看到商機,於是將資金投入到更野心勃勃的商業計畫。當印刷業能賺錢謀利時,更多的資金便流入這個行業。
關鍵時刻
本書著眼於一段四十年的時間,亦即從一四九○年到一五三○年。在這段期間,愈來愈多資本透過這種經濟制度框架流入市場。隨手俯拾其中一項過程,都能算是一項重大發展:諸多學者皓首窮經數十載,甚至花費數個世紀,撰文成書或激烈探討這些過程。箇中理由不難理解。舉例而言,印刷術問世之後,隨即全面引起訊息傳遞的革命。能在人類歷史上首度整合包括美洲在內的地區來達到真正的全球化並非小事一樁。在一五○○年左右的短短數十載,這些過程彼此交織碰撞。一切並非巧合;由於資金流通,這些過程便如火如荼進展。
每個過程都能讓世局動盪不安。馬丁.路德的思想如閃電般迅速傳揚出去,不到幾年便讓宗教改革運動傳播至歐洲邊緣地區,這一切都得歸功於剛剛廣為流行的印刷機。戰爭無處不在:從一四九四年義大利戰爭(Italian Wars)到羅馬之劫隔年的一五二八年,期間至少爆發三十二場戰事,士兵恣意屠殺義大利平民,偶爾甚至傷及數千名黎民百姓。然而,義大利只是其中一處兵燹戰火蹂躪的舞台。哥倫布於一四九二年啟航橫渡大西洋,此後這類征服者陸續登陸新世界,最終導致阿茲提克(Aztec)和印加(Inca)等帝國轟然倒下。他們那一代人橫征暴斂,剝削民脂民膏,將美洲寶藏盡數傾注到歐洲的流通資財,期間還殘害許多無辜原住民。
綜觀這些發展,任何一個都足以顛覆既定的世界秩序,而且它們都是非常短的時間內同時發生。它們並非獨自發生的現象,這些過程受到相同的潛在機制驅動,彼此強化,互為作用。然後,這些過程又與一連串不可預料的偶發事件碰撞(譬如:某些人物意外出生和死亡,以及下決策時間點之類的事件),從而引發前所未有的全球反應。
那是轉型的時代,歐洲生活和社會大幅改變的年代,深刻影響世界的未來格局。我們將其稱之為關鍵時刻(critical juncture),歷時數十載,危機四伏,變化劇烈,交融匯聚,徹底改變後續事件的進程。這個關鍵時刻導致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這段激烈的變化時期過後,歐洲日後方能主宰全世界,不過從當時來看,西方統治全球的日子尚遠。綜觀這四十年,隨著(投資)報酬日益增加,投資規模也逐漸加大。當然,後續的三個世紀仍然出現不少關鍵時刻,最終方能導致工業革命。話雖如此,所有的關鍵時刻無不仰賴這一系列首次同步發生的基礎轉變。
歷史浩瀚,壯麗宏偉,這便是為何前述的四十載至關重要。然而,這也只算是故事的一半。另一半則是令人眼花繚亂、讓人惴惴不安和多事之秋的時代,也是當局者必須經歷的過程。遙想當年,那些活生生的血肉之軀真切感受大西洋的狂風從他們臉頰呼嘯而過,耳聞熙攘港口的喧鬧聲響,嗅到殺戮戰場燃燒的火藥氣味。這些古人四處征戰、飽受苦楚、彼此愛戀、遭人賤賣、務農耕作、紡織作布、成功名就和兵敗塗地,眼看著周遭世界發生不可逆轉的變化。
這些重大事件撼動了全世界,但若是沒有融入日常生活,便欠缺些許人間煙火味。為此,我挑選了九個人,讓讀者從他們身上一窺這段宏偉歷史。這些人俯仰一生,日常舉止無不體現資本、國家、戰爭和印刷等主要議題,他們既是主動驅策這些事件,卻又被動體驗它們。有些是響叮噹的大人物,譬如克里斯托弗.哥倫布、卡斯提爾的伊莎貝拉女王(Queen Isabella of Castile)和鄂圖曼帝國的蘇丹蘇萊曼大帝。其他人則是較為無名之輩,好比獨臂的德意志貴族格茨.馮.貝利欣根或頑強的英國羊毛貿易商約翰.赫里塔奇。透過這些人物的身世,可以更加了解這個時代,知道何謂利害攸關、何謂成王敗寇、何謂獲得丟失。
我們會輕易將這些改變視為積極正面的變化,將其視為浩瀚歷史長河的高潮。畢竟,這些改變直接引發了工業革命,從而締造現今的世界。人們總是輕易相信自己生活在最棒的世界,或者是相當不錯的世界。然而,若將這些轉變碾碎,融入人們(無論大人物或無名小卒)的真實生活,便能清楚看出這些轉變不一定是有益的(甚至通常是有害的),至少在他們短暫的人生歲月是如此。西方國家向外探索,結果大規模奴役百姓,為了征服異邦,不惜滅絕種族,甚至恣意掠奪整個大陸的資源。帝國崛起之後,向臣民橫征暴斂,收納資財,轉頭征戰四方,烽火連綿,無世無之,反令諸國生靈塗炭,陷入絕境。印刷術興起,引發了訊息革命,宗教改革於焉誕生,讓信徒便相互衝突,數代人攻訐殺伐,無數人因此枉死。為了創新和進步,某種程度的創造性破壞不可或缺,即使如此,破壞仍然是破壞。
不能遺忘古人付出的代價。這段重要的歷史時期奠定了諸多基礎,既有正面,也有負面,讓我們得以建構目前的現代世界;然而,資產負債表包括資產和負債,我們也該估算人類在那個時期付出的代價與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