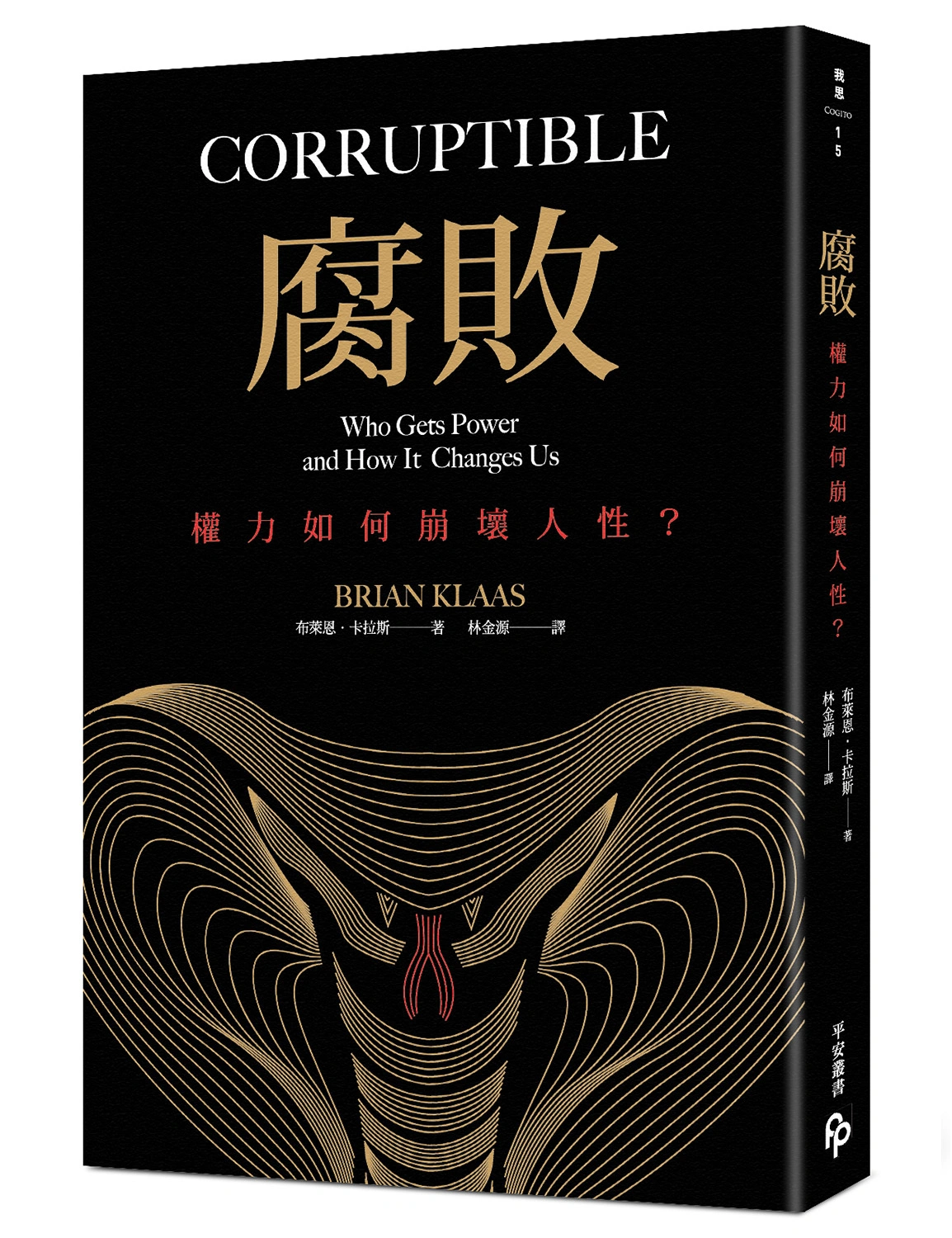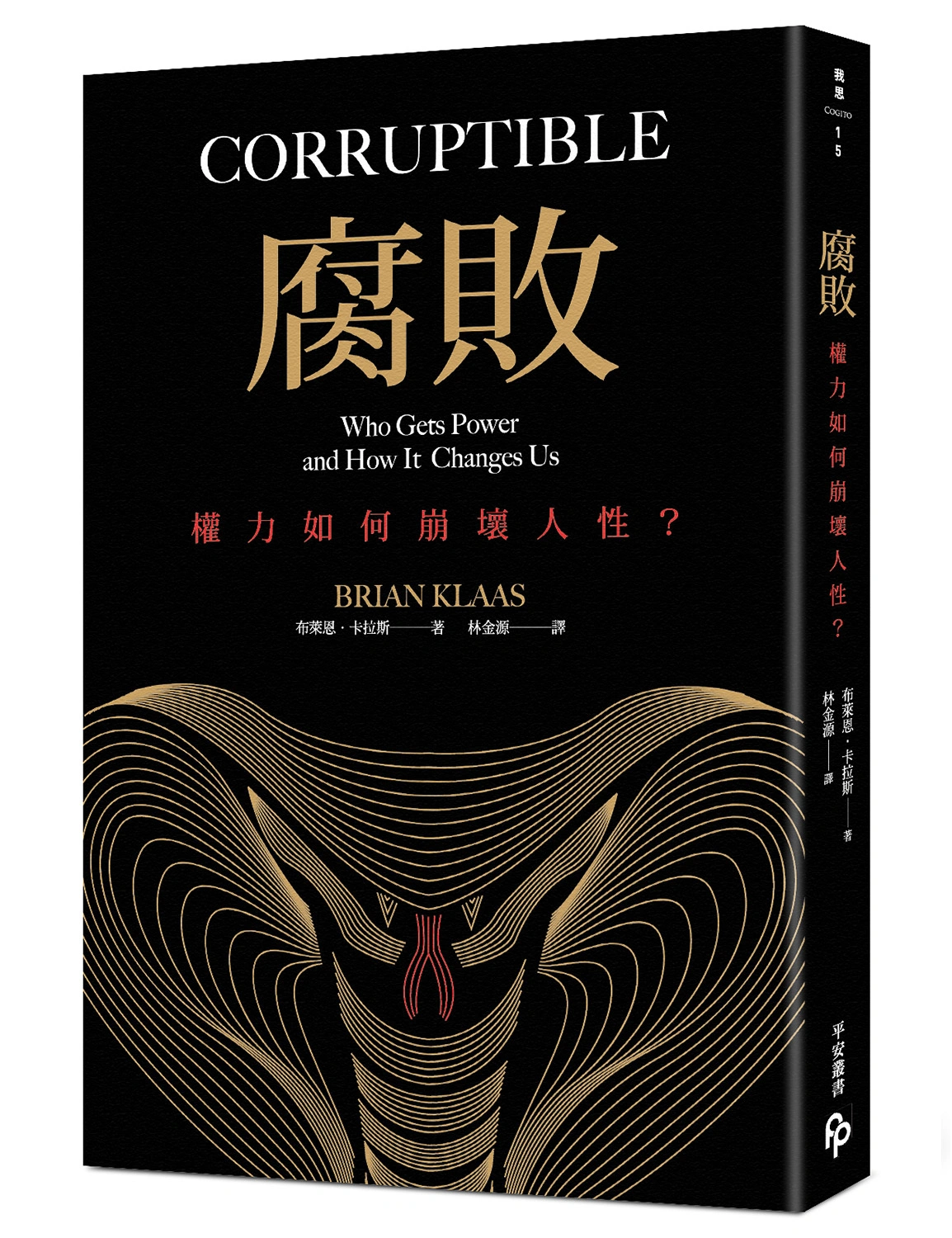內容試閱
如同荷蘭歷史學家羅格.布萊格曼(Rutger Bregman)所言,「真正的《蒼蠅王》是關於友誼和忠誠的故事,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如果能夠依賴彼此,我們會更加強大。」華納依舊定期和其中一位遭遇船難的男孩一起航海,他認為這整起事件「大大展現人性光輝」。
兩座荒島、兩種互相牴觸的人性洞察。其一,一個渴望權力的人鞏固對別人的控制,以便剝削和殺害他們。其二,講求平等的團隊合作佔上風,合作成為最高的原則。我們要如何解釋其間的差異?
燈塔島有結構、有秩序、有等級,最終釀成悲劇。另一方面,阿塔島到處是崎嶇聳立的岩石,但男孩們在十五個月裡所雕鑿出來的社會卻是一片平坦。兩個衝突的荒島故事引發不同的問題。我們是否因為壞人或壞的階級制度而注定被剝削?為什麼這世界上似乎有許多像科內利玆這樣的領導者在掌權,而像阿塔島男孩的人卻何其地少?
還有,如果你和同事被困在荒島上,你是否會推翻老闆,像東加男孩那樣平等合作來解決問題?或者像在燈塔島上,以血腥的方式奪取權力和支配力?你會怎麼做?
本書回答四個主要的問題。
第一,是否比較壞的人會獲得權力?
第二,權力是否使人變得更壞?
第三,我們為什麼讓那些顯然不該掌權的人控制我們?
第四,我們如何確保讓不會腐化的人掌權,並公正地行使權力?
過去十年來,我一直在世界各地研究這些問題,從白俄羅斯到英國、從象牙海岸到美國加州、泰國到突尼西亞以及澳大利亞到尚比亞。作為政治科學家的部分研究,我訪談了不同的人——主要是濫用他們的權力做壞事的壞人。我會晤教派領導者、戰犯、暴君、政變策劃者、刑求者、雇佣兵、將軍、鼓吹者、造反者、貪污的執行長以及被定罪的罪犯。我試著釐清是什麼讓他們發揮作用。了解他們,以及研究他們所處的體制——是阻止他們的關鍵。他們之中有許多人瘋狂且殘忍,有些則仁慈和具有同情心。但他們有一個共通的特點:他們行使巨大的權力。
當你和一個犯下戰爭罪的叛軍指揮官握手,或者與折磨敵人、冷血無情的暴君共進早餐時,你會訝異於他們鮮少符合諷刺漫畫中的邪惡形象。他們往往很有魅力,會開玩笑且面露笑容。他們乍看之下並不像怪物,但有許多確實是惡人。
年復一年,我努力想解開這些揮之不去的謎題。刑求者和戰犯是否是全然不同的類型,或者他們只是我們偶爾會在辦公室或鄰里中遇見的小暴君的極端加強版?未來的惡人是否就藏身在我們之中?在適當的條件下,是否任何人都有可能變成惡人?果真如此的話,那麼我們從嗜殺的暴君身上所學到的教訓,能否用來減少社會上較小規模的濫權問題。這是一個尤其迫切需要解決的謎題,因為當權者不斷地令我們失望。當你告訴別人你是一個政治科學家,他們接下來往往會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有這麼多糟糕的人在掌權?」
但另一個謎題持續要求我們給予解答:這些人是否因為握有權力而變得糟糕?我自己也心存疑惑。另一個可能性在困擾著我:因為權力而變得更壞的人,他們是否只是冰山的一角。或許有更龐大、更嚴重的問題潛伏在波濤下,等待被發現,等著我們去解決。
讓我們先從傳統觀念說起。每個人都聽說過「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使人腐化」這句名言。大家普遍相信這句話,但事實是否果真如此?
幾年前我走訪了馬達加斯加,那是非洲海岸外一個紅土漫布的島嶼。人人都知道馬達加斯加有可愛的環尾狐猴,但它同樣也是一個有趣物種的產地:腐敗的政治人物。馬達加斯加主要由無賴統治,他們從地球上最貧窮的三千萬人身上榨取利益。在馬達加斯加,一份拿鐵咖啡加鬆餅就得花光一般人整週的所得。雪上加霜的是,有錢人往往剝削窮人。我在那裡遇見了馬達加斯加最富有的人之一:島上的優酪乳大亨拉瓦盧馬納納(Marc Ravalomanana)。
拉瓦盧馬納納出身貧寒。為了幫助家計,五歲的他會提著幾籃水田芥,向搭火車路過學校的乘客兜售。某天他交上意想不到的好運:鄰居送給他一輛腳踏車。年幼的拉瓦盧馬納納於是開始騎車到附近的農場,索討剩餘的牛奶並將它們變成自製的優酪乳。在生意剛起步時,他便試著回饋貧困的社區。他在當地教會當志工,或者在唱詩班裡唱歌,除此之外便是騎著那輛搖搖晃晃的破單車,一路叫賣優酪乳,一罐又一罐、年復一年發展出他的事業。
到了一九九○年代後期,拉瓦盧馬納納已經成為馬達加斯加的乳品業大亨,島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二○○二年,他成為拉瓦盧馬納納總統,在幾乎每個人都一窮二白的國家,身為精明的政治人物,他深諳白手起家的故事具有何等價值。擔任總統的拉瓦盧馬納納承諾帶來改變,起初,他履行了諾言。他的政府投資興建道路、取締貪污並以超高的經濟成長率根除貧窮。馬達加斯加變成全世界成長最快速的經濟體之一。這似乎是個成功的寓言故事,一個出身寒微的好人排除萬難,成為明智公正的統治者。
我決定去拜訪拉瓦盧馬納納。當我來到他那有如宮殿般的宅第時,他正穿著滾上白條紋的海軍藍Nike運動服走出前門。他滿面笑容地握住我的手,領著我入內。他帶我參觀他的訓練室,他從早上五點開始就一直在這裡做健身操。(「這是讓你保持敏銳的心智,以便做出重大決定的唯一辦法。」他告訴我。)接著他指向一座用來敬拜耶穌、裝飾華麗的定製神龕,這是某種火車模型版的伯利恆,上面有一具巨大的木製十字架俯臨著微型化的城鎮。我們走上樓,來到走廊盡頭時,他打開兩扇桃花心木製的大門。一張巨大的桌子出現在門後。桌面上擺滿食物、成堆的熱可頌麵包、以各種方式烹製的蛋、五種果汁,以及足夠餵飽他兒時村莊整整一星期的優酪乳。兜售水田芥的貧苦生活早已離他遠去。
儘管有拉瓦盧馬納納的幕僚長陪著我們,但只安排了兩個座位,一個給他,一個給我。我坐了下來,打開筆記本,伸手要拿筆,這才發現我忘了帶筆。
「沒問題。」拉瓦盧馬納納說,「我們或許貧窮,但並不缺筆。」他拿起叉子旁的小鈴鐺搖了起來。幾秒鐘後,兩名員工衝進房間,每個都希望搶先來到桌子旁。
「筆。」拉瓦盧馬納納厲聲說。
兩人匆忙離去,三十秒後回來,手上各抓著一支嶄新的原子筆,搶著得到讚美。動作比較慢、沒有獲得讚美的那個人看起來情緒低落。
這時拉瓦盧馬納納開始辦正事。他準備要在下次選舉中奪回總統寶座。他熱切地看著我。
「我從Google上得知你當過競選顧問。」他說,「告訴我,我應該怎麼做才能贏得選舉?」
這個問題讓我猝不及防。我去那裡是為了研究他,而不是當競選顧問。但我想要建立交情,只好臨場發揮。「我在明尼蘇達州幫忙處理州長競選活動時,我們想出一種有效的招數。我們在八十七天內走訪了全部八十七個郡,以顯示我們關心整個明尼蘇達州。馬達加斯加總共有一百十九個區,你不妨在一百十九天內走訪完這一百十九個區?」
他點點頭,示意我繼續說下去。
「你可以利用這個下鄉行程,搭配你的白手起家形象。你只需騎著腳踏車到每個城鎮,提醒人們你曾有過販售優酪乳的童年,藉以顯示你了解貧窮的滋味。」他點點頭,轉身對他的幕僚長說,「去買一百十九輛腳踏車。」
拉瓦盧馬納納對於如何出奇制勝打贏選戰並不陌生,他對打破規則也無所顧忌。二○○六年時,他雖然佔有再度當選的優勢,但他不願意冒任何風險。他運用了一個新奇的手法來操縱選舉:他迫使他的主要對手被流放,然後阻止他返回家鄉登記參選。每當他的對手設法想回到馬達加斯加,拉瓦盧馬納納就拿起電話,下令關閉島上所有機場,導致對手所搭乘的飛機掉頭返航。這個辦法奏效了。由於這個對手不准從海外登記參選,所以不在候選人名單中。拉瓦盧馬納納於是大獲全勝。
二○○八年,拉瓦盧馬納納,一個出身寒微,參加教堂唱詩班和當過慈善志工的人——變得貪婪。在掌權六年後,他的內心似乎已經被某種事物改變。在一個每人年平均所得只有幾百美元的國家,他花費六千萬美元的國家基金購買了一架總統專機(有點野心勃勃地命名為「空軍二號」)。他設法將這架飛機的牌照登記在自己名下,而非馬達加斯加政府。拉瓦盧馬納納年復一年地掌握權力,他腐化的程度似乎越來越嚴重。
最終這將證明是他垮台的原因。二○○九年,一名暴發的廣播節目主持人轉行從政,他組織了抗議拉瓦盧馬納納總統的活動。這位前主持人在廣播節目中慫恿和平抗議者遊行到總統府。在他們到達時,保護優酪乳大亨的士兵朝他們開火。數十人被射死,激起人們的憤怒。街道上的血跡剛被清洗掉不久,拉瓦盧馬納納便在政變中被推翻,接管政府的軍方擁立這位主持人上台。
或許傳統看法是對的:權力確實使人腐化。五歲時的拉瓦盧馬納納只夢想著從兜售水田芥晉級到販賣優酪乳,他規規矩矩地做生意,為人並不殘暴。他幫助的是別人而非自己。但掌控馬達加斯加似乎改變了他,使他變得更壞。但這或許不是拉瓦盧馬納納的錯。那位廣播節目主持人總統最終可能變得比他所取代的乳品業大亨更腐敗。假使你或我突然被擁立為這個以貪腐而聞名的島國總統,我們也可能會墮落。這只不過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然而傳統觀念有時錯得離譜。假使權力並不會讓我們變得更好或更壞呢?假使權力只吸引某些類型的人——而那些人恰恰是不應該掌權的人?也許最想要權力的人正好是最不適合掌握權力的人。也許渴望權力的人比較容易墮落。
如果你曾閱讀通俗的心理學書籍,你很可能聽說過一個惡名昭彰的研究,這個研究似乎暗示權力確實使人腐化。只是有個問題:關於這個研究,你以為你知道的一切其實是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