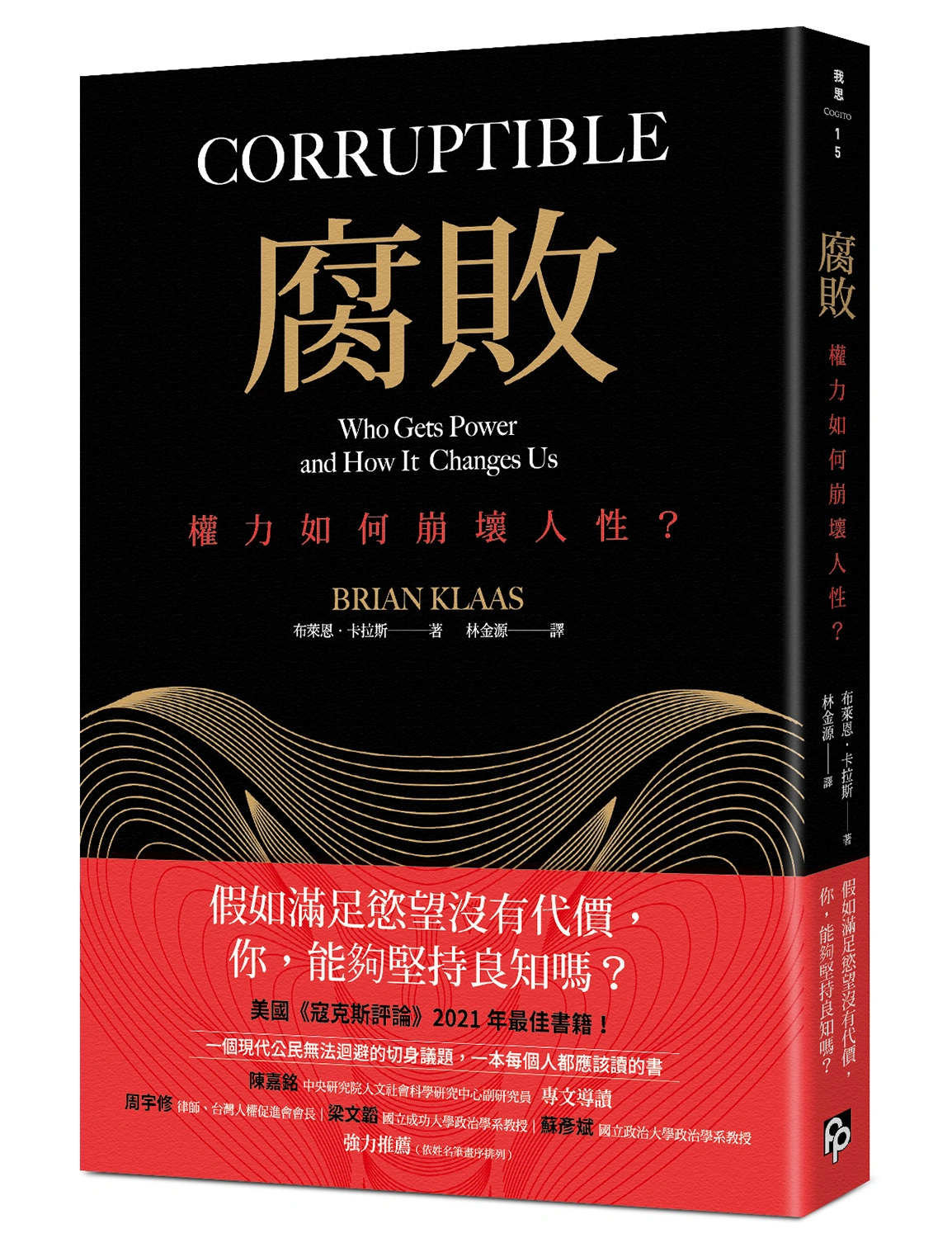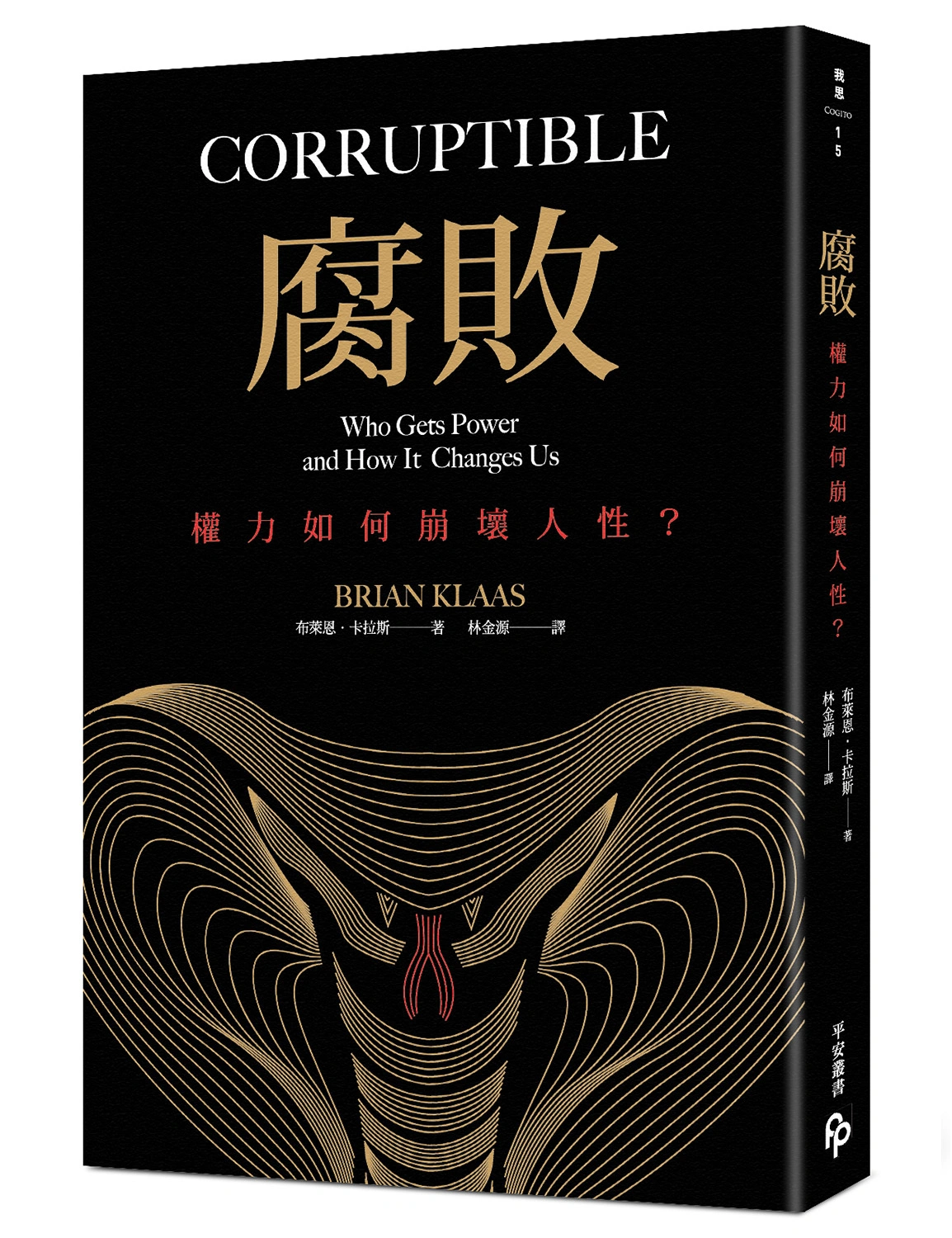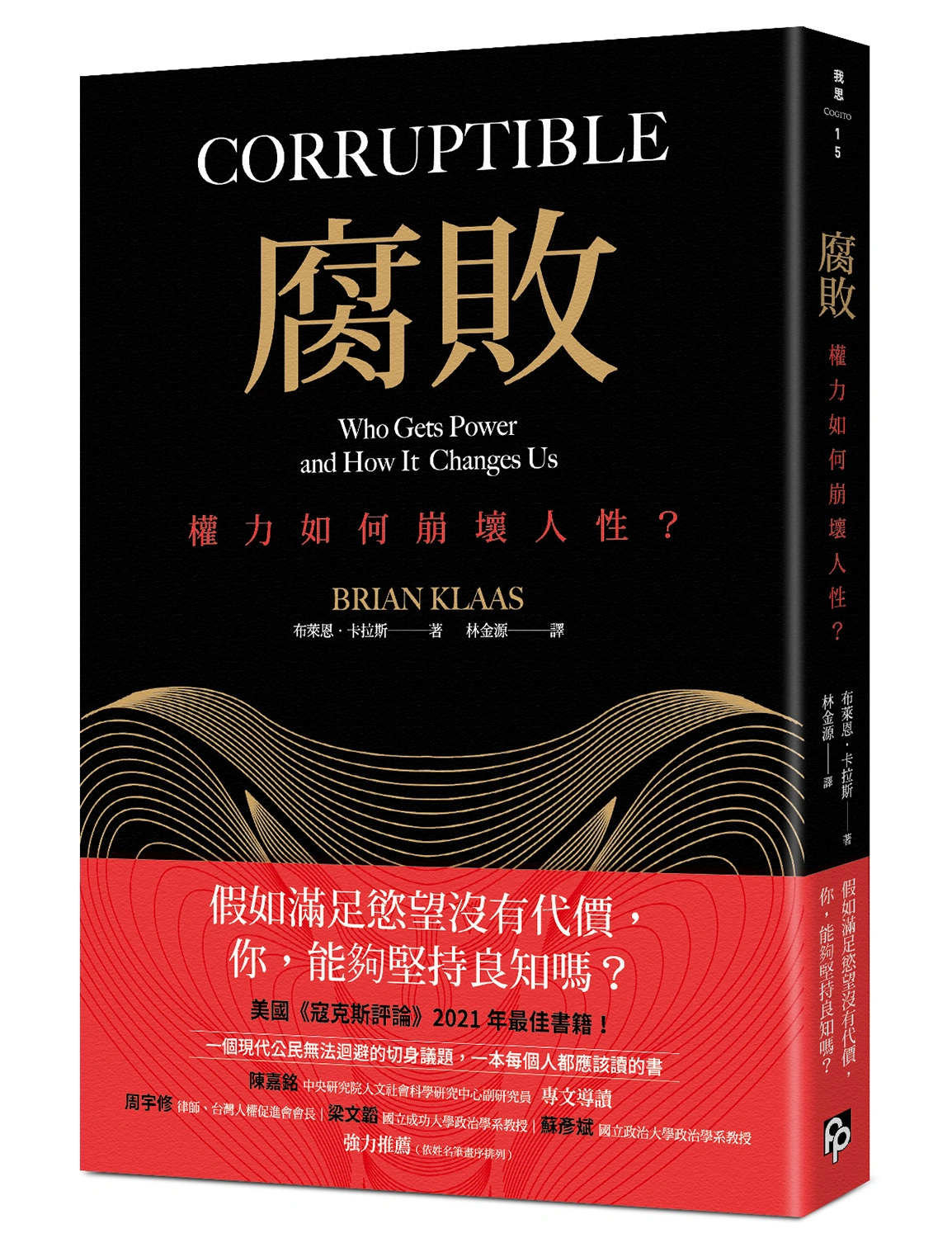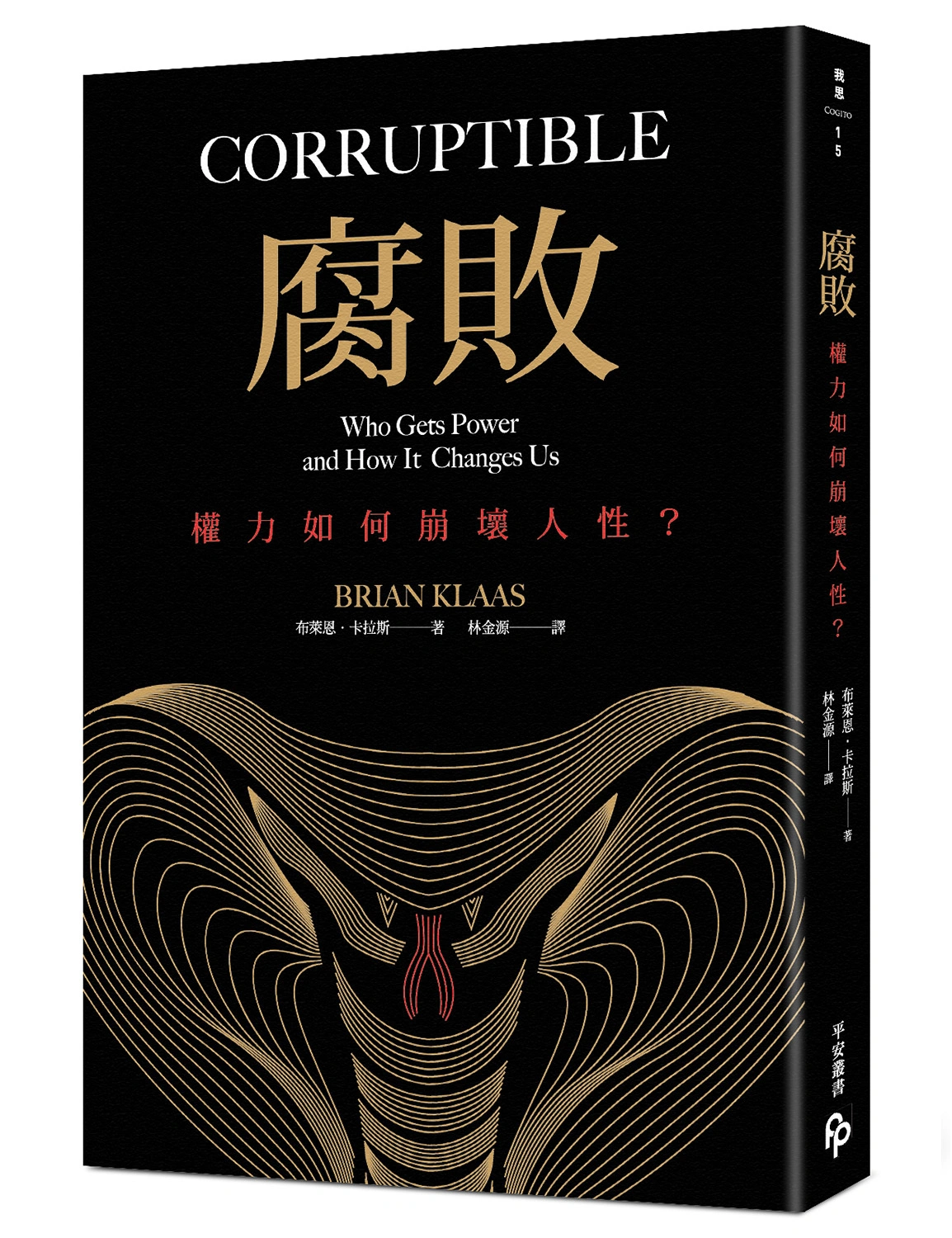內容試閱
第一章
引言
到底是權力使人腐化,或者腐敗的人受權力吸引?侵吞公款的企業家和殺人的警察是壞制度的必然結果,或者他們原本就是壞人?暴君是後天造就或生來如此?如果你被推上權力的寶座,中飽私囊或折磨你的敵人的新誘惑,是否會讓你心癢難耐而最終使你屈服?有點出人意料的是,我們可以從兩個被人遺忘的遙遠島嶼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
遠在澳大利亞西部海岸外,有一小塊名為燈塔島(Beacon Island)的陸地勉強浮出於海面。島上覆蓋著矮小的青草,三角形的海岸線周圍是米黃色沙灘。如果你站在島上的某端,對著另一端投出棒球,它大概會落入海中。這似乎只是一座近岸處點綴著一些珊瑚,不值得注意的無人小島,但燈塔島藏著一個秘密。
一六二八年十月二十八日,一艘長一百六十英尺的香料船「巴達維亞號」(Batavia)從荷蘭啟航。這艘貿易船隸屬於荷蘭東印度公司旗下的船隊,該公司帝國控制著全球貿易。「巴達維亞號」載著一大筆銀幣,準備用來交換現今印尼爪哇島上的香料和異國財富。船上有三百四十個人,其中一些是乘客,大多數是船員,還有一個心理病態的藥劑師。
船上事務按嚴明的階級制度進行規劃。「住宿條件方面,越靠近船首越簡陋。」船長在船尾處坐擁一個大艙房,他嘴裡嚼著醃肉,一面厲聲對著手下發號施令。在兩層甲板下,士兵們擠在通風不良、老鼠出沒,回程時用來儲存香料的爬行空間中。「巴達維亞號」上的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的位階。
杰羅尼姆斯.科內利玆(Jeronimus Cornelisz)是比船長低幾個位階的資淺商人,一個窮困潦倒的前藥劑師。歷經一連串個人的不幸後,他在絕望之餘簽約到船上工作。啟航不久後,他著手進行一項翻身計畫。科內利玆與某位高級職員串通,密謀策劃一場叛變。他故意讓船偏離航道,準備在孤立的水域內奪取控制權。如果一切都按計畫發生,他將控制住「巴達維亞號」並展開豪奢的新生活,大肆揮霍手中的銀幣。
但事情沒有按計畫發生。
一六二九年六月四日在澳大利亞外海,「巴達維亞號」全速撞上低矮的阿布羅略斯群島(Abrolhos Islands)的珊瑚礁,木製的船身碎裂。其間沒有人發出警告,也沒有要求改變航道的呼叫。一看便知道,這艘船顯然已經在劫難逃。大多數的乘客和船員設法游到岸上。幾十個人溺斃,其他人試著攀附著「巴達維亞號」的殘骸。
船長明白除非獲得救援,否則無人能生還,他於是控制住緊急救生艇和搶救來的大部分物資。他和其他四十七個人出發前往爪哇島,其中包括領導階層的所有高級船員。他保證他們很快就會帶著救援隊回來。數百人被拋棄,沒有食物也幾乎沒有飲用水,只剩下期待某天有人回來拯救他們的一絲希望。貧瘠的島上沒有生長任何植物或棲息任何動物。情況很明顯:倖存者命在旦夕。
原本想要叛變的科內利玆也被留了下來。他已經沒有適於航海的船隻可以接管,但是他不會游泳,所以與其跳入水中、拚命地朝島上游去,站在沉沒中的「巴達維亞號」殘骸上似乎是更好的選擇。接連九天,包括科內利玆在內的七個男人佔據一片逐漸縮小的木頭乾燥區域。他們一面喝酒、一面盤算著不可避免的事。
六月十二日,「巴達維亞號」終於解體。在海浪的沖刷下,部分倖存者撞上鋒利的珊瑚而提早喪命,其餘的人不久之後跟著溺斃。科內利玆不知怎的活了下來,他最終「抓住一大塊浮木漂浮到島上,成為『巴達維亞號』的最後一名生還者」。
科內利玆來到位於現今燈塔島潮濕沙地上的避難處。在求生本能下的失序和混亂狀態,逐漸恢復成按階級和地位安排的既定秩序。雖然科內利玆被沖上岸時衣衫襤褸且虛弱,但他依舊是高級職員,意味著他是當家做主的人。「『巴達維亞號』是一個高度講求階級的社會。」歷史學家麥克.戴許(Mike Dash)說,「同樣的情況殘留在燈塔島。」受困在島上的幾百個人連忙過來幫助他們的上司。他們將會後悔這麼做,或者至少有些人會後悔。
一等到恢復健康和重振精神後,科內利玆迅速做了些盤算。情況非常惡劣:船隻失事後所剩的食物、飲水和酒維持不了多久。供給不會增加,他心想,因此必須降低需求。這些倖存者需要減少會張口吃飯的嘴。
科內利玆開始藉由消滅潛在的對手來鞏固自己的權力。有些人被派去進行有勇無謀的任務,然後被推出小船外落水溺斃。有些人被指控犯罪,這是用來判處他們死刑的藉口。可怕的處決行動確立了科內利玆的權威,同時也提供有用的忠誠測試。願意聽從科內利玆命令殺人的人,對他來說是有用的人,而拒絕聽命行事的人則是威脅。這些威脅一一被剷除,很快地,就連藉口都不需要了。為了試試看某把劍是否仍然鋒利,有一名男孩因此被斬首。兒童們無端被殺,這些殺戮都是按科內利玆的命令完成,但他本人沒有親自動手。他穿著從船上取得的華服,藉以展現他的支配力:「絲質長襪、滾上金邊的吊襪帶以及……諸如此類的裝飾品。」其他人穿著骯髒破爛的衣服等著依序被殺。
幾個月後,等到「巴達維亞號」船長帶著救援隊回來時,已經有一百多人遭到殺害。科內利玆最終嘗到他自己的島嶼正義:他獲判死刑。他被砍掉雙手並絞殺。但這個恐怖事件引發了一個令人感到不安的人性問題:倘若當時科內利玆不在船上,是否可以避免這場大屠殺?或者自然會有別人來領導他們做這件事?
燈塔島以東四千英里處,澳大利亞另一邊有一座隸屬於東加群島的荒島,名叫阿塔島(‘Ata)。一九六五年時,有六名十五至十七歲的男孩逃出寄宿學校,他們偷了一艘漁船向北航行。第一天他們只前進了五英里就決定下錨休息過夜。在他們試著入睡時,一陣暴風劇烈地搖晃他們那艘長二十四英尺的船,結果扯起船錨。超級強風很快就吹壞船帆,還摧毀掉船舵。等到天亮時,男孩們無法操縱船隻,也無法航行,只能隨著洋流漂浮。他們連續八天沿著海岸向南前進,完全不知道回家的方向。
當這六名青少年開始失去希望時,他們望見遠方有一片隱約的綠意。那是阿塔島,一座植被濃密的崎嶇島嶼。他們駕駛那艘只能有限度操縱的受損漁船,等到漂近岸邊時便棄船游泳上岸。在被沖進無情的汪洋之前,這是他們最後的機會。他們終於成功上岸,雖然被岩石割傷,但活了下來。
阿塔島周圍的峭壁使得登島變得困難,沒想到卻成為遭遇船難的男孩的生存助力。鋸齒狀的岩石是海鳥築巢棲息的完美場所,他們開始合作架設陷阱捕鳥。由於找不到淡水,他們只能隨機應變吸食海鳥血液。在新家四處搜尋後,他們升級到以椰子水解渴。最終他們的三餐從生食變成熟食,因為他們生起第一把火。男孩們商量好必須使餘火持續燃燒,絕不能讓它熄滅。他們於是輪流看顧餘火,一天二十四小時不眠不休。這條生命線讓他們得以烹煮魚肉、海鳥和甚至烏龜。
在通力合作下,男孩們的生活水準進一步提升。他們接連四天合力從島上大樹的根部一滴滴收集淡水。他們挖空樹幹來蒐集雨水,還用棕櫚葉搭建出一間簡陋的房屋。他們每件事都分工合作,沒有人當領導者。沒有鑲金邊的裝飾和長襪、沒有大聲下達的命令、沒有為了鞏固權力而策劃的陰謀,也沒有殺人事件。當他們征服這座島嶼時,成功和失敗都由大家平均分擔。
遭遇船難六個月後,當中一名男孩特維塔.法泰.拉杜(Tevita Fatai Latu)在每日例行獵捕海鳥時滑倒,結果摔斷了腿。其他五名男孩連忙過來幫助他,利用傳統東加方法,烤熱椰子樹莖製作出夾板,將骨頭固定復位。接下來的四個月,特維塔無法走路,但其他男孩一直照顧他,直到他能再度處理日常瑣事。
他們不時發生爭執。(六個人整天形影不離,菜單是一成不變的海鳥和烏龜肉,難免讓人偶爾脾氣失控。)然而一旦爆發衝突,男孩們會識相地分開。意見嚴重分歧的男孩會各自待在島上的不同地點,有時長達兩天,直到他們冷靜下來,可以再度合作求生存。過了一年多後,他們開始體認到這種新生活不是暫時的,因此得有長期安頓下來的打算,他們藉由製作粗陋的網球拍和舉行比賽、安排拳擊賽和一起健身來度日。為了避免耗盡海鳥存糧,他們同意限制每人每天的食物量並開始嘗試種植野生豆子。
在男孩們遭遇船難十五個月後,一個名叫彼得.華納(Peter Warner)的澳洲人開著他的漁船找尋捕捉螯蝦的地點。當他靠近一座無人居住的島嶼時,他發現一件不尋常的事。「我注意到峭壁上有燒焦的痕跡,這在熱帶地區並不尋常,因為在那麼潮濕的大氣環境中,不可能引發叢林野火。」現年八十九歲的華納回想。接下來,他看見令人驚奇的景象,一位留著十五個月的長髮的裸體男孩。男孩們大聲吶喊並揮舞著棕櫚葉,希望引起這艘船的注意。當船靠得夠近時,男孩們跳進海中,開始游向他們從沒想到會出現的救星。華納不確定發生了什麼事,他不知道這些男孩是否是被放逐到島上的囚犯,這項懲罰專門留給玻里尼西亞社會中最壞的壞蛋。「見到這些沒穿衣服、沒理髮,看起來健康的青少年,我有點驚慌。」他告訴我。華納將步槍裝上子彈,嚴陣以待。
當男孩來到船上時,他們客氣地解釋自己的身分。華納沒聽說有任何男孩失蹤,於是用無線電聯絡接線生,要他打電話到男孩在東加的學校證實他們的說法。二十分鐘後,流著淚的接線生告知華納,這些被認為已經死亡的男孩失蹤了一年多。「他們的葬禮已經舉行過。」接線生說。男孩被帶回東加與家人團圓。在他們獲救後,當中年紀最大的席歐內.法圖阿(Sione Fataua)說起他對生還返家的焦慮:「我們當中的幾個人有女朋友。或許她們已經不記得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