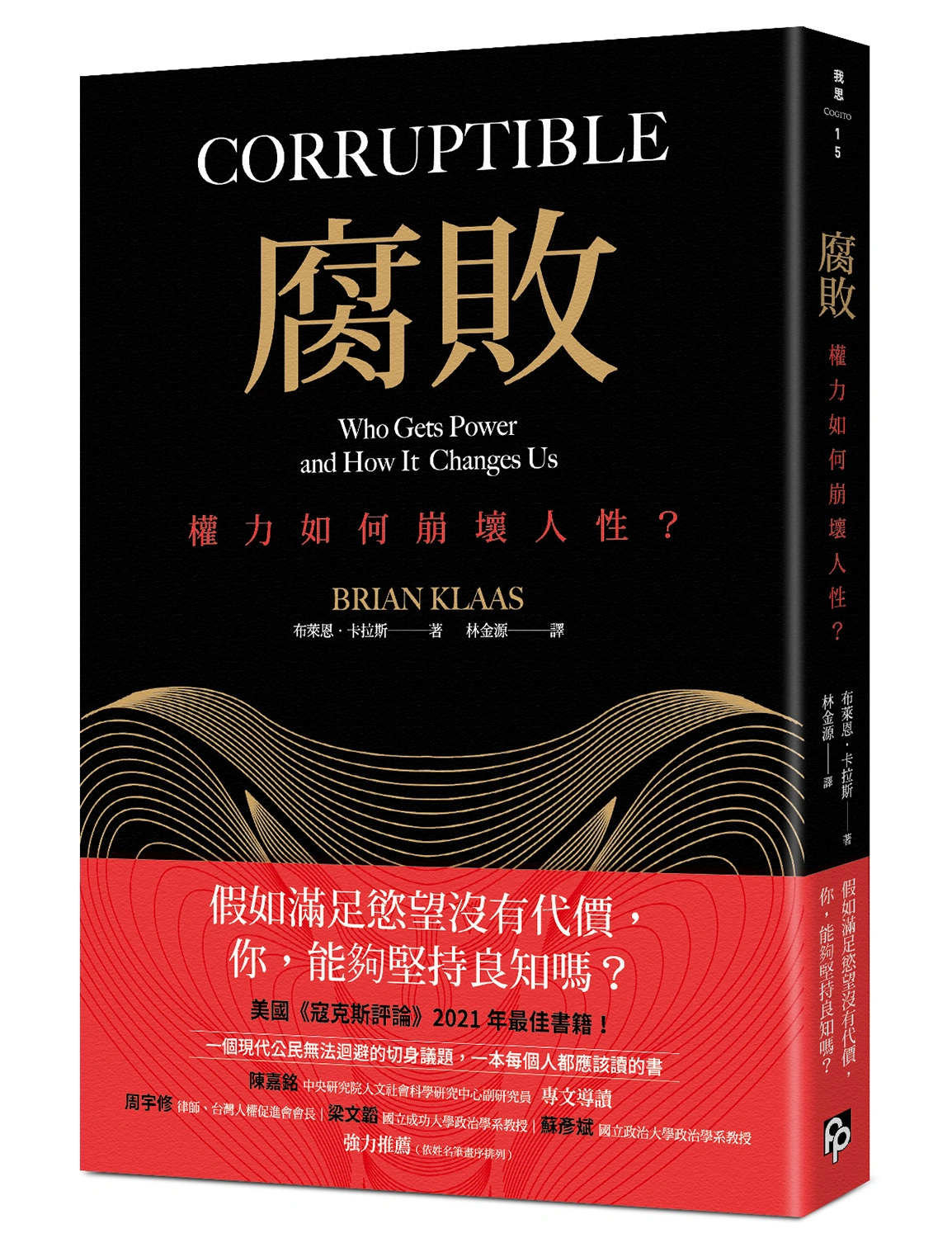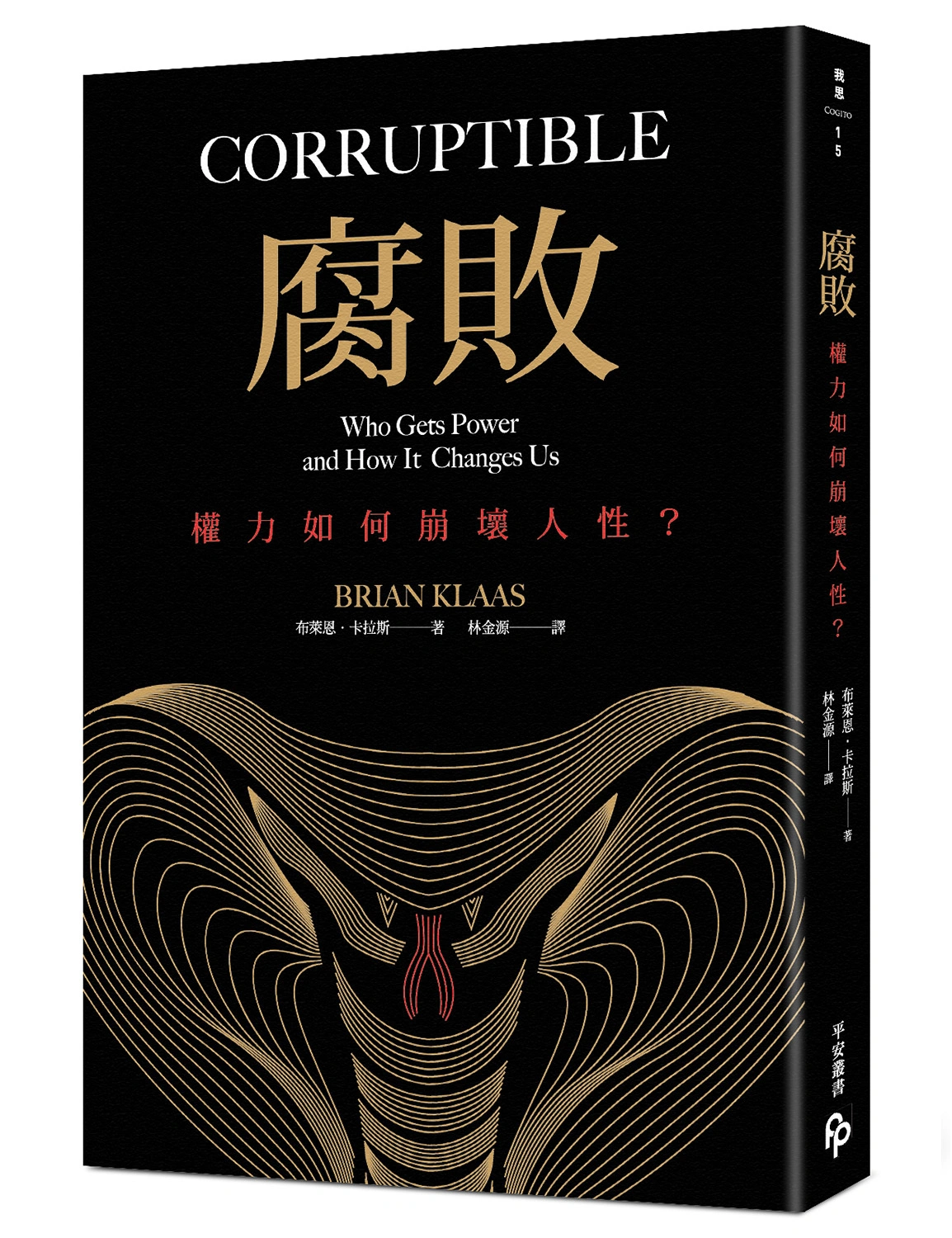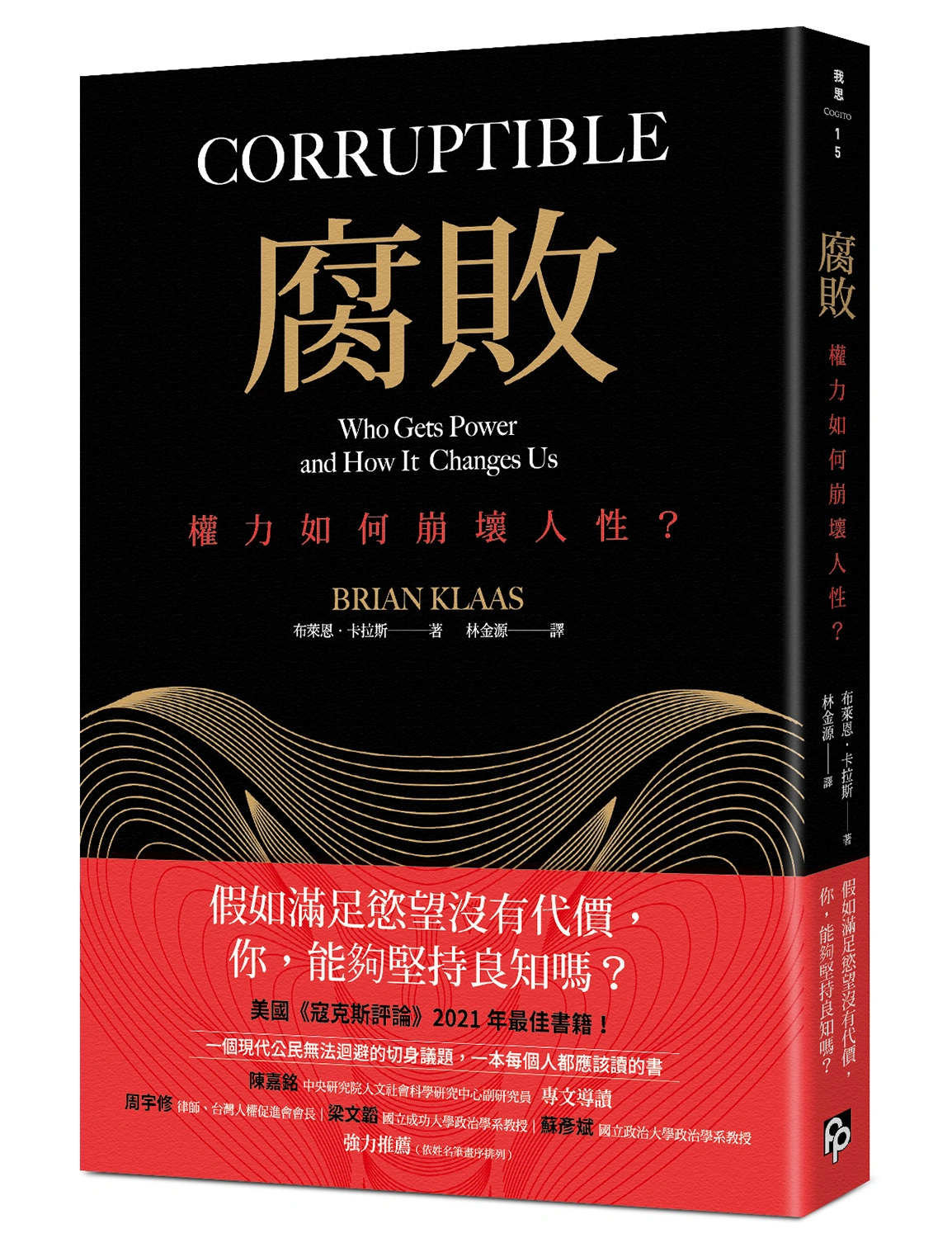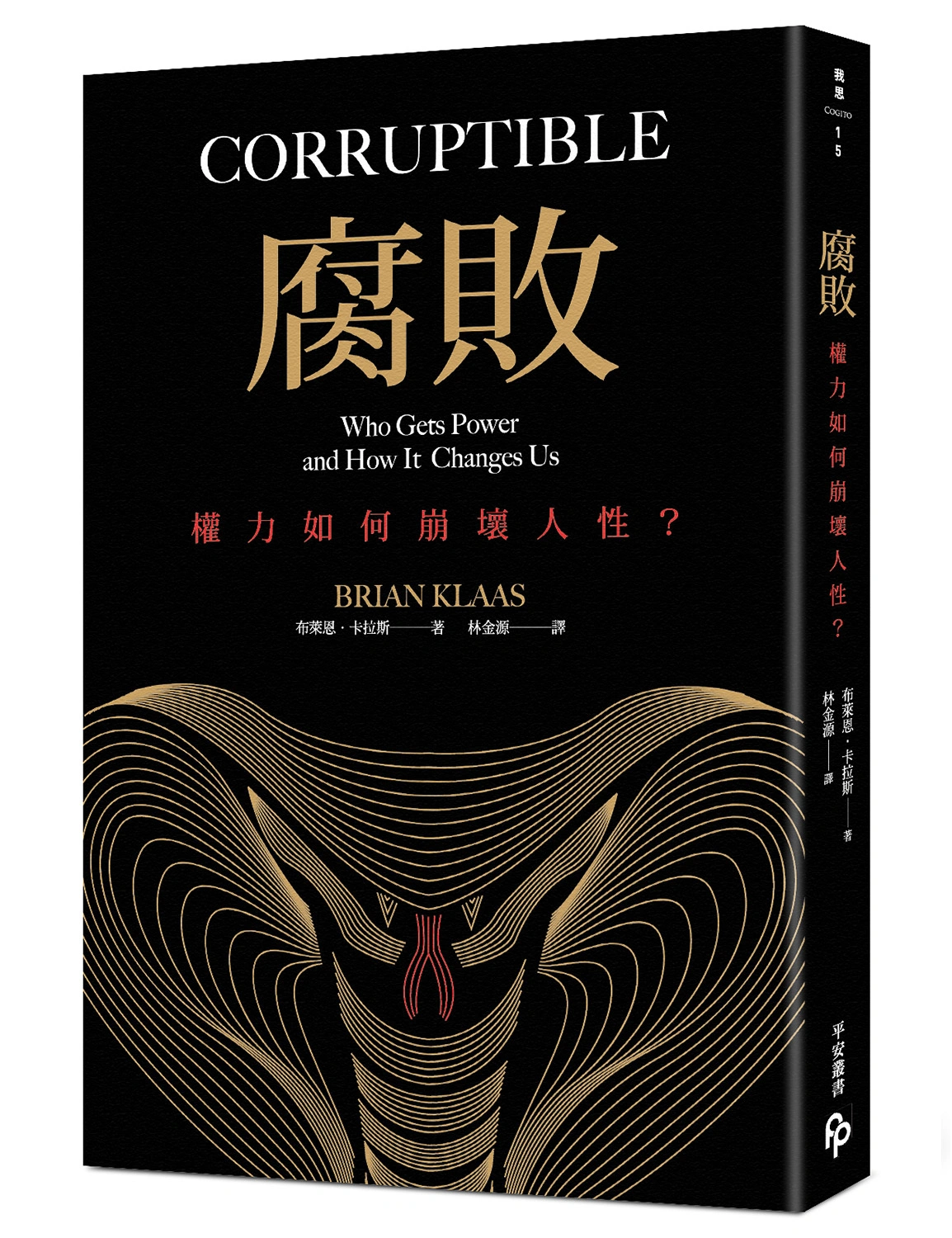內容試閱
一九七一年暮夏,史丹佛大學的研究者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在心理學系的地下室搭建一座模擬監獄。他招募了十八名大學生參與一項準科學研究,目的在判定社會角色是否會改變一般人的行為到不像話的程度。這個假說相當簡單:人類行為變化莫測。我們會配合我們所扮演的角色,或者說我們所穿的制服。
為了測試這個假說是否為真,津巴多隨機指派其中九名自願參與者為「守衛」,其他九名參與者則成為「囚犯」。為了為期兩週、每天十五美元的報酬,他們必須進行一場過於真實的刑事司法角色扮演。接下來發生的事,如今變得惡名昭彰。守衛幾乎立刻開始虐待囚犯。他們用滅火器攻擊囚犯,拿走囚犯的床墊並強迫他們睡在混凝土地板上。扮演守衛的大學生剝光同儕的衣服,只為了顯示誰是老大。權力似乎使他們變得可怕。
在喪失人身控制權後,原本自豪、外向開朗的大學生變得封閉保守和順從。一名守衛在虐待完他的大學同儕後,命令囚犯排好隊以便羞辱他們。
「以後我說什麼,你就做什麼。」
「謝謝你,矯正官。」一名囚犯回答。
「再說一遍。」
「謝謝你,矯正官。」
「說『上帝保佑你,矯正官』。」
「上帝保佑你,矯正官。」
這項研究原本要持續進行兩個星期,但當津巴多的女朋友來探訪這座模擬監獄,她被所目睹的境況給嚇壞了,六天後,她說服津巴多停止了實驗。研究結果發表之後,舉世震驚。有人為此製作紀錄片,也有人寫書。證據似乎相當明確:權力能召喚出我們每個人心中的惡魔。
但這當中藏了一個圈套。看似直截了當的史丹佛監獄實驗故事,不是這麼清楚明白——這已成為心理學的傳統看法。守衛之中只有一些人濫用權力。有些守衛拒絕濫用權力,並給予大學生囚犯尊重的對待。因此,即便權力真的使人腐化,是否有人比其他人更加不受影響?
此外,如今有些囚犯和守衛表示,他們當年只是在進行表演。他們相信研究人員想要看見一場表演,於是便給他們一場表演。近來被揭露的實驗準備階段錄音,已經讓人質疑這些參與者是否因為受到指示而對囚犯苛刻,並非自然而然變卑鄙。因此,情況比我們被引導去相信的還要撲朔迷離些。
但即便有這些提醒,這個實驗仍然教人感到心寒。一般人如果在合適的環境下,是否都有可能變得殘酷和邪惡?一旦我們控制了別人,我們是否全都是等著被揭下面具的虐待狂?
幸好答案可能不是如此。津巴多的結論並沒有考慮到該研究的一個重要層面:參與者的招募方式。研究人員為了找來囚犯和守衛,在當地報紙刊登了以下的廣告:
徵求男性大學生參與監獄生活的心理學研究。自八月十四日起,為期一至兩週,每日報酬十五美元。欲知詳情與應徵,請洽……
二○○七年,西肯塔基大學的研究人員注意到廣告中似乎微不足道的細節。他們感到納悶,這是否已經不慎使該研究產生偏差。為了找出答案,他們複製了這則廣告,只將十五美元改成七十美元(因應一九七○年代以來的通貨膨脹所作的調整)。除此之外,更新後的廣告中每個字都一模一樣。後來,他們又創造一個新廣告,除了一個關鍵的差異,其他部分都相同:「參與監獄生活的心理學研究」改成「參與心理學研究」。他們在某些大學城放置「監獄生活」廣告,在其他大學城放置「心理研究」廣告。其概念是讓一組人自願參加監獄實驗,而另一組參加一般心理學研究。回應這兩則廣告的人會有什麼差異嗎?
招募期結束後,研究人員要求未來的研究參與者接受心理篩選和徹底的人格評估。他們的發現十分驚人。相較於回應一般心理學研究廣告的人,那些回應監獄實驗廣告的人在「侵略性、獨裁主義、馬基維利主義、自戀和社會優勢」的測量項目獲得相當高的分數,而在「同理心和利他主義傾向項目的得分明顯偏低」。只不過是在廣告中包含了監獄這個用語,結果便招來不成比例的一批殘酷成性的學生。
這個發現可能翻轉了史丹佛監獄實驗的結論,在根本上改變我們對權力的了解。史丹佛監獄實驗並沒有證明被賦予權力的一般人會變得殘酷,而是可能證明了殘酷成性的人會尋求權力。或許我們倒因為果。或許權力只是一塊吸引壞人的磁鐵,而非使好人變壞的一種力量。依此構想,權力不會使人腐化——它吸引腐敗者。
但仍有另一個謎。即便不適合掌權的人被權力吸引,他們為何似乎很容易獲得權力?畢竟在現代社會中,大量的控制不是奪取來的,而是被給予。執行長不必與中階經理進行格鬥士般的戰鬥,就能進駐邊間辦公室。懦夫和腐敗的政客,至少在民主政體中,需要一般大眾支持他們掌權。近來所揭露關於史丹佛監獄實驗的事,提升了壞人受權力吸引的可能性。但我們又為什麼容易因為錯誤的理由,而將權力交給不對的人?
二○○八年,瑞士研究人員進行一項實驗來測試這個假說。他們招募了六百八十一名當地兒童,年齡介於五歲到十三歲之間。這些孩童被要求玩一個電腦模擬遊戲,他們必須為一艘即將出航的船做出相關的決定。每個孩童都得依據出現在螢幕上的兩張臉,為他們的數位船挑選一位船長。此外沒有其他資料。如此的設計是為了迫使這些孩童決定:對你而言誰看起來像是個好船長?誰似乎可以成為你想像中的船隻的有效領導者?
孩子們不知道的是,這兩個可能的船長人選並不是隨機搭配。他們是最近在法國國會選舉中競選的政治人物。成對的臉隨機分配給這些孩童,但他們所看見的每一對組合都包含了勝選者和第二高票。研究的結果相當驚人:孩子們挑選出來的船長,有高達百分之七十一的機率是贏得選舉的候選人。當研究人員改以成人為對象,進行相同的實驗時,他們驚訝地發現近乎相同的結果。研究結果有兩方面值得我們注意。首先,連兒童都能光憑長相就準確辨識出勝選者,突顯出我們對於領導潛力的評估方式是多麼膚淺。第二,在挑選掌權者時,兒童和成人的認知歷程並無根本上的差異。此事賦予憑表象(at face value)相信人這個片語新的意義。進一步的證據指出,我們挑選領導者的能力是有問題的,其他幾項研究也顯示在群體討論中,更具攻擊性或表現粗野的人會被視為比更樂意合作或更溫順的人,看起來更有權力和更像領導者。
沒錯,事情越變越複雜。權力可能使好人腐化,但也可能吸引壞人。身為人類,不知怎的我們似乎因為壞的理由而被壞的領導者吸引。
不幸的是,這種複雜性才只是起點,還有另一個需要考量的難題。假使掌權者之所以做壞事,並非因為他們原本就是壞人,不是因為得到權力之後變壞,而是因為他們受困於壞的體制呢?這個想法非常有道理。畢竟奉公守法可能會讓你在挪威晉升,但保證你永遠無法在烏茲別克獲得權力。這有助於解釋為什麼某些位高權重者是真正的了不起——他們一心幫助別人而非幫助自己。因此權力的誘惑和掌握權力的影響可能得視背景而定。幸好,背景和體制是可以改變的。這帶給我們一些好消息:或許我們不是注定要活在一個無法避免科內利玆式濫權領導的世界。
在印度班加羅爾(Bangalore)所進行的研究為上述的樂觀看法提供了一些證據。研究人員想看看什麼類型的人會被公職吸引,當地公家部門是以貪污受賄而聞名。印度文官提供了合適的試驗場,因為他們的貪污腐敗可謂惡名昭彰。人人都知道在班加羅爾當公務員有機會獲得灰色收入。在這個由兩位經濟學家所設計的實驗中,數百名大學生被要求投標準的骰子四十二次並記錄結果。當然,投骰子的結果全憑運氣。然而在投骰子之前,他們被告知如果他們運氣好,投出更高的點數,會獲得更多報酬。投出更多的四點、五點和六點可以賺到更多現金。
但由於結果是自行報告,學生可以謊報他們投骰子的結果。許多人的確這麼做。投出六點的次數佔百分之二十五,而一點只有百分之十。藉由統計分析,研究人員可以確定,如此偏差的結果不可能是因為運氣。有些學生甚至厚顏無恥地宣稱他們接連投出四十二次的六點。但這些數據透露出蹊蹺:在實驗中作弊的學生,他們的職業志向不同於誠實記錄的學生。比起一般學生,自行報告出造假的高點數的學生,有更多人表示他們想要加入腐敗的印度文官體系。
丹麥的另一組研究人員也做了類似的實驗——這個國家的文官體系乾淨且透明,卻獲得相反的結果。誠實地自行報告點數的學生更想要擔任公務員,而說謊的學生尋求能讓他們以骯髒手段致富的職業。腐敗的體制吸引腐敗的學生,誠實的體制吸引誠實的學生。或許這無關權力使人改變,而是與背景有關。好的體制能創造出以合乎道德的方式追求權力的良性循環。壞的體制則創造出讓人們為了爬到最高位,樂於說謊、欺騙和偷竊的惡性循環。如果這是事實,那麼我們應該關切的不是掌握權力的個人,而是修補不健全的體制。
關於這些惱人的複雜謎題,我們有一系列可能的解答。第一,權力讓人變得更壞——權力使人腐化。水田芥變成優酪乳帝國,在你還會意不過來之前,你已經匆匆投入選戰,用不屬於自己的錢買飛機。第二,並非權力使人腐化,而是比較糟糕的人會被權力吸引——權力吸引腐敗的人。心理病態的藥劑師忍不住要在一艘注定滅亡的船上攀登到最高位,而虐待狂無法抗拒穿上制服,用警棍毆打囚犯的誘惑。第三,問題不在掌握權力或追求權力的人身上,而是我們因為壞的理由而被壞的領導者吸引,我們還傾向於授予他們權力。我們的船長是基於不理性的原因被挑選出來——不只是想像中的船。當他們帶領我們撞上礁岩時,我們只能怪罪自己。還有第四,我們不應該將重點放在個別的掌權者,因為一切都取決於體制。壞的體制產生壞的領導者,只要創造出正確的背景環境,權力就能使人淨化而非使人腐化。
這些假說是關於人類社會的兩個最基本問題的可能解釋:誰得到權力以及權力如何改變我們。本書會提供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