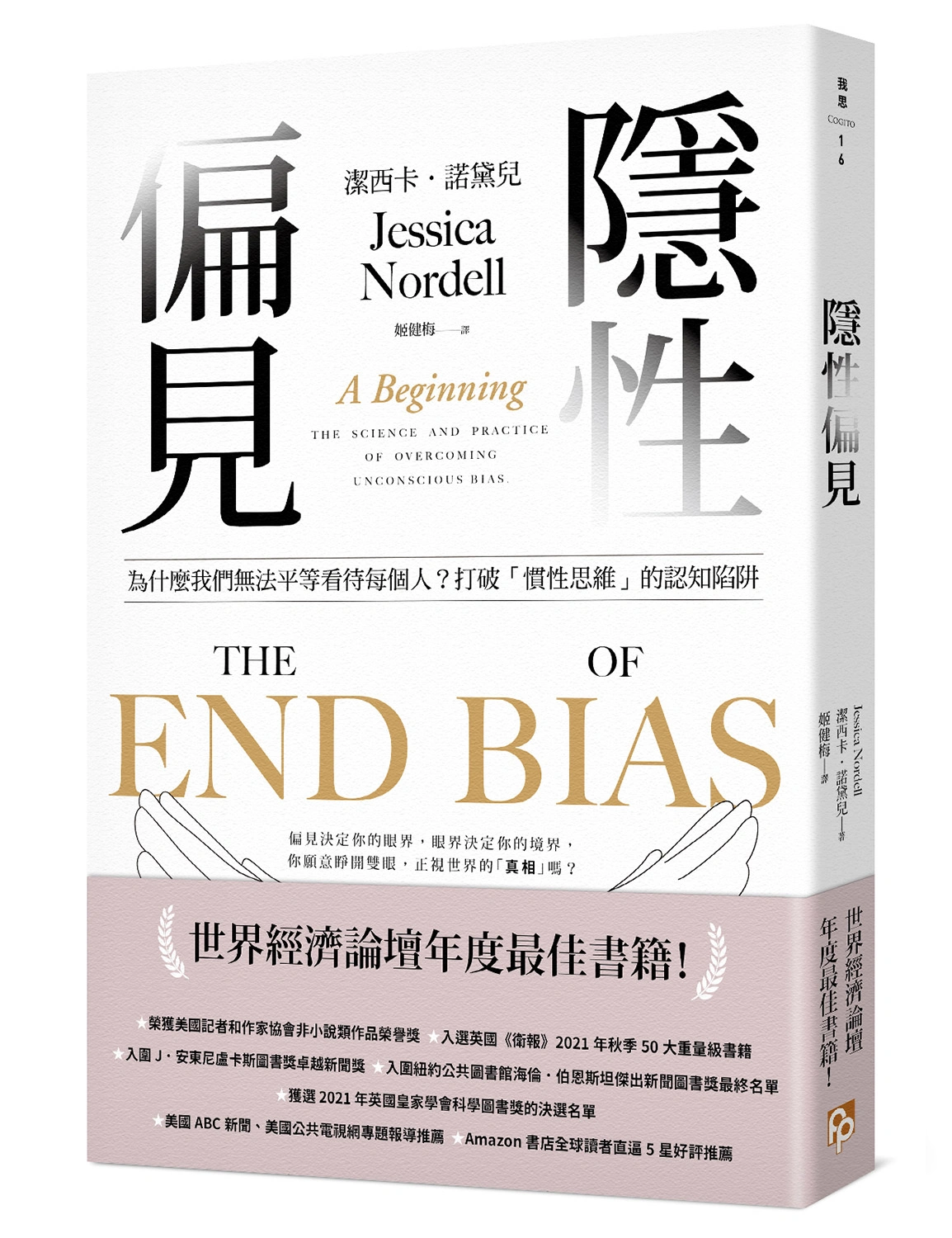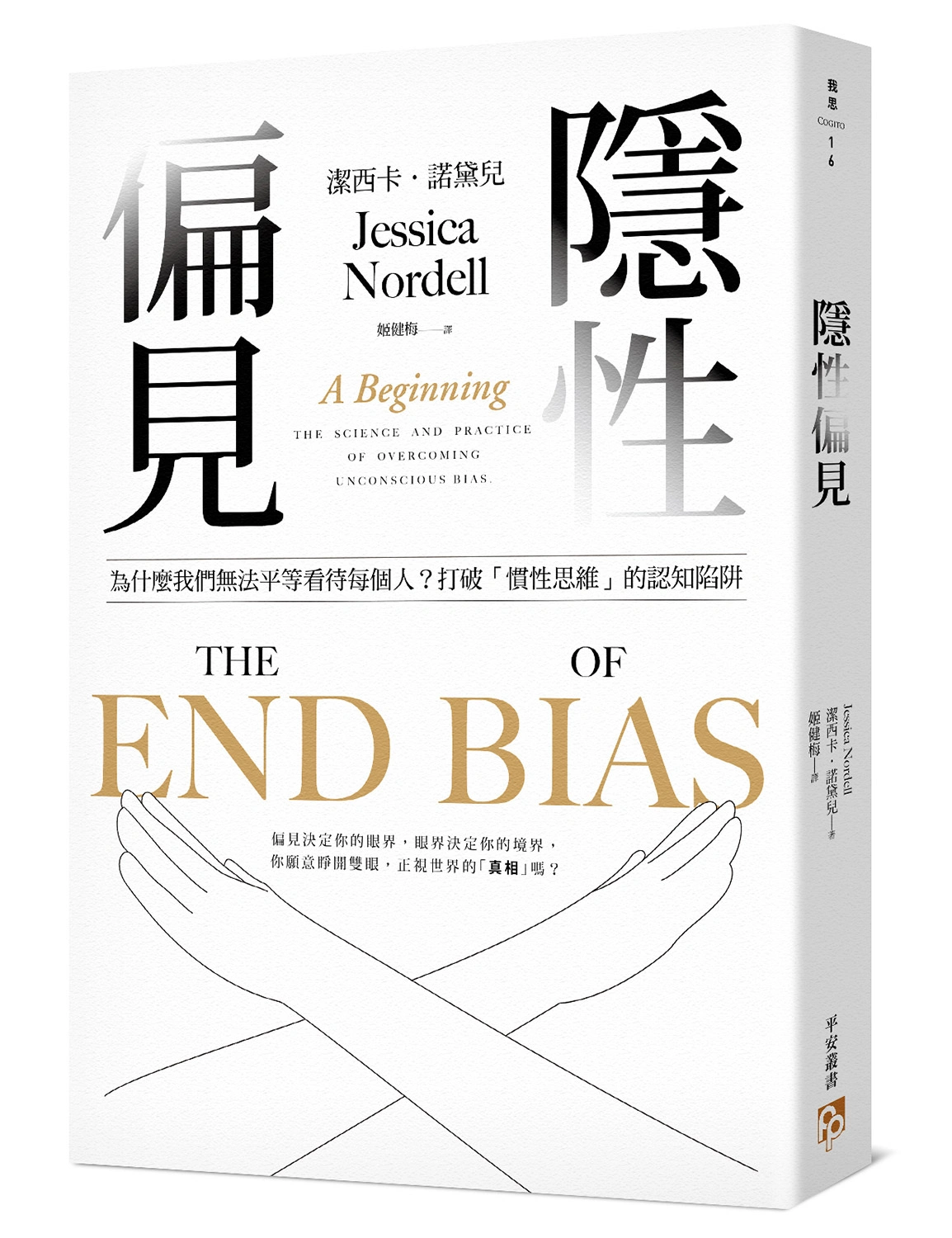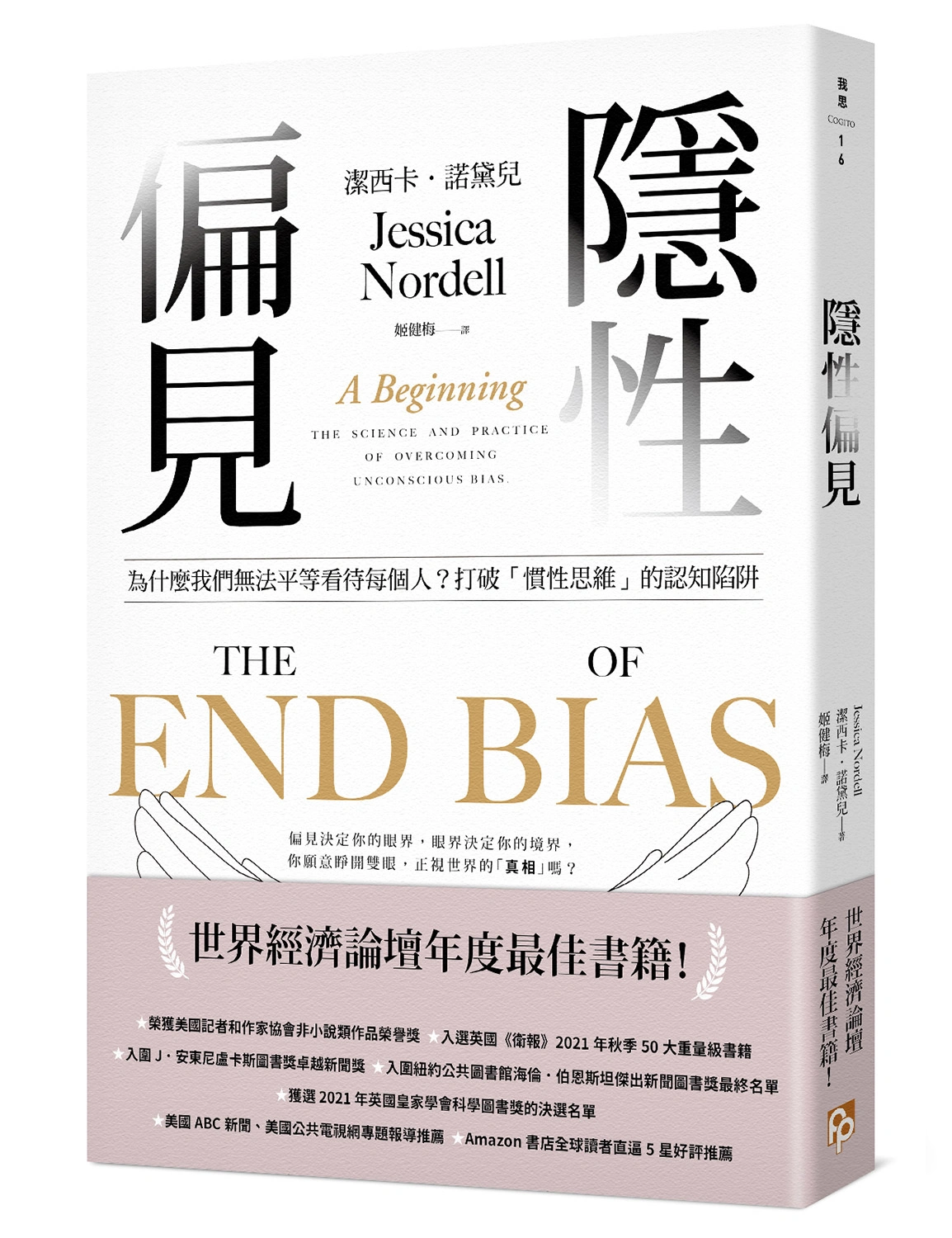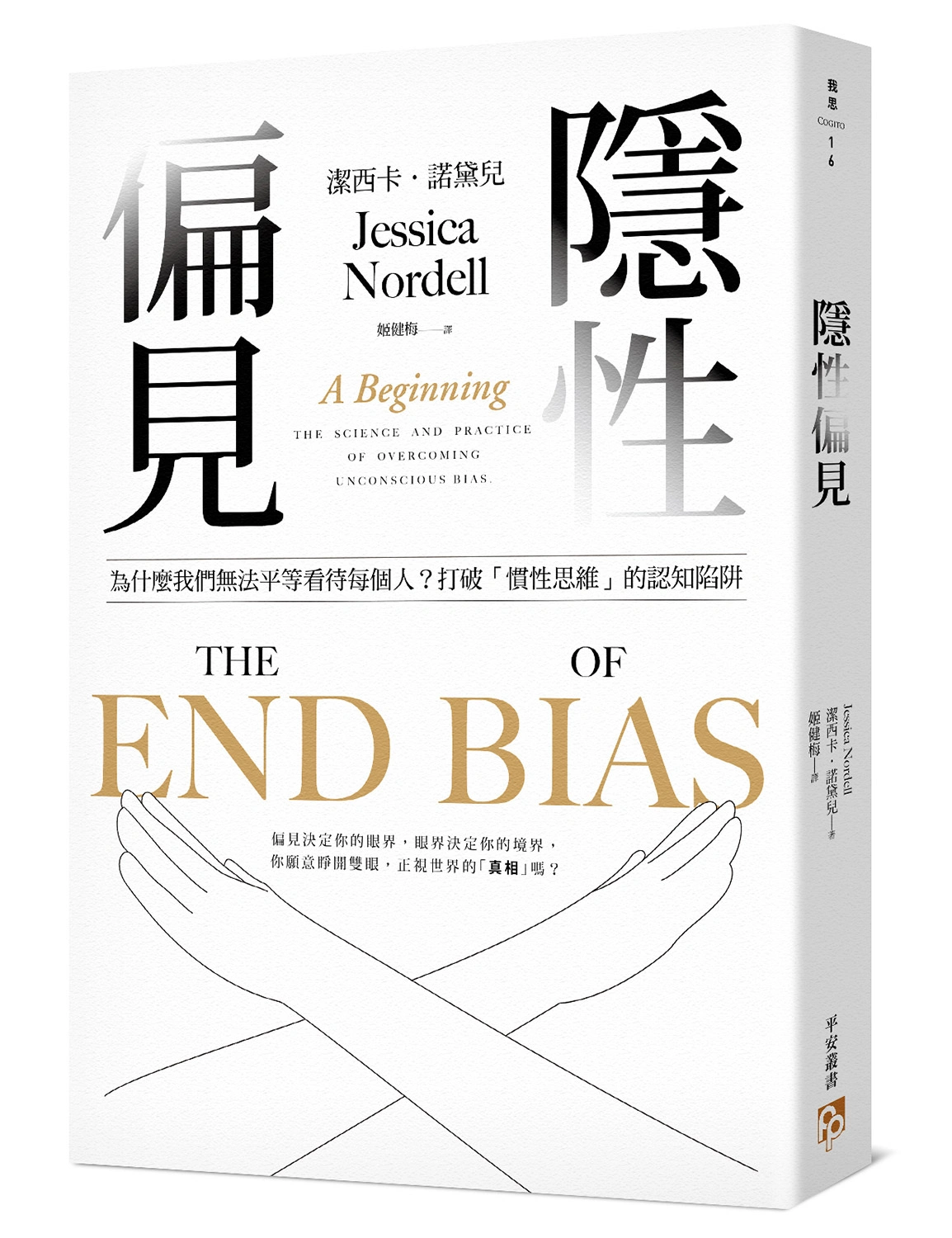內容試閱
我成長於一九八○和九○年代,在許多方面都受到保護,乃至於我無法理解偏見,甚至察覺不出偏見。身為白人生長在一個白人居多的城鎮,雖是猶太人,但別人幾乎看不出來,乃至於我曾在一場聖誕節活動上受邀上台分享「耶穌對我的意義」。我就像大多數白人一樣在種族的地景上移動:像個備受呵護的嬰兒,從來無須認真應付種族歧視,總是能夠選擇不去考慮這個問題。學術界的結構在某種程度上也保護了我不受性別偏見的影響。在我就讀的那所小型天主教中學,如果我在微積分測驗取得高分,那就是不容爭辯的事實。我沒去參加誓師大會,而和對街吸食大麻的癮君子一起閒晃,這並不重要,而我是個女孩這件事似乎也並不重要。成績似乎遮蓋了我身體的具體特徵,保護我免於受到性別歧視。在大學裡,我主修物理。當我在各個領域的課堂上提出嚴肅的問題,有時會受到冷落或忽視,而我就像巴雷斯一樣,並沒有習慣性地把這些輕視和性別歧視連結在一起。我從小就一直在內化有關女性和自己的訊息,可是感覺上,偏見更像是背景中的嗡嗡聲而非警笛。
後來情況改觀。大學畢業幾年之後,我努力想投身新聞界,向全國性雜誌的編輯提出想法,但全都石沉大海。我灰心喪氣,決定試著用一個男性名字寄出一篇文章,用自己來進行一次實驗。我建立了一個新的電子郵件帳號,再次向同樣的機構投稿,這一次用的名字是J.D.。在幾個小時之內,我的收件匣裡就出現了一封回信:我的稿件被採用了。我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試圖以潔西卡的名字來發表同一篇文章。J.D.卻在一天之內就辦到了。
那篇文章開啟了我的職業生涯。身為J.D.,我不僅更成功,在自我表達上也覺得更自由。我更為直接,較少道歉。我會寫只有一行的電子郵件,不多加解釋和說明。我近距離觀察到偏見及其反面──優勢──乃是具有穿透力的動態力量,不僅會從外部對其接收對象產生作用,也會從內部改變他們。可是我不擅長說謊,說謊令我焦慮,管理這種雙重身分令我疲憊。過了幾年之後,我告別了我趾高氣昂的分身,開始寫有關偏見的文章。在這個過程中,我替許多組織工作過,累積了相當多在職場上因性別而受到差別待遇的經驗,例如我的想法被歸功於他人,或是被告知我的成功純屬僥倖。
人往往是經由自身經驗所打開的一扇門而涉入與正義有關的議題。性別偏見替我打開了那扇門,當時我還不了解它在一種多層面的大規模現象裡所佔的位置。我們很容易忽視各種形式的偏見之間的關聯,由於其背景和嚴重程度相去甚遠。如同一九五六年在第一屆「國際黑人作家與藝術家大會」上,巴貝多作家喬治‧拉明(George Lamming)所作的解釋,當一個人的生活深深被一種壓迫所塑造,他很容易忽視「在威脅到他的災難和更廣泛的背景與情況之間的關聯,而威脅到他的災難就只是這個更廣泛的背景與情況最明顯的例子」。各種宗教、種族、民族、能力、性傾向、性別的人所經驗到的無意識偏見,其表現與惡毒程度有著巨大的差異,從失去工作機會到致命的身體傷害。但是在每一種情況下,那種粗暴的機制都一樣。行事帶有偏見的人是和一種預期而非現實打交道。這種預期乃是由文化中的人為產物所組成:新聞標題和歷史書籍、迷思和統計數字、真實和想像的遭遇,以及對現實的選擇性詮釋,以證實自己原先的信念。懷有偏見者眼中看見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人形白日夢。
隨著時間過去,我漸漸把偏見視為一種靈魂暴力,它不僅攻擊了個人生活的物質條件,攻擊了一個人能有的選擇和機會,也攻擊了一個人的自我意識。這種靈魂暴力在知名的「克拉克娃娃實驗」(Clark Doll Study)中有目共睹,這項研究曾在一九五四年的「布朗訴教育局案」判例中被用來作為取消學校裡種族隔離的證據。在這項研究中,心理學家瑪米‧克拉克和肯尼斯‧克拉克(Mamie and Kenneth Clark)把看起來是黑人或白人的娃娃拿給黑人小孩看。當那些小孩被要求指出漂亮的娃娃,大多數小孩選擇了白娃娃。當他們被問到哪個娃娃「看起來不乖」,他們選擇了黑娃娃。然後,當他們被問到哪個娃娃看起來和他們相像,那些小孩又選擇了黑娃娃。有些小孩心裡非常難受,他們哭了起來,或是跑出了房間。數十年後,肯尼斯‧克拉克在接受訪問時說,他們的實驗結果是如此令人不安,乃至於他們將實驗數據擱置了兩年之後才加以發表。
克拉克補充說明,雖然在這方面已經有了進步,當代的種族歧視卻更為陰險。今日的種族偏見,不管是明是暗,都繼續在改變一個人的內心經驗。如同詩人妲恩‧蘭迪‧馬丁(Dawn Lundy Martin)所寫:「壓抑成為你的一部分,乃至於你幾乎感覺不到……看見警車駛過時,你的心跳加速,而警車一轉過街角,你就感到鬆了一口氣。」偏見隨著寒冷的氣流從外在世界進入一個人的內心深處。
我愈是研究這個問題,就愈發想知道可以做些什麼來解決。遭遇偏見的人所得到的建議不勝枚舉。(給職場上的女性:行事不要太咄咄逼人,穿著展現女性輪廓的服裝!給黑人男性:把你的駕照擺在一眼就能看見的地方!)但是這些指示並沒有解決問題,只是交換了解決問題的責任。事實上,一系列的研究發現,「挺身而進」(Lean In)式的訊息使人認為職場的性別不平等乃是女性的錯,而解決這個問題的責任也在於女性。這些指示是不夠的:再大的笑容、再柔軟的毛衣、再謙虛的語氣、再明顯可見的行照和駕照,都不足以避免另一個人作出錯誤的判斷。
然而,如果那些承受偏見的人無法阻止偏見,誰能做到呢?有什麼辦法可以減少歧視本身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