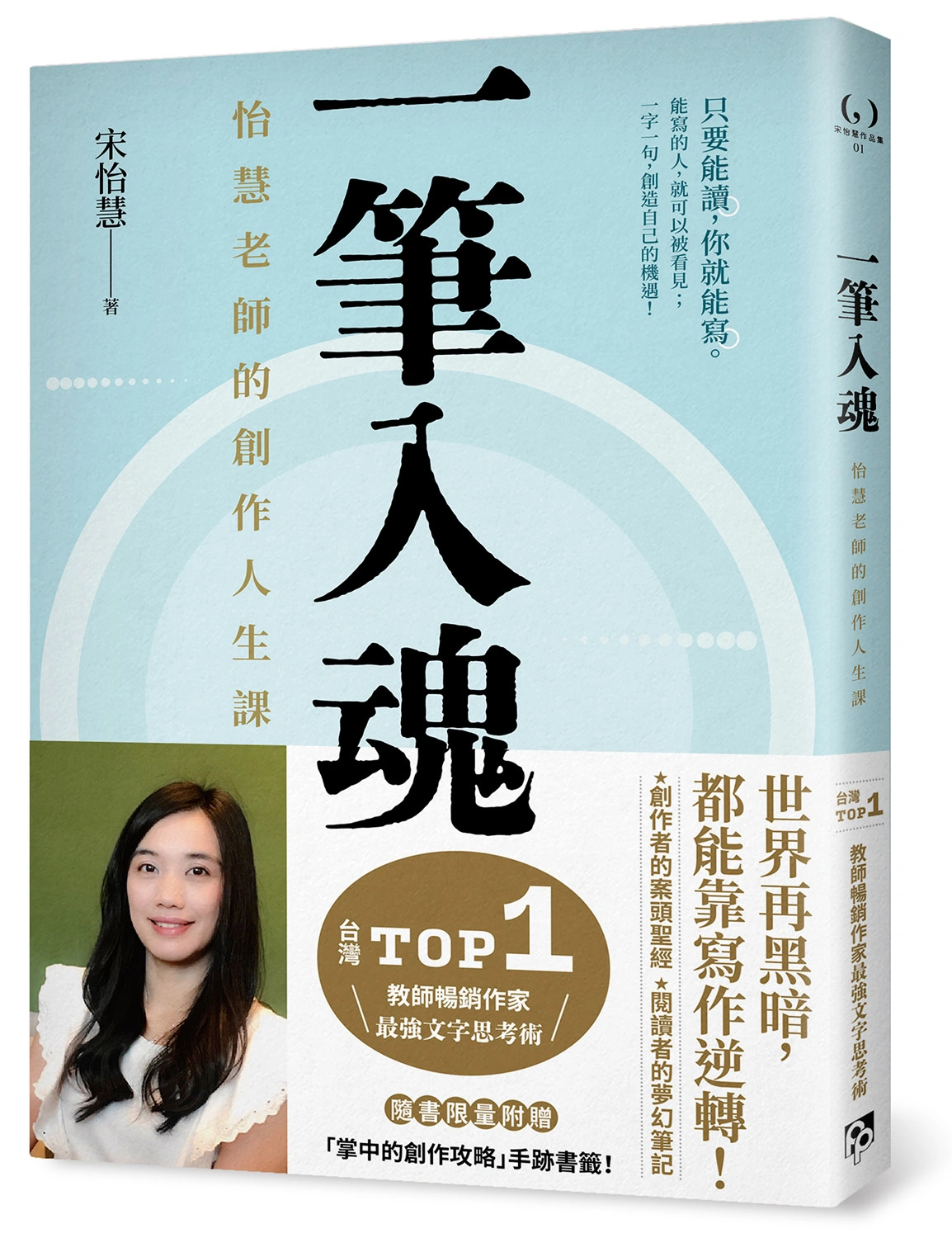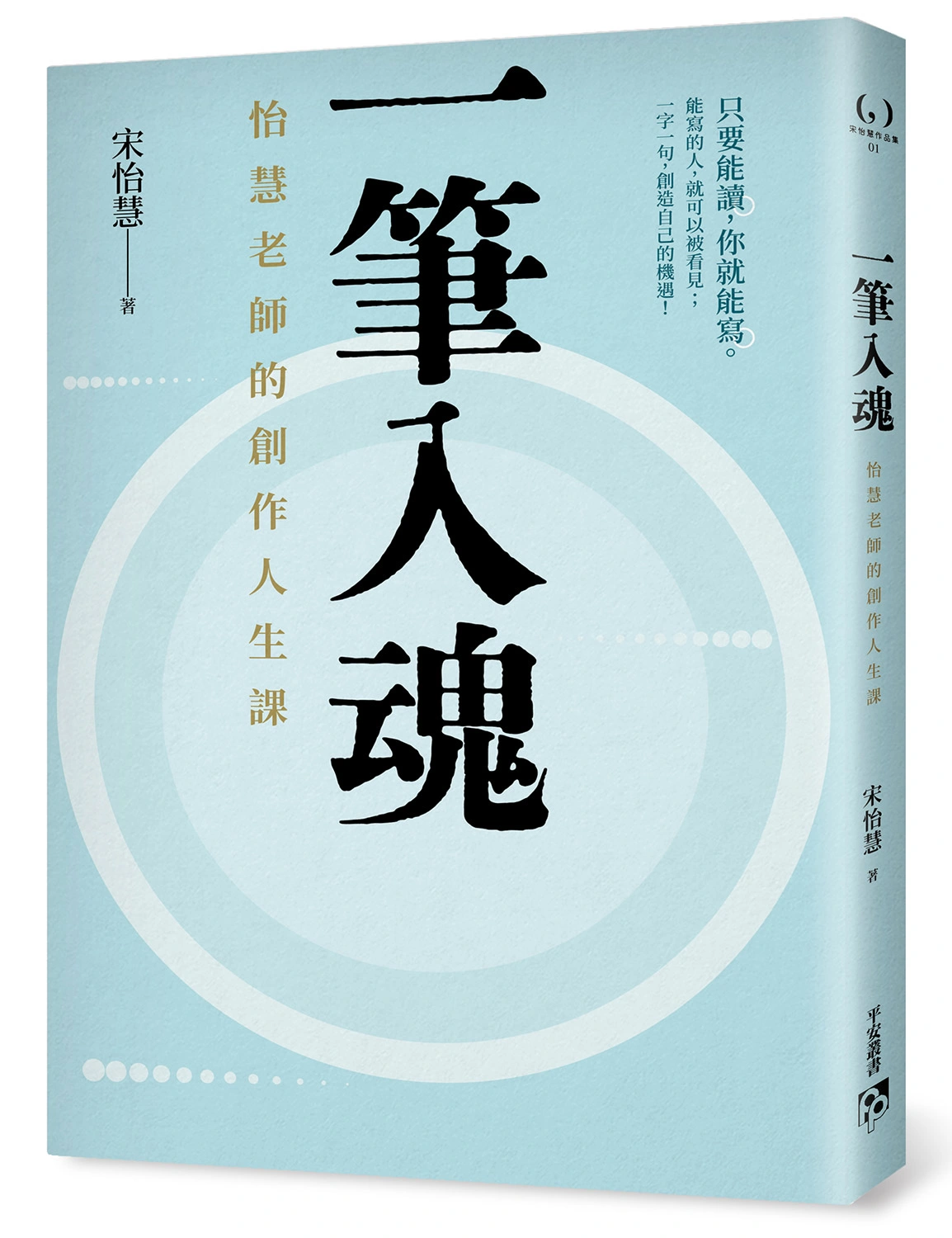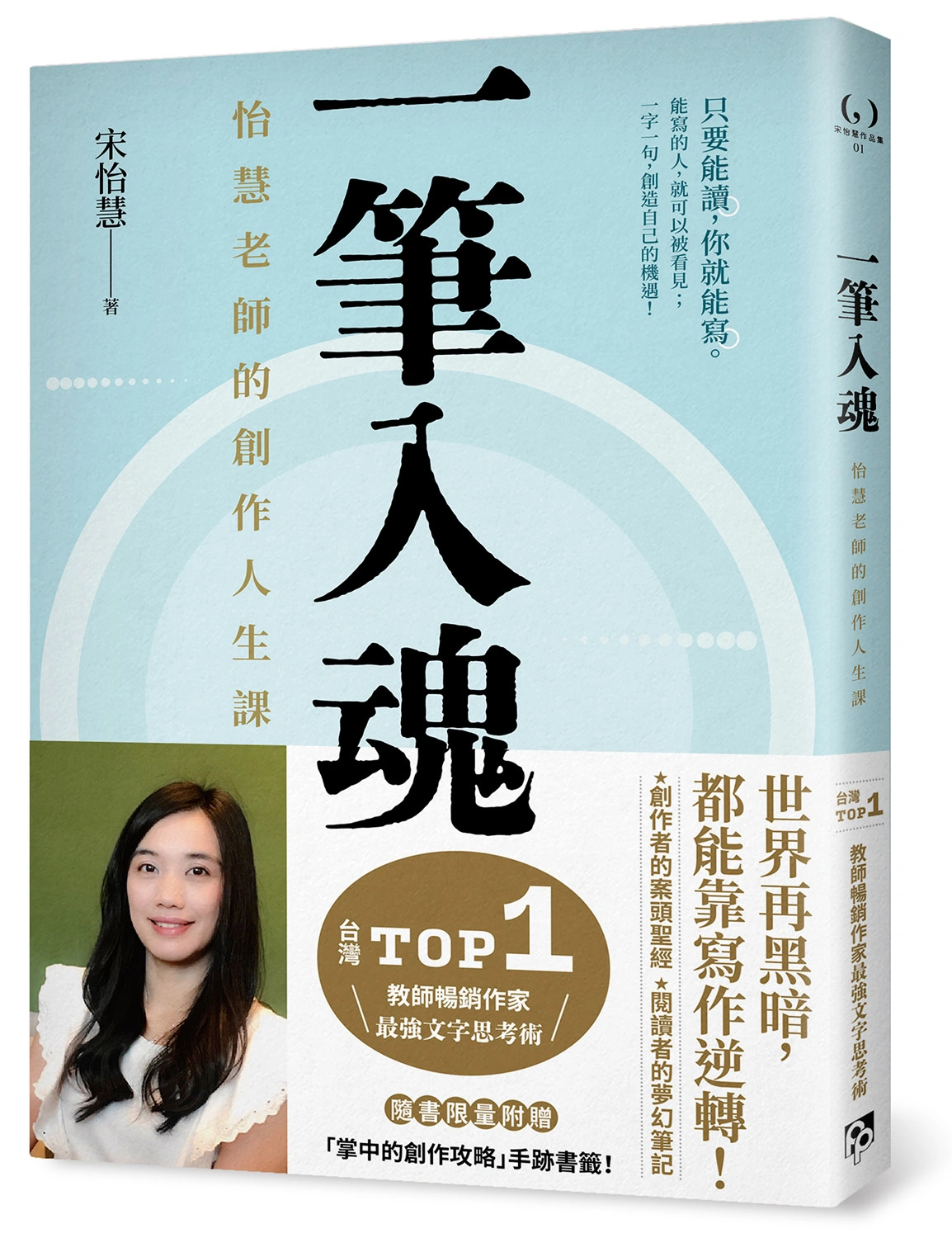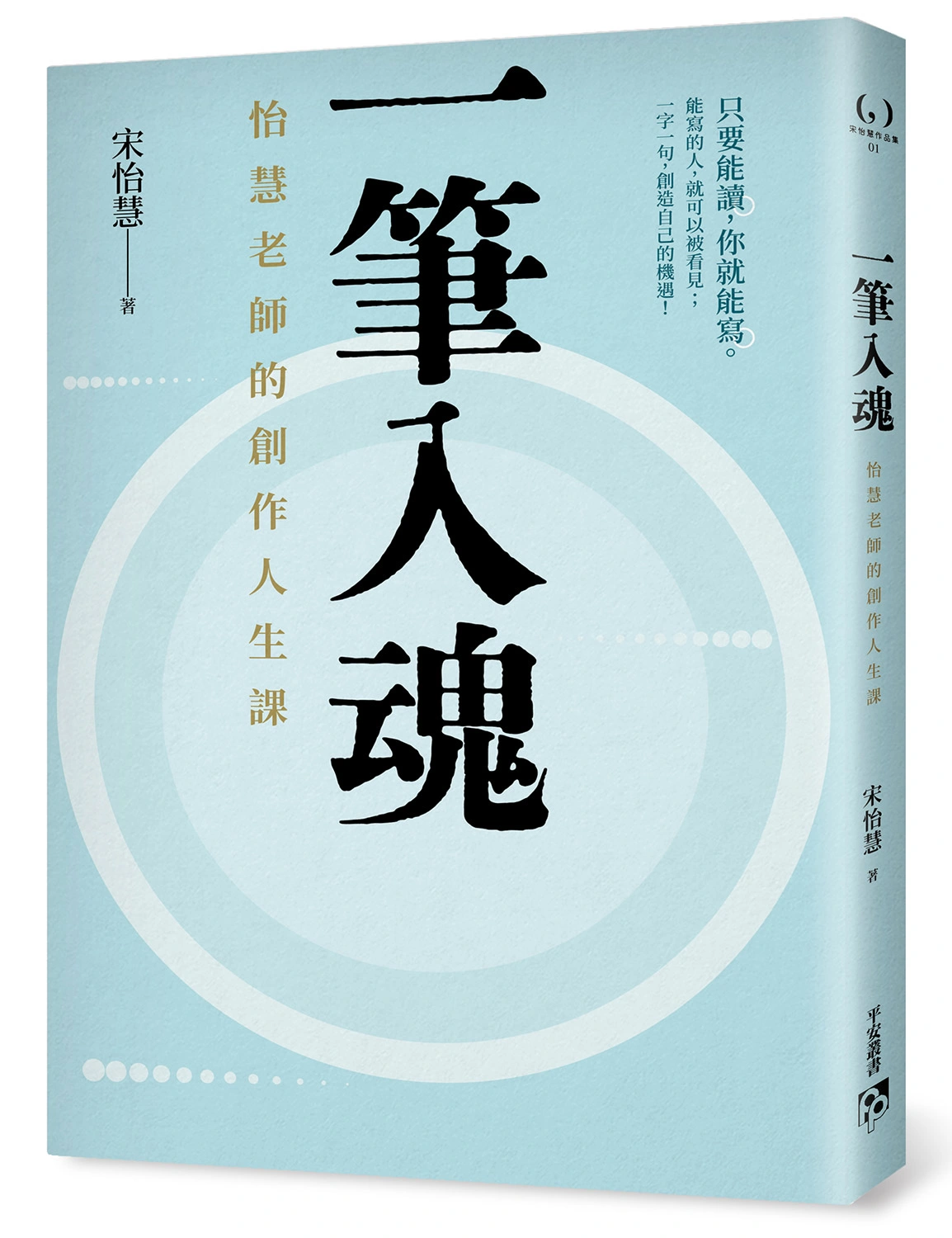內容試閱
影響世界的不是科技,而是生命的價值
另一位蘇格蘭作家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經典作品《金銀島》,企圖顛覆我們對海盜形象的既定印象,把少年冒險的嶄新視點帶入小說題材中,從尋找寶藏連結冒險之心,不斷出現善與惡、正與邪兩種心態,讓讀者思索:夢想是自我實現,還是物質滿足而已?當大海盜西渥弗與失去父親的少年吉姆從相識到衝突,從衝突到磨合,單純的「尋夢」,也變成自己的內在價值的追尋。小說家栩栩刻劃了大海盜西渥弗,這個促使主角乘風破浪去尋找夢想金銀島的契機人物,並以「金銀島」象徵每位小孩曾經幻想過的心靈桃花源,用它來體現邪惡勢力與真善美的對抗時,我們內心的掙扎。「寶藏」是我們放棄安逸,投向冒險的動力,當我們願意認真作夢、勇敢尋夢就是開放思維促使行動的璀璨實踐,每個人都可能是自己未來的英雄。當史蒂文森寫出《金銀島》之後,他絕對不會自限於目前的寫作成就。緊接著,他在一八六六年出版《化身博士》,透過懸疑推理的全新情節,以科學家傑奇博士為主要敘寫人物,看似風光無比的人生勝利組,卻在喝下邪惡藥水之後,變身為人格扭曲的海德先生,一位是位居神龕的仕紳傑奇博士;一位是作惡多端的海德先生,兩者竟同存於一個人的生命裡,科學家的身分,創造出一個人「意識」與「潛意識」之間既善又惡的雙重人格。小說家巧妙的設計彷若解密的情節,讀者要運用現有的線索抽絲剝繭地找到真相,可疑的、真實的穿插其中。細心的讀者會發現:小說家為何不斷讓傑奇博士自言自語地吐露心聲,但從頭到尾都沒有安排「海德先生」自剖的橋段,他想以如此奇詭的寫作形式來呈現小說哪一個重要的核心思維?無論是「雙重人格」抑或是「善惡衝突」,每個角色的個性與話語權之間,作者明確地利用文字進行表態,傳達自己對於哲學、人權,甚至難以釐清的複雜善惡觀,所有的虛構,最後都會反映出小說家對真實世界的邏輯脈絡裡。
在浪漫主義的洗禮下,瑪麗.雪萊透過《科學怪人》的怪物,對強權世界提出質疑;《化身博士》則是更進一步把不合時宜的怪物設定在自己身上,史蒂文森這樣形容著傑奇:「我自己從這新生命吸進第一口氣時,就知道這個自我更為邪惡,比原本的我邪惡十倍,將原本的我出賣給我原始的罪惡。」從這兩部小說來看,真正影響世界的永遠都不是科學或科技,而是善惡價值帶來的生命決定。所有的「自以為是」,常常在創作過後,會更真實地逼創作者找到人生答案──「原來真相不是○○,是○○」。創作者對價值的自我釐清,能讓世界的真相不流於主流或非主流的兩端,而是給予讀者自己真正思考過後的書寫話語權。
AI給不出的答案,就在你的人生中
若再以讀者有感的「親情」議題,年輕新世代小說家楊富閔在《花甲男孩》熟稔地運用自己的大內原鄉為創作元素,在白話台語的敘寫風格中,融入年輕世代的新潮語彙,呈現楊富閔「新鄉土小說」的獨創風格。徐緩地道盡大內人重視家族綿密的人際關係,即將被遺忘的前代俗土故事,以及親人間的生老病死。楊富閔寫的不火不慍,不只精準勾勒農家社會隔代教養的真實風貌,將自己與祖母阿嬤楊林蘭的祖孫情深寫得絲絲入扣。影響他最深的不是父母,而是把愛藏在心底,只會不斷付出愛與情的樸實祖父母。阿公、阿嬤既是慈愛的陽光,也是守護自己的生命大傘。因而,楊富閔稱自己擁有的是地表最強的大內一姊,那位年輕守寡卻強悍多情的阿嬤,成為小說中母愛的象徵。小說整體呈現解嚴後台灣囝仔成長的歷程,新一代作家的母土拓墾成長情事──農業鄉鎮日漸隱沒光芒、蒼涼的命運,卻是楊富閔筆下令他為傲為榮的故鄉。跨世代家人之間,即便相愛,思維斷層仍帶來衝突荒謬又極度有情有愛的情節,它留住彼此的,是相互拉扯卻又和解共感的動人畫面。這類的親情題材與寫作技巧,催生出ChatGPT永遠都無法組合出來的獨創語言。
面對親人死亡的議題,劉梓潔以四千字的散文〈父後七日〉拿下當年林榮三文學獎散文首獎,甚至以作者身分完成同名電影編導的工作。這篇風格獨特的散文,劉梓潔用將近一年的時光去整理父喪後內在感受,也鮮明地呈現北漂青年因現實離家卻無從言說的鄉愁。一部優秀的作品猶如釀酒的過程,它需要極好的原料、純熟的技術、時間的等待,是既複雜又迷人的過程。一如陳芳明說的:它開闢了散文的全新版圖!劉梓潔開頭是這樣寫的:「今嘛你的身軀攏總好了,無傷無痕,無病無煞,親像少年時欲去打拚。葬儀社的土公仔虔敬地,對你深深地鞠了一個躬。這是第一日。」面對摯愛家人的離開,劉梓潔獨有的敘述風格,掌握極具魅力的語言節奏,以平日較少被提及的喪葬為書寫主軸,穿插幽默詼諧的情節,呈現台灣喪葬「有禮無理」的台式文化。它不像皮克斯動畫片《可可夜總會》以墨西哥「亡靈節」為出發,從節慶歡樂的立基來談面對家人「死亡」的意義:我們愛的人從來沒有真正離開過我們,他們只是到另一個世界等我們。劉梓潔〈父後七日〉刻劃中南部喪家面對守喪肅穆的氣氛、繁複的儀典,情節時而衝突時而逗趣,讓人讀來又哭又笑,女兒在每日每日的誦經、祭拜的忙亂時間之餘,尋回過往父女相處的點滴回憶。對已逝父親的攫心思念和不捨,並非發生在面對家人離去的當下,而是在空間與時間移轉下慢慢發酵,形成一種不能說的悲傷氛圍,以及嘴邊的瀟灑一笑,其實是對無常而不得不放下的孑然自嘆。死亡在劉梓潔筆下,已非是令人恐懼悲傷、寂然荒蕪的情調,而是在黑色喜劇氛圍裡,企圖為父喪之後,生者如何和死者從誤解到和解的歷程,以及面對未來生活,我們如何漸進入一派寧靜從容、祥和自在的新起點。關於生與死的思考,AI機器人無論多麼先進,永遠都無法給予我們滿意的應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