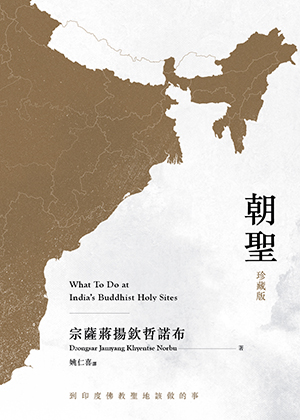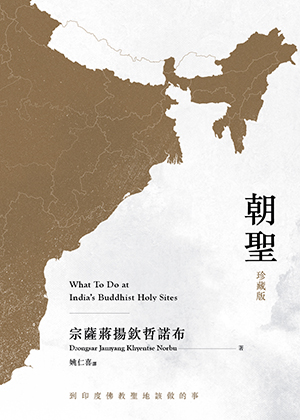內容試閱
第一部.旅程
佛教聖地
前往聖地朝聖,是數千年來所有偉大的宗教都鼓勵信徒們從事的修行。近年來,朝聖愈來愈受歡迎,部分的原因是它讓靈性追求者有個機會,享有兼具遊樂與善行的假期。對我們大部分人而言,到具有異國風情的地方去旅行,比起我們傳統所鼓吹的嚴峻修行,來得有意思多了。雖然追求玩樂不應該是前往朝聖的唯一理由,但它畢竟是個很有效的胡蘿蔔,可以誘使像我這種物質主義的佛教徒,至少做了某種型式的修行。而且朝聖也是相對容易達成的事,這就更吸引我們了。
一般而言,心靈朝聖之旅的目的,是要造訪某個「神聖」之地。然而,「神聖」是甚麼?它在何處?這會隨不同的靈性傳統和修行方式而有所改變。對有些宗教而言,由於曾經有先知出生或被謀殺在某個地點,該地就被認為是神聖之地;或者,因為有聖人加持過某根釘子或某塊木頭,它們因此成為「神聖」之物。從佛教的觀點,一個人、一件東西、甚或一個時刻被描述為「神聖」,是指它不為人類貪婪與瞋恨,或者更重要的,不為二元與分別的心所染污。因此,嚴格地說,我們並不需要尋求外在的聖地或聖人;如同佛陀親自所應允的:「任何人憶念我,我就在他面前」。當我們對佛陀與他的教法生起憶念心或虔敬心的那一剎那,他就會與我們同在一處,而該處也就會成為「神聖」之地。
然而,我們多數人的問題是,不論聽過多少遍這種說法,我們「聰明」、悲觀而且多疑的心根本就不相信,以致於我們一點都不像來自貢布的阿班(Ben of Kongpo)。阿班是屬於那種稀有的人——一個具足豐裕福德以及絕對信心的聖者,他的純真與清淨的虔敬心,使他能毫不費力地消除了制約感知的局限。他從小就心儀在拉薩聞名的覺沃仁波切1,一直聽說他的各種故事;經過多年的渴望,阿班終於得以成行,從藏東康地遠行到拉薩,前來親見覺沃仁波切。
阿班抵達供奉這尊佛像的寺廟那一天,正好四下無人,因此他得以直接走到覺沃仁波切的正前方;他凝視佛像金色微笑的臉龐,心中即刻生起極大的好感。然後阿班注意到,這位好喇嘛四周有許多供品和酥油燈,不知道是做甚麼用的。他思忖,也許這些食子和燈上熔化的酥油是喇嘛的食物,而且,禮貌上他應該跟喇嘛一起分享才對。於是,阿班就拿了一大塊食子,沾了燈上的酥油,很高興地吃下去。
接,阿班想,他應該去繞佛。可是問題來了,他必須把鞋子脫掉,卻不知道要放在哪裏才安全。他心想:「這位好喇嘛應該可以幫我看鞋子吧!」於是他脫下鞋子,放在覺沃仁波切的腳下,就前去繞佛了。一會兒工夫,看管寺廟的人回來了,他看到這雙最舊、最髒、最不成體統的鞋子,竟然放在覺沃仁波切面前,驚嚇不已。他二話不說,立刻上前想要把這雙鞋子拿開,然而,出乎意料地,當他彎下腰拿起鞋子時,覺沃仁波切開口了,他說:「不要丟掉這雙鞋子!這是貢布阿班要我幫他看的!」
最後,阿班要離開時,回到這位好喇嘛面前,謝謝他幫忙看鞋子,而且還邀請覺沃仁波切到他貢布的家鄉造訪。這尊佛像毫不猶豫地回應道:「我會去。」根據巴楚仁波切所說,覺沃仁波切翌年造訪了阿班與他太太,而後就消融至附近的一塊巨石中。從此之後,這塊石頭一直被人們認定與拉薩的覺沃仁波切一樣神聖。
像阿班這樣心地單純的故事很多。這些故事告訴我們,由於這些人有如此專一渴望的虔敬心,因而創造了聖地,甚至迎請了聖者親身示現在他們自己的感知之中。就像另外一個例子:有個人名叫洛卓,他對文殊師利菩薩有極大的虔敬心。有一天夜晚,他在書上讀到一段令他驚喜的文字,文中提到文殊師利菩薩曾經三度誓願,對於任何造訪五台山2的人,他都會親現其身。對洛卓而言,這是最美妙、最動人的發現了。他興奮異常,好不容易熬過了無法闔眼的一夜,連早飯都沒吃,就跑去上師家裏,請求上師的允許與加持,讓他前往五台山。起初洛卓的上師極力勸說他,這樣一趟充滿了危險及困難的旅途,完全沒有必要;但洛卓堅持要去。他一再地懇請上師讓他成行,上師終於放棄努力,同意了他。
在那個年代,旅行是相當艱難的。但是洛卓不畏懼任何可能遭遇的危險,打包了幾個月分量的食物和藥品,放到驢子背上,跟上師、家人與朋友道別後,便踏上橫越西藏高原的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