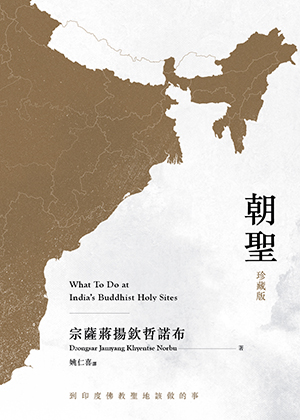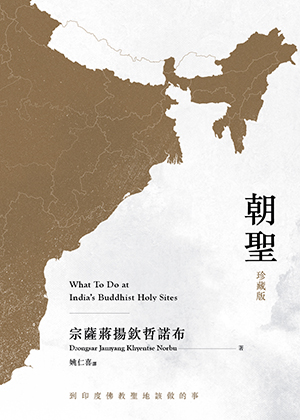內容試閱
在那個年代,旅行是相當艱難的。但是洛卓不畏懼任何可能遭遇的危險,打包了幾個月分量的食物和藥品,放到驢子背上,跟上師、家人與朋友道別後,便踏上橫越西藏高原的旅途。
一路上崎嶇難行。洛卓渡過了好幾條湍急險峻的河流,走過了好幾個炙熱乾燥、只有毒蛇和野獸相伴的荒漠。經過幾個月的旅程,洛卓終於安全抵達了五台山。他隨即開始尋找文殊師利。他一再地到處尋覓,但是卻連一個稍微貌似文殊師利菩薩的人都找不到。一天夜裏,他倚寺廟前冰冷的鐵製台階上休息,很快地就睡了。
後來他回想起來,依稀記得走進了一家很熱鬧的酒館,有許多當地人在裏面喝酒喧鬧、談天說笑。由於天色已晚、洛卓也累了,於是他想要個房間住。但是坐在走廊盡頭、小桌子後面肥胖的老闆娘告訴他,客棧已經住滿了,除非他願意睡在廊邊的角落。他滿懷感激地接受了,安頓下來,從行囊裏拿出一本書出來唸,準備入睡。
過了一會兒,一群喧鬧的少年從酒吧衝進走廊,開始捉弄這位胖老闆娘。洛卓想辦法不去注意他們,但為首的少年卻看見了他。他大搖大擺地走過來,端詳洛卓。
「你來這兒幹甚麼?」他問道。
洛卓不知如何回答,情急之下,天真地把文殊師利菩薩的誓願說了出來。這位少年聽完,大笑不已。
「你們這些西藏人怎麼都這麼迷信!為甚麼呢?」他大叫:「你還真的相信從書本裏讀到的東西!我在這裏住了一輩子,從來也沒聽過任何一個叫做文殊師利的人!」少年難以置信地搖搖頭,轉身走回那群夥伴,一邊回頭說:「冬天快到了,你最好趕快回家,免得凍死在這裏!」
於是這群人搖搖晃晃地又回到酒吧喝酒去了,老闆娘跟洛卓互相使了個眼色,鬆了一口氣。
過了幾天,洛卓再度上山尋覓,還是無功而返,在路上又撞見這位少年。
「你還沒走啊!」他叫道。
「好吧!我放棄了!」洛卓答道,露出一絲蒼白的微笑。「你是對的,我太迷信了!」
「你終於受夠了吧!是不是?」少年得意地叫道:「終於肯回家了吧?」
「我想我就去蒙古朝聖,」洛卓說,「反正就順道回家,也不會讓這次的旅途是完全浪費時間。」
洛卓看起來很傷心,他說這些話的時候,雙肩無力地向下垂。這位中國少年的心被洛卓的模樣軟化了。
「我跟你說,」他變得不像先前那麼氣勢凌人了。「你的盤纏不多了,食物也所剩無幾,你需要有人幫忙才行。這樣好了,我有個朋友在蒙古,我寫封信給他,你把信送去,我相信他一定會想辦法幫助你的。」
第二天,洛卓再度把他所有的東西打包到那頭老驢子的背上,他心灰氣餒地看了這文殊之山最後一眼,絕望中期望文殊師利終能現身與他告別,可是甚麼也沒有。在他面前匆忙來去的人群裏,除了那位帶來信件的中國少年之外,甚麼也沒出現。洛卓向他道謝,把信塞在犛牛皮大衣裏,就往蒙古去了。
走了幾個月後,洛卓來到了少年所說的地方。他把信函拿在手上,逢人就打聽收信人住在哪裏。不知怎麼回事,問到的人看了都大笑,讓洛卓非常困惑。最後洛卓遇到一位老太婆,她忍住不笑,問洛卓她是否可以打開信函,讀讀內容。洛卓把信交給她,自己卻不去看信。她仔細地讀過之後,問道:「這封信是誰寫的?」
洛卓就把事情的經過告訴了她。老太婆搖搖頭嘆口氣說:「這些年輕小伙子!總是欺負像你這樣無助的朝聖者!不過我倒是知道有隻畜牲,牠就叫做這信上收件者的名字。如果你真的要把信送到,去村子邊的垃圾堆上,就可以找到這隻豬。牠很胖,你絕對不會找不到的。」
雖然洛卓聽了一頭霧水,但是他想,既然已經來到這裏,就去瞧瞧那隻豬吧!不久,他找到了一個如山一般高的垃圾堆,頂上坐一隻長滿毛的大肥豬。洛卓打開信函,很尷尬地把它拿到那隻豬細小而明亮的眼睛前面;讓他驚訝的是,那隻豬竟然似乎真的讀起信來!豬唸完了信,開始無法控制地哭泣起來,然後倒下來,死了。洛卓突然生起強烈的好奇心,想知道是甚麼內容會對這畜牲有這麼大的影響力?於是他終於讀了這封信。信上寫:
法聖菩薩:
您在蒙古利益眾生的任務已經圓滿。請速回五台山。
文殊師利 親筆
洛卓既驚又喜,他重拾信心,以最快的速度奔回五台山,心中只有一個念頭:「這次我再見到文殊師利,我一定要緊緊抓住他,不讓他離開!」
他回到先前下榻的酒館,找到老闆娘。洛卓問她是否看到那位少年。
「那群少年總是來來去去的,誰曉得現在又到哪兒去了!」
洛卓聽了,心一沉。
「你看起來很累了,」老闆娘的語氣變得溫柔一些,「倒不如去睡個覺,明天再去找那些年輕人吧!」她把上次的那個角落又給了洛卓,他很快地就睡了。當洛卓從台階上摔下而醒來時,他才發現自己還在寺廟前,整個人都幾乎凍僵了。四下無人,沒有老闆娘、沒有酒館、也沒有小鎮。他置身五台山,這個據稱是文殊師利菩薩駐錫的外境,然而,洛卓的福德使他與文殊師利菩薩有關的一切體驗,都發生在一場夢裏。我一直希望洛卓終能理解,文殊師利菩薩的悲心是如此地廣大而遍在,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迎請他現身,即便就在自己的家鄉也行。從這個觀點來看,雖然洛卓的五台山之旅是沒有必要的,但絕對不是浪費時間。因為假若他不去朝聖,也許就經驗不到這個內在的旅程,也許也就不會有任何的了悟。
聽聞了德松(Deshung)仁波切說過這個故事之後,我造訪五台山數次,結果都比洛卓還不成功。我不僅完全無法迎請文殊師利菩薩現前,甚至連個夢都沒有。唯一發生的,是我對大部分寺廟的售票機制與售票僧人感到厭煩,尤其是看到許多神聖的殿堂被簡化為歷史紀念建築,令我極為失望。然而,過了一下子,我的智識心開始懷疑,那些只在乎門票銷售量、傲慢又貪得無厭的僧人當中,是否有一位正是文殊師利菩薩本人?誰知道呢?
在世尊佛陀入滅二千五百年後的今天,佛法修行者得以造訪許多聖地,比如我們的導師證得正覺的菩提伽耶(Bodhgaya),或他曾經說法的瓦拉納西(Varanasi),以及所有其他在兩百年前都還不太為人所知的佛教聖地。我們在這些聖地重溫歷史,大多的故事都溫馨感人而且栩栩如生,我們藉此鼓舞自己、也相互激勵。然而,並非所有的聖地都有如此振奮人心的歷史。
在西元前三世紀中葉,阿育王歷經許多血腥與征戰之後,控制了印度絕大部分的疆土。但是羯陵迦(Kalinga,現今的奧禮薩邦Orissa)的領導者拒絕降服於他的意志,於是阿育王派遣印度有史以來最強大的軍隊入侵,要把對方完全殲滅。戰爭的結果,總共有超過十萬以上的士兵被殺,無數的家庭被迫離散,阿育王贏得了空前的勝利。戰後的羯陵迦滿目瘡痍,就像在二次世界大戰時遭到原子彈轟炸的廣島一般。
當這位大王視察這一大片屍首成堆、血流成河的戰場時,他突然被一股強烈的領悟所衝擊,他了解到自己必須為這麼巨大的痛苦與恐怖負起最大的責任;最後,他終於能夠由自己的暴力所帶來的傷痛中有所收穫。他深刻的悔恨,使他成為世尊教法的追隨者,而且將自己的下半輩子,完全致力於廣揚佛法,成為佛教史上佛弟子轉化最著名的例子。如今,對於發願修持非暴力(ahimsa)的人而言,這個可怕的戰場成為真正具有啟發性的聖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