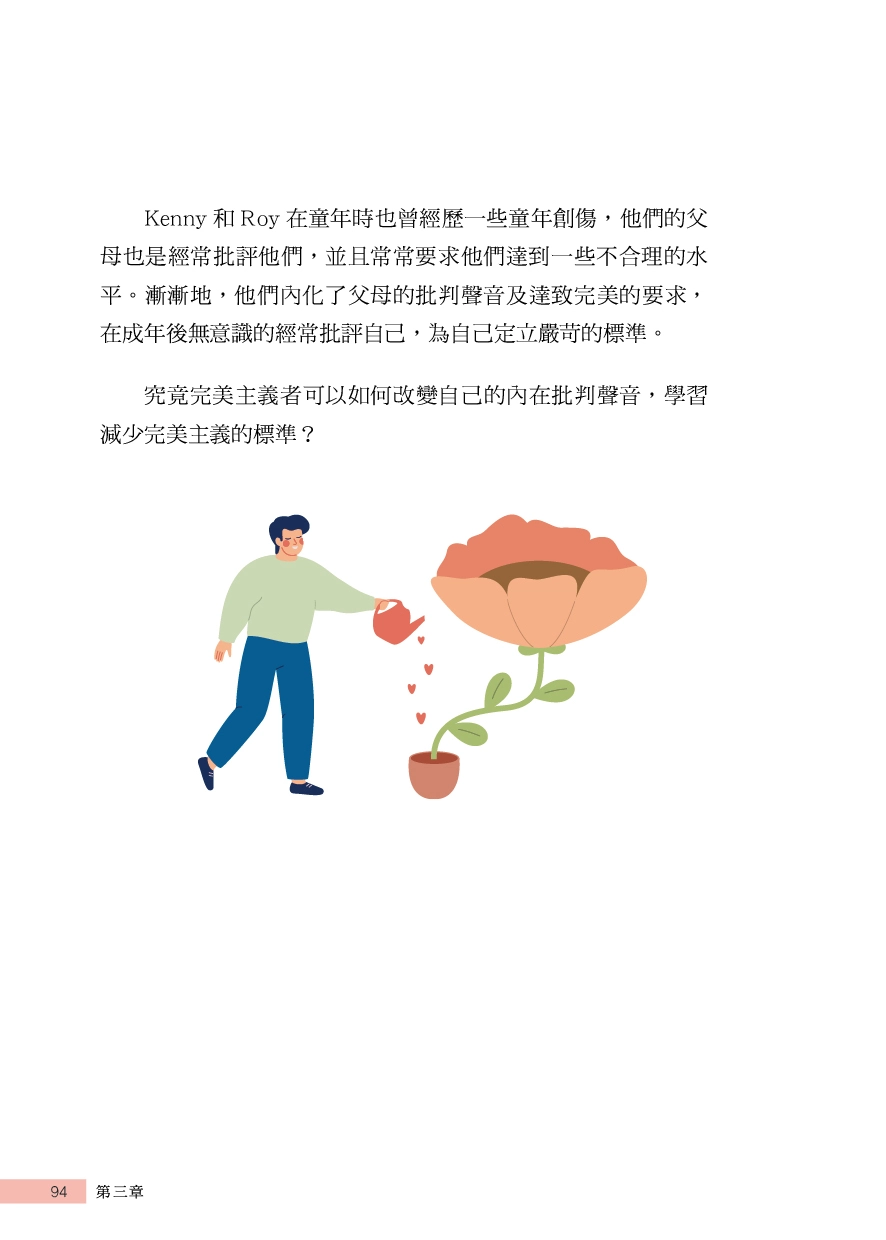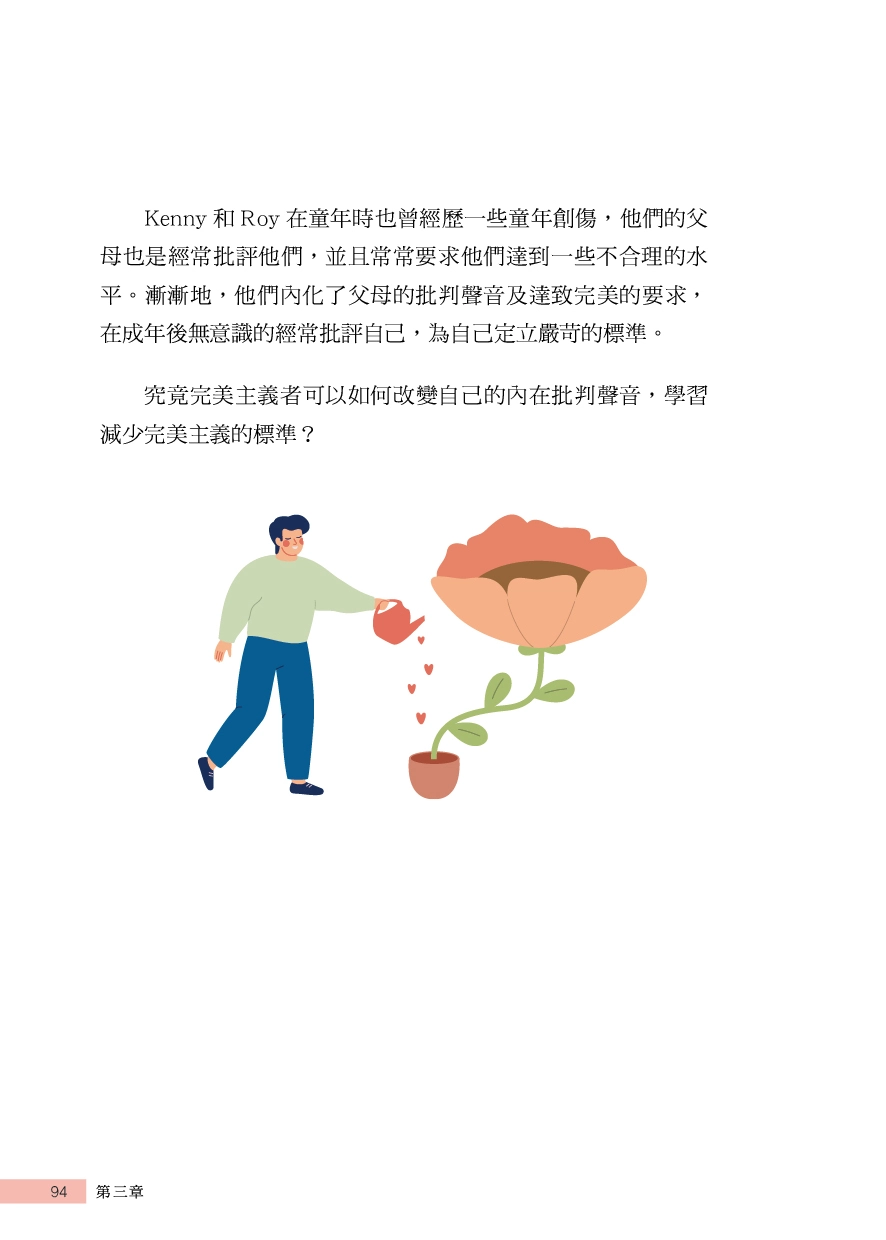正常人?異常人?
一位朋友跟我說:「透過社交媒體,我們可以更了解一個人的陰暗面。」
我回應他:「除此之外,別人的陰暗面好比一面鏡子,照出我們正在逃避自己的另一面。」
他想了一想說:「的確是,我們愈討厭的人,愈藏着我們想逃避面對的自己。」
我點點頭:「黑與白界線模糊,世上並沒有正常人與異常人之分,我們都曾經經歷一點點的創傷。」
完美的抑鬱症患者
有一次,一位年近40的女士Abby來到我的辦公室。雖然已踏入熟女的年紀,但Abby的外表看上去卻像20多歲,臉上妝容完美,一身打扮優雅高貴,叫我心裏禁不住讚嘆。
「無論我的生活有多好,也是活在抑鬱中。」她的聲音十分溫柔,總是給我一種想表現得完美無瑕的感覺。
「你看上去生活得很好,既是一位專業人士,在你的工作領域中亦頗有成就,是甚麼令你長期覺得不快樂?」我嘗試提出她話中的矛盾。
她用那雙修飾得近乎完美的手撥了撥長髮,回答說:「很多人也對我這樣說,但是我總是覺得自己沒有甚麼價值。」
她完美的外表令我有點分心,我定一定神,嘗試問道:「你已告訴過我很多關於你為家人和朋友做的事情,除了完美的外表,你還有一顆為人服務的善心,為何你會覺得自己沒有價值呢?」
她抬眼望了望窗外的風景,然後向我微笑說:「我也想知道為甚麼?我覺得自己沒有價值到不值得坐在這裏接受治療。」
在過去20多年,各式各樣的人帶着一些想不明白的事情來到我的辦公室,他們都希望能在我這裏多了解自己,好處理他們在情緒上及人際關係上的種種問題。
Abby和很多曾經經歷童年創傷的人一樣,覺得自己的價值必須建基於外在的成就或條件。例如完美的外表、成功的事業、和諧的人際關係等等。
和Abby談過幾次之後,我認為她的核心問題及一些性格特質,可能跟她的童年經歷及成長背景有關,於是我開始跟她了解她和父母的關係。
被忽略的情緒與需要
有一次,我和Abby談到她跟父親的關係,她回憶着說:「小學的時候,有一次我興高采烈地拿着一篇得到80分的作文給父親看,告訴他老師稱讚我中文作文進步了很多。」
我按常理推斷:「你的父親一定替你很開心,感到很驕傲。」
誰知她搖搖頭說:「我父親沒有反應,只是望了文章一眼,未有細心閱讀便評價我的文筆很普通。」
我想她被父親潑了冷水,一定很失望:「他這樣回應你,你覺得怎樣?」
她回答說:「我當時很困惑,認為自己不應該感到開心,覺得自己非常差勁。」
在另一節治療中,Abby想起曾經告訴母親一件事:「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我被四個女同學排擠,她們經常在我背後取笑我。我覺得很委屈,有一天決定回家告訴母親。」
我看見她好似鼻子也酸了,問:「你母親怎樣回應你?有沒有做甚麼幫你解決這個問題?」
她搖着頭說:「我母親當時忙着弄晚餐,不但冷淡地叫我不要哭,還語氣肯定地說我一定是做錯了一些事,導致她們不喜歡我。」
我開始明白她為甚麼永遠只顧幫助朋友,卻忽略了自己的感受。我接着問:「你當時會否感到很困惑?」
她點點頭:「我當時覺得自己不應該感到委屈,不斷反省自己是否做錯了甚麼。」
從我倆多次的談話中,可以發現童年時Abby的父母都忽略了她情緒及被認同的需要。
由於Abby的父母在她童年時沒有作出適當的認可,導致她長大後不斷追求完美。……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