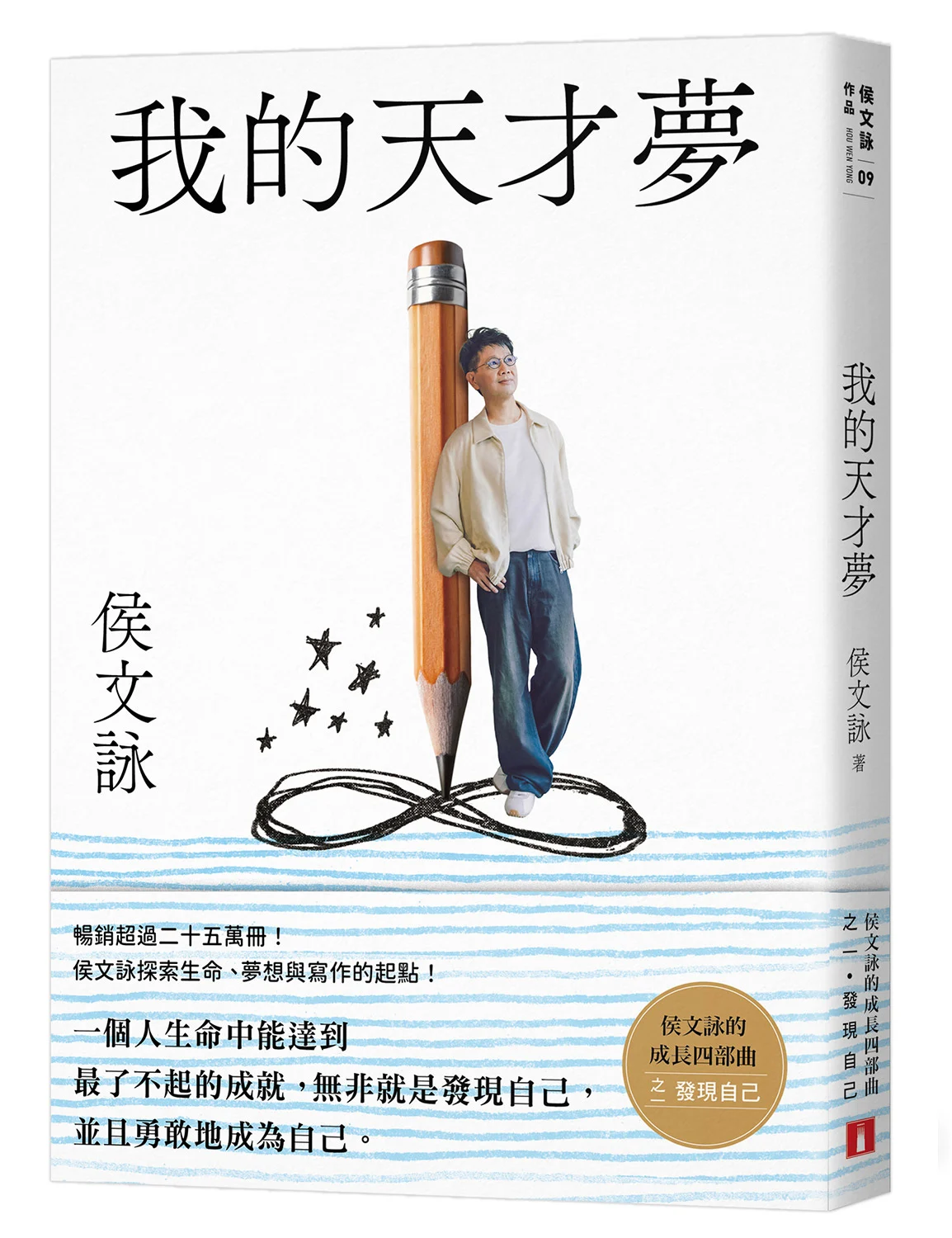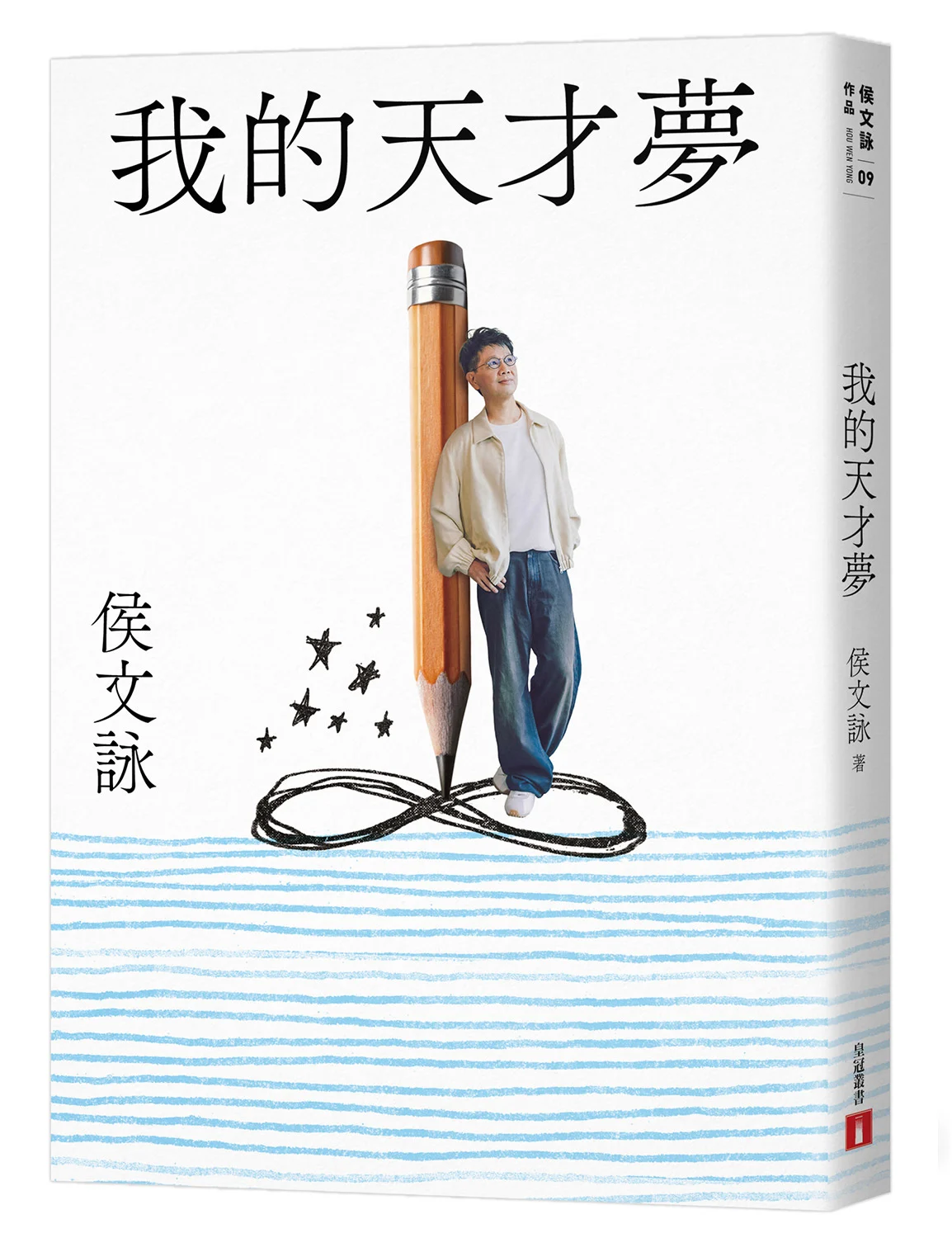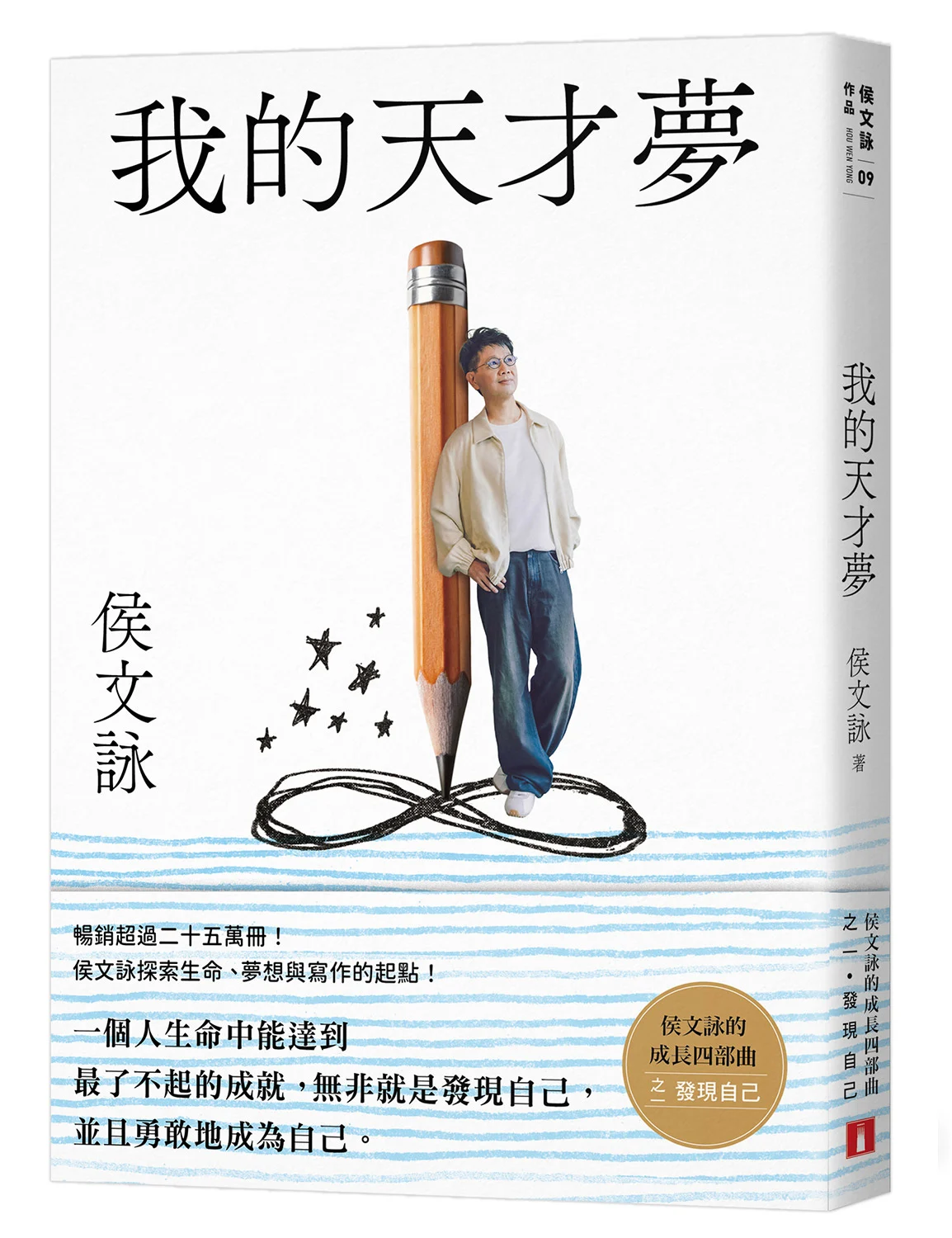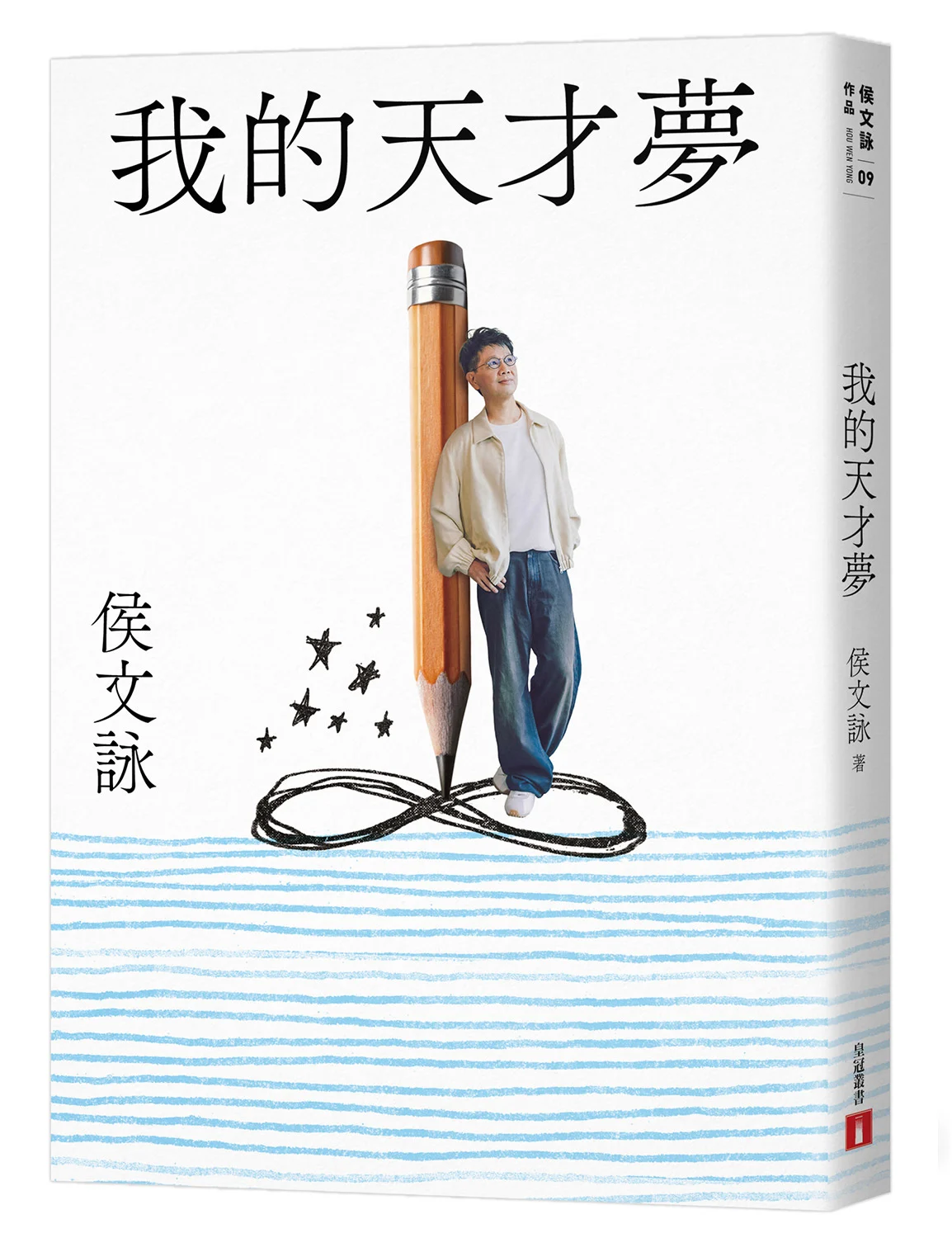內容試閱
10
上了高中以後,就不再遇到打人的老師了。可是很奇怪,雖然說沒有人用藤條逼迫你的功課,你卻可以感覺到有種氣氛不但沒有消失,反而愈來愈嚴重。
那時候,我上學總是遲到,學校的教官就在學校門口等人。在那個一元化教育的世界裡,教官的價值世界是確定而不可動搖的。
「你又遲到了。昨天晚上幹什麼去了?」教官問。
「讀書。」
「賭輸?」教官諷刺地說,「每天不讀書,只曉得賭博,當然賭輸。」
我昨天晚上真的是讀書,可是在教官的世界裡,凡是遲到的學生,操行就不好;操行不好的,成績一定不好。反之亦然。
有一次,我在行政大樓碰到那個教官,故意拉他去看我因成績優良,貼在榮譽榜上的照片。
「報告教官,那個人是我。」
教官看了看照片,又看了看我,好像看著什麼世界奇觀似地。他脫下了帽子,不可思議地抓了抓頭,終於說:
「好小子,真有你的!」
我記得後來這位教官的態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他終於明白,原來我是屬於他必須努力保護的那群好學生之一。後來哪怕是真的遲到了,他也會關心地呵護我說:
「自己身體要照顧,別讀太晚了喔!」
我常想,要是我一直留在那個被保護、照顧得很好的菁英集團裡,事情應該會進行得很順利。不過我高中的時候參加辯論比賽、英文演講比賽、排演話劇、班級合唱團、班刊、製作班旗班服、對外投稿……隨著我所參與的事情愈多,我得到的警告也就愈大。
我一直記得小學發生《兒童天地》事件時,老師問我說:
「你這麼聰明,為什麼不做點別的更有用的事?」
很神奇地,高中老師也講一模一樣的話,好像不同的老師都共同串通好了台詞似地,一點也不因時光過往,而有所改變:
「你又不是功課不好,為什麼不把時間放在有用的事情上面?」
這些善意的老師不斷地提醒我,空有才華是沒有用的,他們總是細數一些從前搞社團的、搞刊物的學長,如何荒廢了學業,如何考不上大學,如何走投無路的故事。
有用與沒有用這樣的命題對我的困擾愈來愈嚴重。特別是當同學都躲回家裡準備學校的考試,我卻還來回奔波在印刷廠和製版廠之間校訂著即將出刊的班刊,或者是為班上的運動會設計班服及班旗時,我對自己到底在做什麼愈來愈覺得迷惑……
我終於把班刊搞砸了。搞砸的原因很多,我自己沒有經驗,從邀稿到完稿到製版印刷拖了太久的時間,物價一直飆漲。我又遇見偷工減料的印刷廠老闆,印出不完美的成品來。本著要求完美的個性,我堅持要和老闆談判重新印刷。
我記得我透過學校師長找他出來談判時,那個老闆不但不覺得不好意思,他還大剌剌地說:
「侯文詠,我把你害慘,也被你害慘了。」
這麼一拖的結果,班級從一年級升級成為二年級了,不但同學人馬改變,導師也不同了。可是我們的班刊還在講著上個班級的事情和內容。搞砸的結果,只好要求加收班費,以應額外的支出。
最倒楣的是有些同學才加入我們這個班級,莫名其妙地就要被收錢。還有一些原來支持班刊的人也不願意再繳錢。另有一些人完全沒有參與編輯的樂趣,從頭到尾都聽到班刊編輯的一些烏龍事。還有一些人純粹是針對我個人的行事風格有意見……總之,一時之間,怨謗之聲鼎沸。我變成了拿別人的錢在出自己風頭的主編,或者獨斷卻又無能的人,甚至有人直指我收了外面廠商多少好處……
很多在班會公然指責我的人乾脆公開不和我講話了。我每天到班上上課,面對著許多冷冷的面孔,像是一座又一座冷冷的牆。
如同關心我的老師所預言的,我的成績一落千丈。那一學期我得到了十三名的名次,在我的考試史上從沒有發生過的慘劇。我在南部溫和的父親並不曉得他的孩子去台南讀高中,經歷了這些風波。他看到成績單時顯然愣了一下。不過他最激烈的反應也只是問我:
「我有沒有看錯,是第一名,還是第三名?」
「是十三名。」我淡淡地說,低下了頭。
「你知道是十三名,」爸爸緩緩地把成績單還給我,「那就好。」
我安靜地坐著。自己和自己常常陷入某種激烈的衝突之中。有一天,我問父母親:
「你們這輩子最大的期望是什麼?」
「我們把小孩扶養長大,看到你們有成就,對社會有貢獻,我們就很高興了。」
他們簡單的回答常讓我有一種罪惡的心情。我的父母親是標準的公務人員,如果他們一輩子可以那樣,為什麼我不行?為什麼我不能不管其他,只把書念好,然後長大,有成就,對社會有貢獻?
「你們難道都沒有自己的夢想嗎?」我問。
「我們小時候上課,一天到晚防空警報,躲美國飛機,那時候要好好地活著,好好吃一頓飯,還真不容易。有時候我覺得你們這一代人在福中不知福,不曉得都在想些什麼?我記得當初跟你爸爸結婚的時候,什麼都沒有,現在我們擁有房子、這麼多東西,還有你們這些小孩,我們已經感到很滿足了……」
有一位對我很特別的文史科老師,他有一次告訴我說:
「你是塊特別的料子,我覺得你應該放棄理工,鼓起勇氣走文史哲的路。你當個醫生或工程師也許只是稱職的專業人員,可是你走文史哲的路,我相信你一定有機會闖出個名號來。」
很奇怪,得到這麼高的評價,照說我應該覺得很興奮才對。相反地,我卻沒有。那是一個成績好的學生都拚命往理工科擠的年代,我開始懷疑自己的能耐。有沒有可能我在文史哲的領域根本闖不出一個名號來,變成了一個一無是處的人呢?
會不會走上理工科,將來做一個現世安穩的工作,完成一個合理的夢想,勝過千百個不安的狂妄而不實際的想像呢?如果我的一生是一個醫師,一個工程師,在我臨終時,至少我可以清楚地指出,我完成了哪些工程,救活了哪些人。可是如果我的一生是一個作家,我會不會只留下一些沒有用的喃喃囈語,連我自己都沒有把握是幫了人或害了人呢?
迷迷糊糊走著人生,你還可以有種迷迷糊糊的興致和樂趣。可是有一天,忽然有人指出來,明擺著兩條分別通往不同地方的路,並且有個明確的分叉點,問你要走哪個方向?
你開始徬徨了。
一條呼應著你的內心的路,從不許應你任何未來,一眼望去,遙遠而看不到終點。另外一條路,遊戲規則清晰而明確,你只要保持領先,很容易就聽到了外在的掌聲。
To be or not to be? 你在乎的又是什麼?
11
我終於拒絕了這位老師善意的建議。
高中最後的一年,我停掉了所有的課外活動。我不再寫東西,不再在班上主動發言,或談論任何和考試不相干的事。我唯一能感受到的是七月的大考離我愈來愈近,我專心啃書換取分數,想盡辦法爭取在有用世界裡面最難取得的資源,競爭大家千方百計搶奪的名次,以及那個名次所能優先分配的權益。
八月分,我的名字出現在大學聯考醫學系的放榜名單時,爸爸很高興,在家門口掛起了一串鞭炮。儘管我再三違拗,他還是執意把鞭炮點燃。
那是我最多愁善感的年代。在煙霧彌漫中,我有點感傷,覺得很不划算。我一直印象深刻,那時候,我想起我失去的青春年少再也回不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