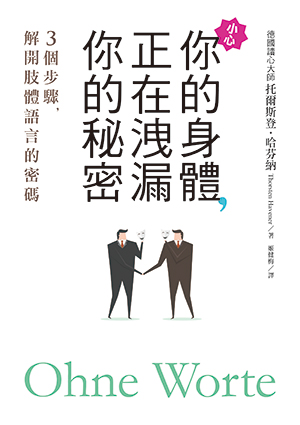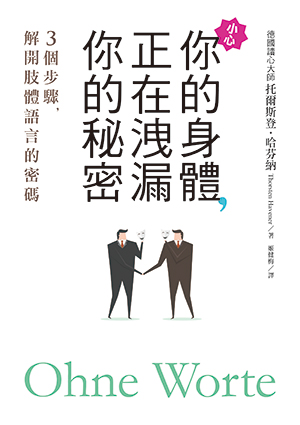肢體語言的簡短文法──寫給養成中的肢體語言口譯員
談到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奧地利心理學家瓦茲拉威克(Paul Watzlawick)研究得比誰都透徹。他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他說過一句常被引用的話:「我們不可能不溝通。」不管我們做什麼,我們總是不斷在告知身邊的人一些訊息──就算我們什麼也不說,還是傳達出了一些訊息。當你走進一個地方,裡面都是你認識的人,而你沒有跟他們打招呼,沒有跟他們攀談或是對他們微笑。在這種情況下,你所表達的訊息就是你沒有說話。
而就算你沒有微笑,也沒有看著任何人,你仍然帶著某種表情,擺出某種姿態,這種表情和姿態是我們溝通中的固定成分,強調出對我們重要的事,使抽象的事物變得更清楚。你不妨試著描述一下去火車站要怎麼走,而不要用到手臂和雙手。你會發現這很難做到,你必須刻意去要求自己不用手勢才行。
在溝通上,尤其是在肢體語言上,最令人吃驚的是我們很少意識到自己所做的事;一切幾乎都是不自覺地進行。而由於這種行為大多不由自主地發生,我們也就很難加以控制。基於這個理由,相對於口說的陳述,我們會覺得肢體語言更為真實。一個人也許能做到不在言語上被逮到說謊,在肢體語言上要做到這一點就比較困難了。
當我們要刻意去做平常一向本能去做的表情和手勢,就格外會察覺我們使用表情和手勢是多麼地不自覺。在這種時候,肢體語言甚至會變得相當好笑,至少是對旁觀者來說。某個人參加了一個肢體語言研討會,之後他有可能忽然不想再把雙臂交叉在胸前,因為他在研討會裡聽到這是個表示拒絕、與人保持距離的姿態(稍後你就會知道並沒有這回事)。有趣的是,當此人忽然很想交叉雙臂,但如今卻是在深思熟慮之後來做這個從前自然而然擺出的姿勢。現在他會想:在此刻交叉雙臂真的會很舒服,可是研討會那位親切的講師說過我不可以再這麼做!那我現在該把手臂往哪兒擺呢?好吧,我就讓手臂自然下垂。噢,天哪,這看起來真蠢。現在我要把一雙手擱在哪裡?對於旁觀者來說,這一幕的確很好笑。
而對那個不知道該把手臂放在哪兒的人來說,問題還不僅止於此。他不再聽得見和他交談的人正在說些什麼。他太過專注於自己身上,怎麼還聽得見對方說話?而對與他交談的人來說,事情就不再好笑了。這人不見得是朋友,也可能是主管,對方會想:這是哪裡來的怪咖?也難怪對方會這麼想,因為那人開始不安而無目的地擺動雙手,完全失神落魄,顯得心不在焉。而他也的確是心不在焉。儘管他參加過肢體語言講習,與別人的溝通卻沒有改善,反而惡化了,正因為他刻意想去改變自己平常不自覺的行為。
我們不斷在溝通、思考、說話,用我們的嘴,也用我們的身體。我請問你:在動念之後是先有話語,還是先有動作?根據我的觀察,這個順序在每個人身上都一樣:心念──動作──話語。
如果你氣得要命,那麼在你身上就會是這種情形:
①大腦察覺你非常生氣。
②你伸手去捶桌子。
③你說:「夠了!」
如果你忘了什麼:
①大腦察覺你忘了什麼。
②你伸手去拍額頭。
③你說:「我真差勁。哈芬納在他的書裡介紹過那麼棒的記憶技巧,我也全都讀過而且記住了,儘管如此,我還是想不起來我有沒有把熨斗的插頭拔掉!」
但凡在不假思索的情況下,就會是這個順序。舉例來說,對方可以藉此看出你是否是真心真意。如果你遇見某個人,而你很高興見到對方,通常的順序會是這樣:你看見了對方,你露出笑容,然後才朝他走過去。如果你不是真心感到高興,你會先朝對方走過去,然後才開始微笑。我們全都不自覺地能看出對方是否在演戲,因為我們對此……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