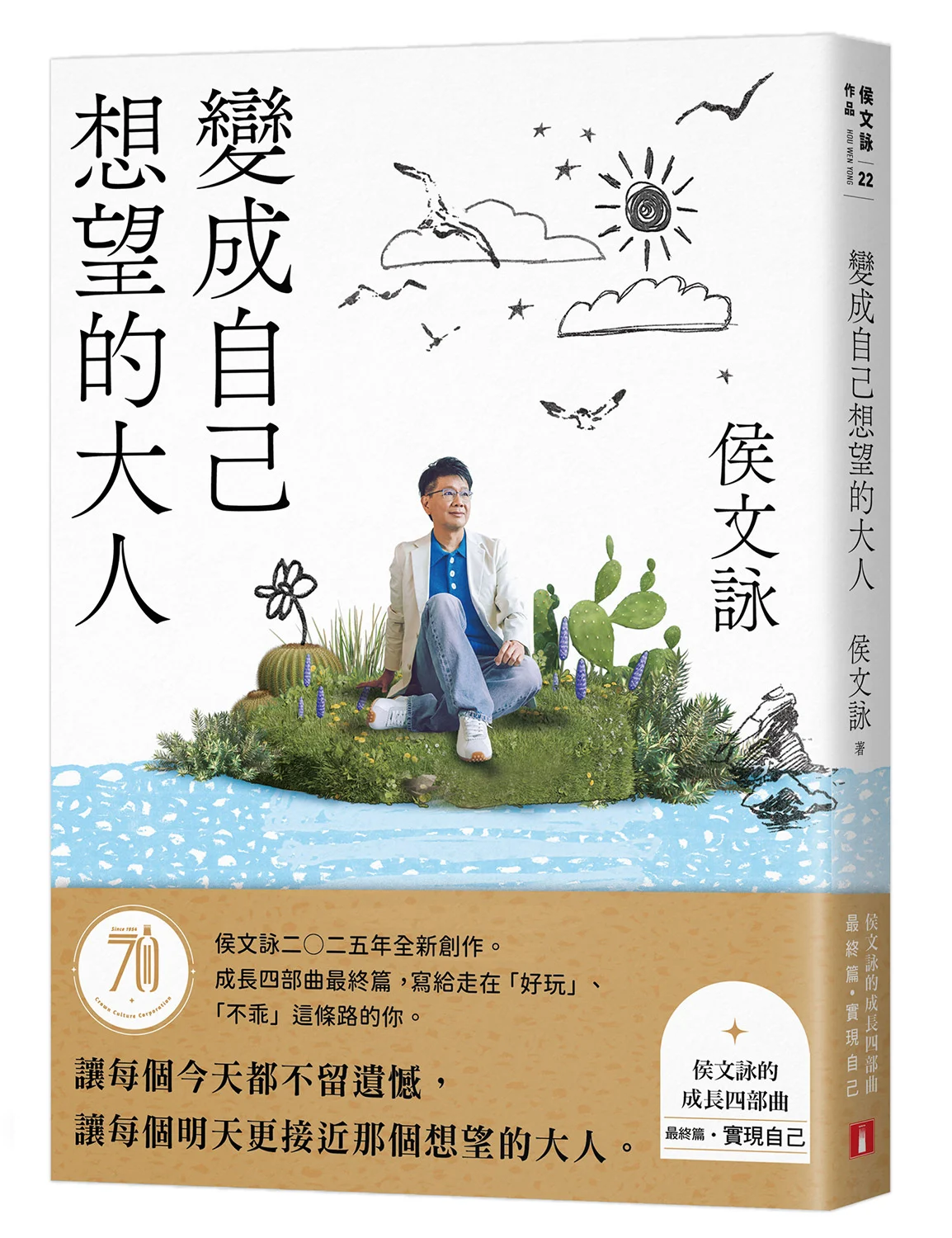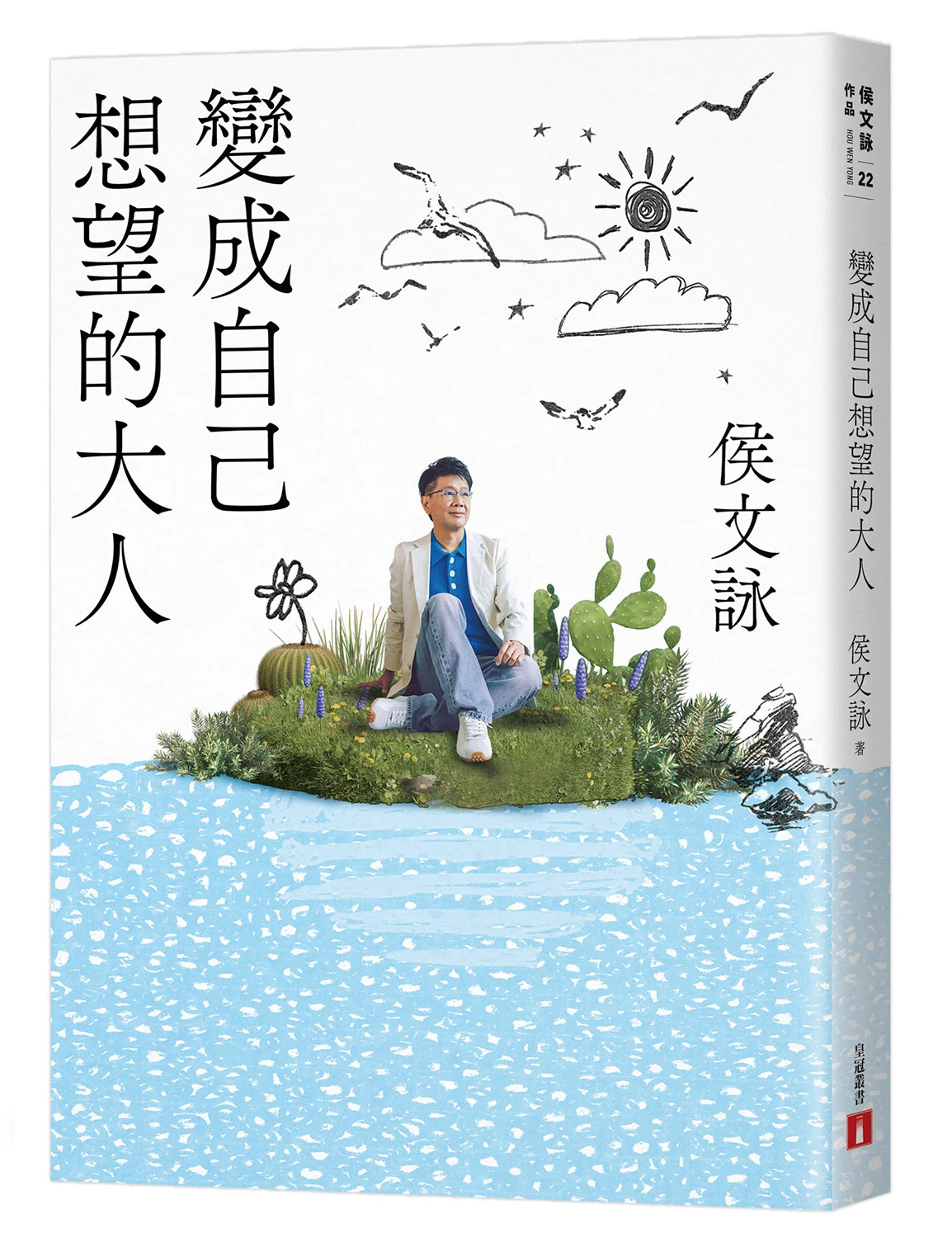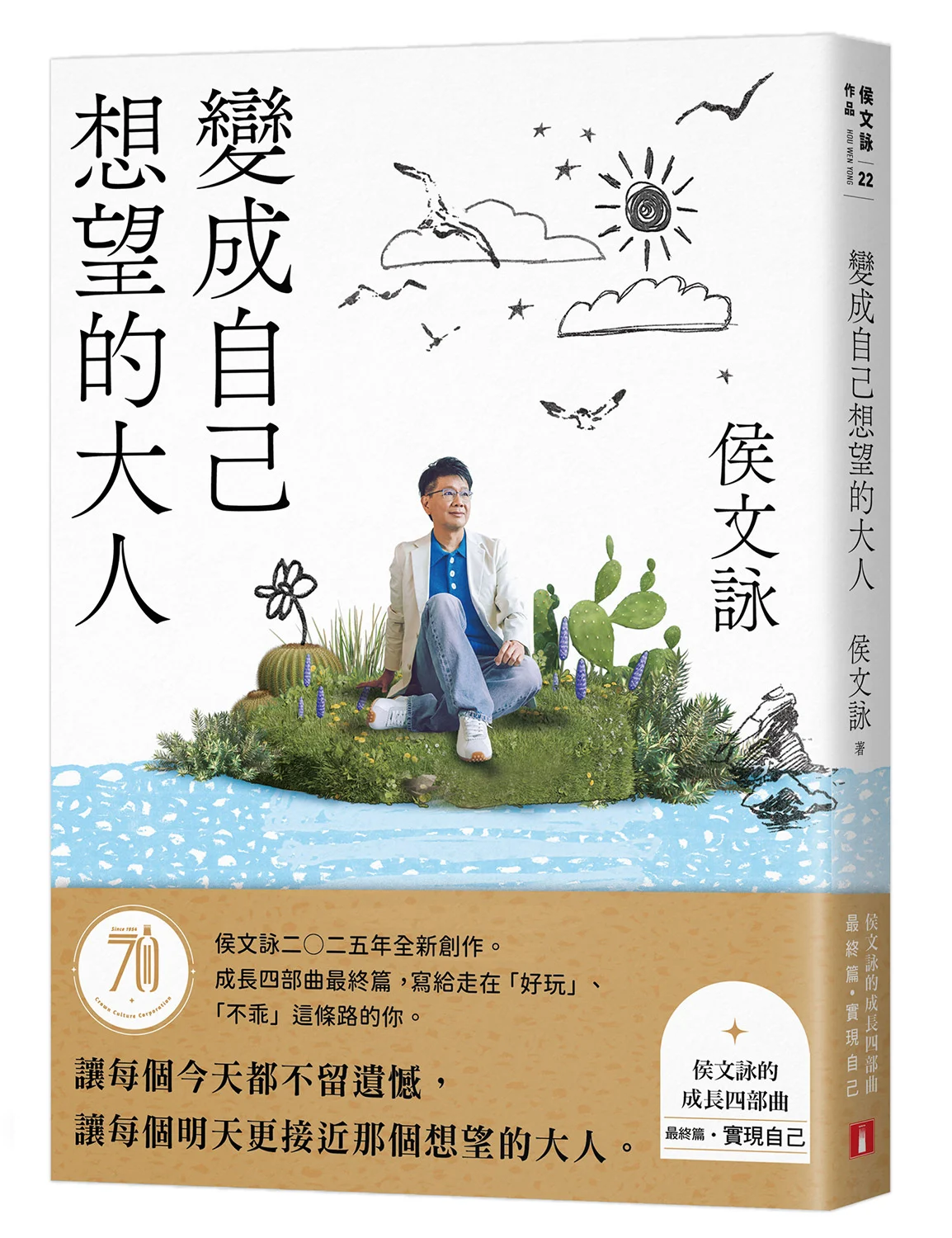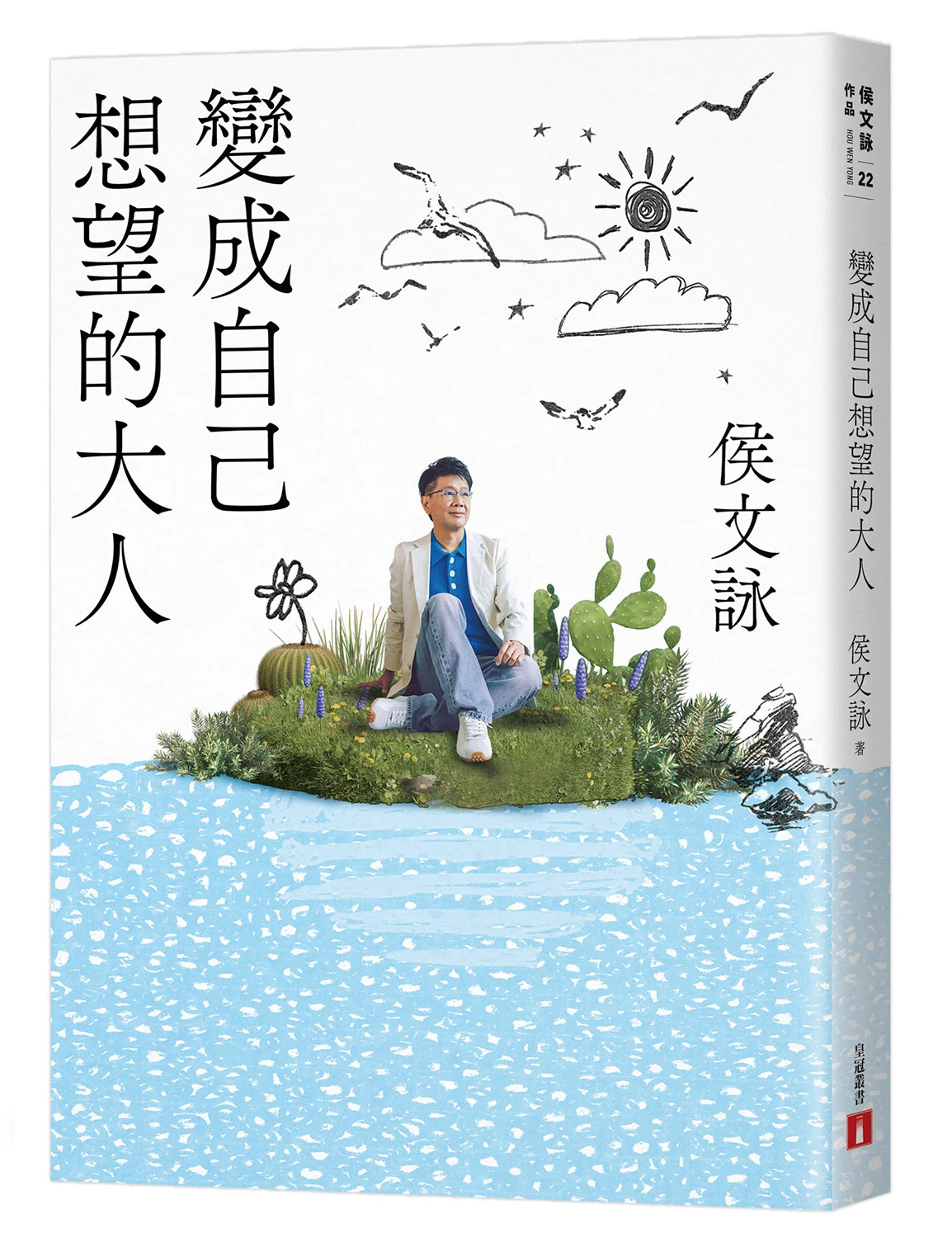內容試閱
矛盾的是,這種真實存在的感覺。在我所存在的另外一個「努力」的世界裡,卻是虛幻的。一百分的國文考題分布中,作文就占了四十分,其餘的六十分才是國文課本外加中國文化基本教材(《論語》、《孟子》)。
我參加大學入學考試是一九八○年的事情。當時作文題目的命題,基本上,跟清朝末年科舉的題目,差異不大。就以我應試的前七年作文的題目來說,分別是:
曾文正公云:「風俗之厚薄,繫乎一二人心之所嚮。」試申其義(一九七三)
「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試申其義(一九七四)
言必先信,行必中正說(一九七五)
仁與恕相互為用說(一九七六)
一本書的啟示(一九七七)
人性的光輝(一九七八)
憂勞所以興國,逸豫適足亡身(一九七九)
當時我們想盡辦法拿到考古題還有作文的範例,把它當成練習題的答案似的,試圖把握其中公式般的規律、背下其中的經典句型,好在將來正式的考試時,也能用那樣的口氣,板著臉孔說話。
輪到我應試那一年(一九八○)國文作文考題是:「燈塔與燭火」。
在考場看著題目,我愣了幾分鐘。
燈塔跟燭火都跟光線有關。一個大,一個小。燈塔只能用來照明、指引方向,燭火卻有多種用途。用民主時代的邏輯來思考的話,這個題目的脈絡應該是:
到底燈塔(政府)應該為燭火(個人)服務,還是燭火(個人)應該犧牲自由與權益,配合燈塔(政府)的權力與目標……
當時台灣還在戒嚴時期,一黨獨大的國民黨政府仍然堅持「反攻大陸」的目標。回到當時的歷史脈絡,就在前半年才發生了美麗島事件,參與的主事者(這些人後來都變成了民進黨的大老或顯耀的政治人物),全被用叛亂的罪名判處了徒刑……
不追隨那個主流脈絡,冒險地寫出自己內心的想法固然有機會得到高分,但更可能閱卷老師根本不認同我的觀點,給了我懲罰性的分數……
大概過了三分鐘左右,我窩囊地決定選擇了那個政治正確、風險最小的脈絡。
個人像燭火,光芒雖然微小,卻是社會基礎。燭火如果聚合起來,就能形成巨大光芒,像燈塔一樣放出巨大的光芒。作為社會國家的一分子,如果我們也能夠服從在大有為政府的領導之下………
那些夸夸而談的大話我寫得還算流暢,最後我似乎還寫了反攻大陸,解救同胞這一類的文字。我知道我寫的作文內容平庸,但平庸就是我保存「努力」的戰果,最佳的防守策略。
一個多月之後,我收到了成績單——作文的部分,我得到了跟大部分的人平均差不多的分數。靠著其他科目較高的分數,我如願地考上了醫學系。
那一年,我從南部到台北念大學。之後的一、二十年間,台灣的政治經濟正發生重大的變化,民意代表改選、總統直選,政黨輪替即將開始。各式各樣的選舉造勢場合、演講、抗議示威遊行,讓人目不暇給。此外,蘭陵劇坊、雲門舞集、表演工作坊、各式各樣的影展、演唱會……也都在我眼前的世界,繽紛燦爛展開。
開學沒多久,我在耕莘文教院聽到了黃春明老師的演講。
當時晚上八點檔的黃金時段有一齣電視連續劇收視率高達40%——這意味著,光是台北市就有八十萬人坐在電視機前面收看連續劇。八點十分,當第一個廣告進來時,許多人起身上廁所,上完廁所之後,當然就是按水沖洗抽水馬桶。
「我有一個朋友在自來水公司做事,就在八點十一分的時候,觀察到自來水廠蓄水的水位陡然下降。」黃春明老師說。
接著是一陣笑聲。等到笑聲稍止之後出現的,黃老師說出了那句對我的人生很大影響的一句話。他說:
「在一個所有的人都看一樣的連續劇、在同樣時間上廁所、按馬桶的世界活著,諸位會不會覺得,這樣的人生太無聊了?」
我受到很大的鼓舞,開始參加社團、大量閱讀書籍、看電影。想辦法讓自己成為那個變化的一部分,追求擁有一個「不無聊」的人生。
我並沒有太多的時間去思考自己大學聯考作文的事。對我來說,那些事情都已經過去。閱讀過那麼多心儀的文學作品後,我告訴自己,從此我不會再為了那個「努力」的世界,勉強自己寫出任何違背心意、毫無創意的一字一句了。
那時候,我一點也不知道,那個「努力」的世界並沒有消失,它只是暫時蟄伏,將來還會幽靈似的如影隨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