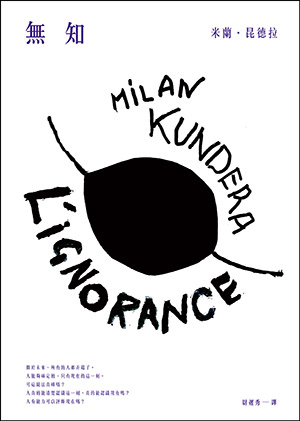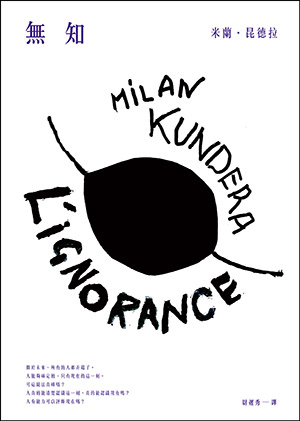內容試閱
4
打從流亡的最初幾個星期,伊蓮娜就作了一些怪夢:她坐在一架飛機裡,飛機改變了航向,降落在一個陌生的機場;穿著制服、全副武裝的男人在空橋下等著她;她額頭上沁出了冷汗,因為她認出那是捷克的警察。在另一個夢裡,她在法國的一個小鎮上閒逛,看見了一群奇怪的女人,每個人手上都拿著一只大大的啤酒杯向她跑來,用捷克語斥責她,個個都笑得那麼真誠卻又不懷好意,這時,伊蓮娜嚇壞了,她發現自己身在布拉格,她放聲大叫,醒了過來。
她的丈夫馬丹也作同樣的夢。每天早上,他們都跟對方訴說著對於回歸故鄉的恐懼。後來,伊蓮娜跟一個波蘭朋友(她也是流亡者)說起來才發現,原來所有的流亡者都會作這種夢,每個人都作,沒有例外;她先是因為這些素不相識的人們在夜裡團結友愛的表現而感動,後來卻有點不快:如此私密的作夢經驗,怎麼能以集體的方式來體驗呢?那她獨特的靈魂何在?可是問這些永遠沒有解答的問題又有何用?可以確定的是:成千上萬的流亡者,在同樣的夜裡,以無可數計的變體形式,作著同樣的夢。流亡的夢:這是二十世紀下半葉最奇特的現象之一。
這些夢魘對伊蓮娜來說,確實是神秘莫名,因為在此同時,她也為無法遏止的鄉愁所苦,她感受到的,是另一種完全相反的經驗:故鄉的景物在白晝時分兀自出現在眼前,不,這不是悠悠長長、有意識、刻意的白日遐想;這完全是另一回事:一幕幕的景物在她腦海裡兀自亮了起來,出乎意料之外,突兀、迅速,乍現即逝。前一刻,她還在跟她的老闆說話,轉瞬間,如閃電霹靂,她卻看見一條橫越田野的道路。前一刻,她還擠在地鐵車廂的人群裡,突然間,布拉格一片綠地上的小徑卻閃現在她眼前。整個大白天,這些轉瞬即逝的影像不時來造訪她,舒緩了她對失去的波希米亞的思念。
執掌潛意識和夢境的,是同一個導演。白晝,他把洋溢著幸福光影的故國景物一幕幕送給伊蓮娜,到了黑夜,他策畫的回歸卻令人驚惶,目的地是同樣的國度。白晝,那遭人遺棄的美麗國度閃耀著,到了黑夜,換成航向故國的恐怖回歸在發光。白晝在她面前呈現的,是她失去的天堂,夜晚所展示的,則是她逃離的地獄。
5
共黨國家都忠實地追隨了法國大革命的傳統,放逐了流亡者,對他們詛咒撻伐,將他們斥為最最可憎的叛徒。這些留在國外的人,都在缺席的情況下,在他們的國家遭到審判、定罪,他們的同胞也不敢和他們有所接觸。然而,隨著時日久遠,嚴厲的放逐令也漸漸弛緩了,在一九八九之前的幾年,伊蓮娜的母親──一個新寡又沒啥害處的退休公民──就拿到了簽證,在國營旅行社的安排下,去義大利度了一個星期的假;第二年,她決定到巴黎待上五天,偷偷去看她的女兒。伊蓮娜滿心感動與憐惜,心底浮現了一個年邁母親的形象,她幫母親在旅館訂了房間,還犧牲了一部分的假期,準備好好陪伴母親,片刻不離。
「妳看起來還不錯嘛,」見面時母親這麼對她說。母親一邊笑一邊又接著說:「其實我也不壞。出境的時候,邊境的警察看了我的護照,對我說:夫人,這本護照是假的!上面的出生日期不是您的!」這會兒,伊蓮娜突然在母親身上找到以往她認識的那個樣子,她感覺到,這近乎二十年的時間似乎什麼也沒改變。她對一個年邁母親的憐惜突然消失了。母女兩人面對面,宛如置身時間維度之外的兩個存在,宛如不具時間性的兩種本質。
分離了十七年之後,母親來看女兒,女兒看到母親卻不開心,這樣的女兒不是太糟了嗎?伊蓮娜動員了全副的理性、全部的道德感,好讓自己的行為舉止像個孝順女兒。她帶母親去艾菲爾鐵塔二樓的餐廳吃晚飯;她帶母親去搭遊河船,沿著塞納河介紹巴黎的風光;既然母親想看展覽,她就帶她去畢卡索美術館。在第二間展覽廳裡,母親停下腳步說:「我有個朋友是畫家,她送給我兩幅畫當禮物。妳一定想像不到那兩幅畫有多美!」到了第三間展覽廳,母親說她想看印象派畫家:「在網球場美術館有個常設的展覽。」「這個美術館已經沒有了,」伊蓮娜說,「印象派已經不在網球場美術館了。」「不是,不是的,」母親說。「他們還在網球場美術館。我知道的,而且我沒看到梵谷是不會離開巴黎的!」為了彌補梵谷的缺席,伊蓮娜提供了羅丹美術館。母親在一尊雕像前嘆了口氣,像在作夢似的:「我在佛羅倫斯看了米開朗基羅的大衛像!我站在那裡看得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媽,」伊蓮娜按捺不住了,「妳現在在巴黎,跟我在一起,我帶著妳在看羅丹。羅丹!妳聽到了嗎?羅丹!妳從來沒看過的羅丹,妳這是在幹什麼呢?在羅丹面前,妳去想米開朗基羅幹嘛?」
這問題問得一點也沒錯:母親這是在幹什麼?她和女兒在分離多年之後重逢,難道她對女兒向她展示、向她述說的事都沒有興趣嗎?為什麼要提米開朗基羅呢?她跟一群捷克觀光客一起看的米開朗基羅難道比羅丹更有吸引力嗎?這五天以來,她沒問過伊蓮娜任何問題又是為了什麼呢?為什麼她沒問過任何一個關於伊蓮娜生活的問題,也沒問過任何一個關於法國的問題,關於法國菜、法國文學、乳酪、葡萄酒、法國政治、戲劇、電影、汽車、鋼琴家、大提琴手、運動員?
母親不提這些,反而不停地提起在布拉格發生的事,提到伊蓮娜同母異父的弟弟(母親和她剛過世不久的第二任丈夫生的),也提到其他人,有的伊蓮娜還記得,有的她連名字都沒聽過。她幾次試著要把她在法國生活的話題插進去,可母親用話語砌成的壁壘毫無間隙,伊蓮娜想說的話根本鑽不進去。
打從伊蓮娜小時候,她們就是這樣了:母親像呵護一個小女孩那樣,溫柔地照拂著兒子,而對待女兒的方式,卻是十足陽剛的斯巴達教育。我這裡要說的,是她不愛女兒嗎?說不定是因為她看不起伊蓮娜的父親,也就是她的第一任丈夫?我們別這麼壞心眼吧。她是費心思量之後才這麼做的:她一副精力充沛、身強體壯的樣子,是因為她擔心女兒欠缺活力;她想藉著自己粗魯的態度,驅走女兒的多愁善感,就像一個運動神經發達的父親,把膽小怯懦的兒子丟進游泳池裡,因為他認為這是教會他游泳最好的方法。
不過,她心裡很清楚,光是她的出現,就夠她女兒受的了。我也沒打算否認,她對於自己在身體方面的優勢,有一種秘密的快感。不然要怎麼樣呢?要她怎麼做呢?要她為了發揚母愛而消失得無影無蹤嗎?她的年歲無情地向前推進,可她對自己的活力有某種自覺,就像伊蓮娜感覺到的那樣,這樣的自覺讓她整個人年輕起來。當她在伊蓮娜身邊,發現她因為感覺到這股活力而驚惶、而沮喪,她就想要把此刻延續下去,讓她崩壞中的霸權可以儘可能地延續下去。帶著一丁點虐待的心理,她刻意把伊蓮娜的脆弱當作冷漠、懶惰、散漫,還斥責了她。
長久以來,伊蓮娜只要在母親面前,就會覺得自己變得比較不漂亮、比較不聰明。她不知多少次跑到鏡子前面,只為了看清楚自己其實不醜,自己看起來不像個笨蛋……啊,這些都是陳年舊事,幾乎都快忘了,可是母親待在巴黎的這五天,這股自卑、軟弱、附屬的感覺,又再次向她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