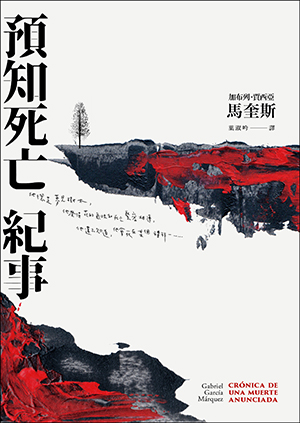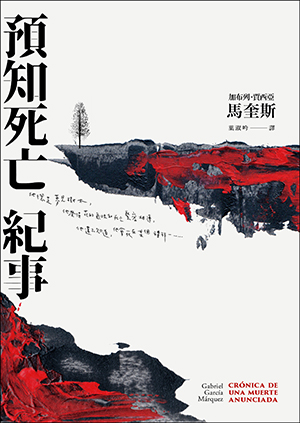內容試閱
他們殺他那天,山迪亞哥.拿紹爾一大早五點半起床,準備迎接主教搭乘的船抵港。前一天夜裡,他夢見自己穿越一片無花果樹林,天空下著毛毛細雨,剎時他在夢裡很快樂,可是醒來後他感覺淋了一身鳥屎。「他總是夢見樹木。」他的母親普拉喜妲.里內羅對我說,二十七年後,她細細回想那個令人椎心泣血的禮拜一。「前一個禮拜,他夢見一個人搭著錫紙飛機,穿越扁桃樹林,沒有撞到半棵樹。」她對我說。她擅長解夢,聲名遠播,空腹解夢尤其神準,不過她沒察覺兒子的兩個夢透露凶兆,或是在送命前幾天早晨告訴她的其他有關樹木的夢。
山迪亞哥.拿紹爾也沒發覺預兆。那晚他睡得少,也睡得差,衣服沒脫就爬上床,醒來後頭痛欲裂,嘴裡有一股銅綠苦味,他認為這是狂歡一夜種下的自然惡果,那場婚禮派對一直到午夜過後才結束。況且,他從六點零五分出門到一個小時後像頭豬遭到屠宰,一路上遇到許多人,這些人憶起他睡眼惺忪,可是心情愉悅。也許是巧合,他對每個人說這真是個美麗的一天。沒人能確定,他這句話指的是不是天氣。許多人記得那天早晨確實陽光燦爛,微風從海上吹來,穿過了香蕉園,讓人直覺這會是這段時節的一個風和日麗的二月天。可是,大多數人異口同聲地說那一天天氣陰沉,天空灰濛濛,雲層低垂,瀰漫一股雨水即將降下的厚重氣味。在慘劇發生的那一刻,天空已經飄下綿綿細雨,一如山迪亞哥在夢中樹林看見的情景。我也參加了婚禮派對,警報鐘聲響起時,我窩在瑪莉亞.阿蕾韓蒂娜.塞萬堤斯眾人躺過的懷裡歇息,睜不開眼,還以為那是歡迎主教的鐘聲。
山迪亞哥穿上一件褲子和一件白色亞麻襯衫,兩件衣服都沒漿過,打扮一如前一天參加婚禮。這是他出席特別場合的服裝。要不是主教光臨,他應該會穿上卡其服和登山靴,照例在禮拜一去天使臉孔,那是他從父親那兒繼承來的牧場,不是什麼大事業,卻經營有方。上山時,他通常腰部插著一把點三七五麥格農子彈手槍,他說這種穿甲子彈能將一匹馬攔腰截斷。狩獵山鶉季節,他也會帶著放鷹打獵的工具。他的櫃子裡還有一把點三○○六曼利夏.施奈爾獵槍,一把三○○賀南麥格農獵槍,一把有兩面準星的二二黃蜂獵槍,和一把溫徹斯特連發步槍。他學父親,睡覺時會在枕頭套裡藏一把武器,可那天出門前,他取出子彈,把槍收進小夜桌的抽屜。「他從不填裝子彈。」他的母親跟我說。我知道,我也知道他會把武器收在某處,再把彈藥放在隔非常遠的另一處,這樣一來,不但能打消屋內有人想裝子彈的意圖,也一併杜絕意外。這是他父親立下的家規,因為某天早上有個女僕脫下枕套時,甩了甩枕頭,手槍掉落地板射出子彈,失控打中房內的衣櫃,射穿客廳的牆壁,伴隨著戰場上震耳欲聾的隆隆聲,穿過鄰居屋子的飯廳,飛越廣場,把另一頭教堂聖壇上一尊真人大小聖人像,炸成一堆石膏粉末。當時,山迪亞哥.拿紹爾年紀很小,他永遠忘不了那次災難學到的教訓。
他的母親對他的最後印象,是他踩著急促的腳步走進臥室。她聽見他在浴室摸索著想找出藥箱裡的阿斯匹靈而完全清醒,她打開電燈,看見兒子拿著一杯水站在門口,往後她一直記得這一幕。就在這一刻,山迪亞哥.拿紹爾跟她說起他的夢,可是她沒特別注意夢裡的樹木。
「凡有關鳥的夢都象徵健康。」她說。
她凝視兒子,如同此刻躺在同一張吊床上,只是當我回到這座遭到遺忘的村莊,試著重新拼湊多如鏡子摔碎後的殘屑記憶,見到的她已是風中殘燭。即使是大白天,我也認不出眼前的輪廓是她,她的兩邊太陽穴貼著草葉,兒子最後一次進來臥室後,留給她永遠治不好的頭痛。她側臥,抓住吊床的繩索想坐起來,昏暗中一股浸禮池的氣味襲來,像我在命案那天早上詫異聞到的一樣。
我一出現在門口,她立刻把我跟腦海中對山迪亞哥的記憶混淆。「他就在那裡。」她對我說。「穿著只用水洗的白色亞麻套裝,他的皮膚太細嫩,禁不起上漿後的摩擦。」她坐在吊床上許久,嚼著小荳蔻,一直到以為兒子回家的幻想消散。這時她嘆口氣:「他是我這輩子最重要的男人。」
我透過她的記憶看見了他。一月的最後一個禮拜,他滿二十一歲,他瘦削蒼白,睜著一雙阿拉伯人的眼睛,還有一頭遺傳自父親的鬈髮。他是一樁為了利益而結合的婚姻生下的獨生子,這樁婚姻從未有過幸福時光,可是他跟父親在一起似乎是幸福的,三年前父親猝逝,他繼續跟單身的母親過著幸福的日子,一直到他死去的那個禮拜一。他從她那兒繼承直覺能力。從父親那兒則是很小就學會使用武器,對馬匹以及猛禽的熱愛,但是他也學到展現勇氣的高超技巧以及謹慎。他們父子講阿拉伯文,但是絕不在普拉喜妲.里內羅面前這麼做,以免她覺得遭到排擠。從沒有人看過他們在村裡帶武器,頂多那麼一次,當他們帶著訓練過的遊隼到義賣市集去做馴鷹術表演時。父親過世,他不得不中斷中學學業,接手經營家族牧場。山迪亞哥.拿紹爾的優點是樂天、溫和以及心腸軟。
他們殺他那天,他的母親見他一身白色套裝打扮,以為他搞錯日子。「我提醒他那天是禮拜一。」她對我說。可是他解釋他的盛裝打扮,是希望有機會親吻主教的戒指。她聽了不覺得感興趣。
「他不會下船。」她跟他說。「他只會按照承諾主持祝福禮,然後返回他來的地方。他討厭這座小村莊。」
山迪亞哥.拿紹爾知道她說得沒錯,但是他忍不住對教堂盛大的慶典做起白日夢。「那就像電影場面。」有一次他跟我這麼說。相較於主教光臨,他的母親只關心兒子別在雨中淋濕,因為她聽見他在睡夢中打噴嚏。她勸他帶傘,可他只是舉起手揮別,走出房間。那是她最後一次看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