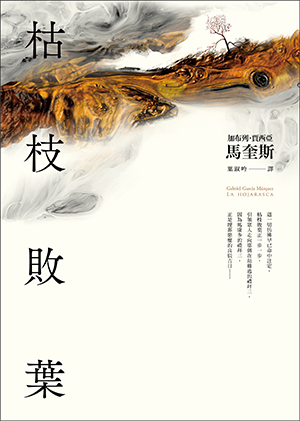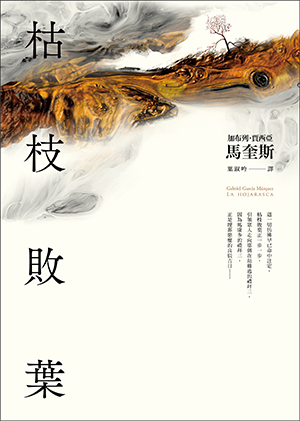內容試閱
這是我第一回目睹屍體。這天是禮拜三,可是感覺像禮拜天,因為我沒上學,穿上某個部位很緊的綠色燈芯絨禮服。我牽著媽媽的手,跟在外公背後,他拄著一根拐杖,每走一步都先探路,免得撞著東西(他在昏暗中看不清楚,走路又一跛一跛的),當經過客廳的鏡子前,我看見自己從頭到腳的打扮,一身綠色禮服,那條漿過的白色領結勒在脖子一側。我照著這面骯髒的大圓鏡,心想:這就是我,今天像禮拜天。
我們來到死者的家。
屋子緊閉,裡頭熱得令人窒息。耳邊只聽見陽光烤曬著街道,除此之外,沒有其他聲響。空氣靜止了,凝結成一片;讓人錯以為是一面可以扭轉的鋼片。停放屍體的房間裡充滿衣箱的氣味,可是四周都見不著衣箱。角落有一張吊床,一頭掛在鐵環上。空氣夾雜一股垃圾味。我想,圍繞在我們四周那些破爛甚至解體的東西,就算真有其他味道,聞起來就是垃圾。
我以為死者都應該戴著帽子。此刻看到的卻不是這麼一回事。我看見死者泛青的臉孔和綁著手帕的下巴。我看見他的嘴巴微張,紫紅色的嘴脣露出一口汙漬斑斑的亂牙。我看見他咬過的舌頭吐在一邊,粗肥而溼黏,比臉的顏色略暗一點,就像用麻繩勒過後的指頭顏色。我看見他睜著雙眼,眼睛瞪得比活人還大,目光烙印焦慮和迷惘,而皮膚彷彿幾經踐踏的潮溼地面。我以為死者應該帶著平靜睡去的面容,此刻目睹的卻恰恰相反。我看見的人端著吵架時那種清醒和暴怒的臉。
媽媽也是禮拜天的打扮。她頭戴遮住耳朵的舊式草帽,身上一襲黑洋裝,領口緊緊扣住,長長的袖子包住手腕。這一天是禮拜三,因此,她看起來格外遙遠、陌生,當外公起身迎接抬棺的工人時,我感覺她像有話想對我說。媽媽坐在我的旁邊,背對著一扇緊閉的窗戶。她費力地呼吸,不時整理從那頂匆忙戴上的帽子底下垂落的髮絲。外公命令那些工人把棺木抬到床邊。這時,我才注意到死者真的躺得進棺木。他們剛抬進來的時候,我看著死者占滿整張床的體型,還以為棺木實在太小。
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帶我來這裡。我從沒來過這棟屋子,還以為裡面根本沒人住。這棟大屋坐落在街角,我想,門從沒打開過吧。我一直以為是空屋。當媽媽對我說:「下午不用上學。」我一點也開心不起來,因為她的語氣沉重又謹慎;我看著她拿來我的綠色燈芯絨禮服,默默地幫我穿上,接著我們一起到門口跟外公會合;我們走過相隔三棟屋子的距離,抵達大屋,我到現在才發現這個街角有人居住。這個人死了,媽媽告誡我時提到的男人應該就是他:「你必須在醫生的葬禮上表現得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