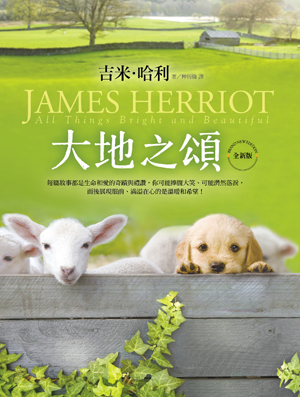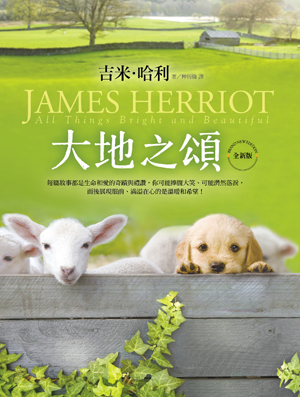內容試閱
偷得浮生半日閒
這是真正的約克郡。潔白的石灰岩壁矗立在山邊,山腳下的蒼綠之中劃過一條兩旁簇擁著石南花的小徑。我獨自逆著芬芳的和風走著,又再度迷失在這遠離煩囂的草原上。遍野的紫花,碧綠的波浪,紫藍色的淨空……你說我如何不流連忘返呢?
其實我並不是一個人,我的身旁還有山姆。海倫帶給我的太多了,而其中我最珍寵的就是山姆。牠原是海倫的獵犬,海倫嫁給我後,牠也就成了嫁妝。我頭一次看見山姆的時候牠才兩歲,當時我萬萬沒有想到這條狗會成為我最忠實的伴侶。山姆坐在車裡隨我到鄉下出診,陪我度過了十來個年頭,使我能愉快地勝任工作且從未因旅途漫長而感到孤寂。
我時常懷疑牠是不是在哪兒看過了「如何做一隻忠實的獵犬」這一類的書,因為跟我坐在車裡的時候,牠會將前爪搭在儀表板上,兩眼焦急地盯著前面的擋風玻璃;在臥房裡的時候,牠會想盡辦法把頭放在我的腳上;外出散步的時候,牠會一步不離地死跟著我。假如我到酒館裡喝啤酒,山姆會趴在椅子下陪我;假如我在理髮,你只要掀開白布就會發現牠躲在我腳底下。世上只有一種場合我不敢帶牠去──那就是電影院。每次我和海倫在電影院的時候,山姆就一定在床底下偷哭。
大部份的狗都喜歡坐車兜風,可是牠們絕不會像山姆那麼狂熱。即使你在半夜把牠叫醒說是要去兜風,牠還是會興高采烈地跟你衝進刺骨的寒夜。每次出診我才拉開車門牠就先跳進車裡,因此在牠去世以後,每當我拉開車門時都會感到缺少了什麼似的。
自從有了山姆以後,我開始允許自己在日常工作中忙裡偷點閒。在城市裡,不管是辦公室或工廠都會有午茶時間,因此我也時常在不知名的野外停下車,和山姆一起穿過樹林到河邊走走或像今天這樣在草原上散個步。
我沿著彎曲的小徑走上山坡,坡上的綠茵中散佈著一簇簇的石南花,金色的陽光均勻地灑在搖擺的花瓣上──這就是我無法抗拒大自然呼喚的原因。我不情願地瞥瞥手錶,發現還有幾分鐘可以享受這般的閒情逸致。待會兒除了要去戴魁先生家做結核檢驗之外並沒有很急的事,因此我躺在世界最柔軟的地毯上,盡情享用這珍貴的幾分鐘。
我瞇眼看著耀眼的晴空,讓濃厚的石南花香味隨著清風徐過臉龐。我慶幸自己走上獸醫這一行並選了德祿這個小鎮。
也許我的合夥人正在某處忙碌,而屈生可能在診所裡看書。我從沒見過屈生看書,因為他頗有一點小聰明。對於一個平日不燒香,臨時也不抱佛腳的人來說,畢業考該是他唯一痛改前非的機會了,因此這一陣子他居然也啃起書本來。毫無疑問,他一定會通過考試,成為正式的獸醫,可是將這麼一位愛好自由的天才用繁忙的獸醫業束縛起來,倒也是相當殘忍的事。他的畢業象徵著他那光輝燦爛的時代的結束。
突然,一個掛著長耳朵的頭出現在我臉前遮住了陽光──那是山姆,牠正爬到我的身上。牠好奇地看看我,似乎在問我是不是該走了,如果我打算繼續待下去的話,牠就要開始蒙頭大睡。我坐直身子拍拍牠的頭,於是牠興奮地跳起來,隨著我的腳步一起回到山腳下的車子裡。
「過來,比爾!」戴魁先生一把揪住莊裡大公牛的尾巴,並對牠吆喝道。
那個時期,幾乎每一家農戶都飼有大公牛,牠們的名字不是叫比爾就是叫比利,我猜想給牛兒取這種成人的名字是希望牠們長得又高又壯。比爾是一頭十足的大笨牛,當牠一感覺到有人在揪牠的尾巴,牠就將那龐大的身軀向旁邊橫跨一步,而這樣剛好提供了我足以容身的空間,使我得以鑽到牠和一面隔間板之間,藉著頂住隔板的反作用力將牠推出去。
我的工作是做結核檢驗。為了要測出皮內分泌的反應,我必須用一支測徑器測量牠頸部表皮的厚度。
「三十。」我大聲讀出刻度。
那農夫將數字登記在檢驗簿上並笑了起來。
「老天,牠的皮怎麼這麼厚?」
「是啊。」我邊說邊從牛身和木牆之間擠出來。「不過牠是個大傢伙,不是嗎?」
牠的體型立刻就迫使我面對現實了。我正要脫身的時候,牠突然靠攏過來,把我卡在木牆上。其實這些小動作是母牛所擅長的,一頭大公牛這麼做實在有些丟人。過去對付母牛的時候我都是抱住自己的頭,用力朝阻擋我的東西頂過去。可是對比爾用這辦法就行不通了。
我猛吸一口氣,使出每一條肌肉的力量,頂住比爾那滿是肥油的身子,可是我發現牠比一棟房子還難以推動。
農夫戴先生扔掉手裡的檢驗簿,又揪住大公牛的尾巴,不過這一次比爾卻毫無反應。牠似乎對自己的行為感到相當滿意,因為牠毫無惡意,只是一心想將身子舒舒服服地靠在隔間板上。我想這個時候牠根本沒有想到人道問題。
不過,無論牠是否無意,其結果都是相同的:我的生命受到嚴重威脅。我的兩眼突出,呼吸困難,太陽穴充血……就在我猜想自己可能要與世告別的時候,比爾開始上下晃動身體。我這才知道牠把身子靠向隔間板的原因──牠是想抓癢。
不錯,牠是抓到癢了,可是我的悲劇卻升上高潮,我確信自己的五臟六腑已經被均勻地磨成肉粉了。我試著再作垂死掙扎,可是比爾壓得更緊。
要不是那扇隔間板已經老朽的話,真不知我的下場會如何。就在我感覺到靈魂已經飄飛而出的時候,身後爆出了破裂聲,同時我被拋入隔壁的牛舍,我癱在爛木板上盯著戴先生,等待我的肺部再度恢復功能。
那農夫的第一個反應是咬緊自己的上脣,因為如果不這麼做,他就會爆笑出來。不過他那從頭到尾都站在乾草堆上觀戰的小女兒可就沒那麼有修養了。她高興地手舞足蹈,並發出清脆悅耳的笑聲。
「唔……爹地,爹地……嘻……你看那個人!你看他,爹地……砰……吱……笑死人啦!」她的笑聲是我所聽過變化最複雜的。她今年才五歲,我誠摯地相信今天這場表演她會記得一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