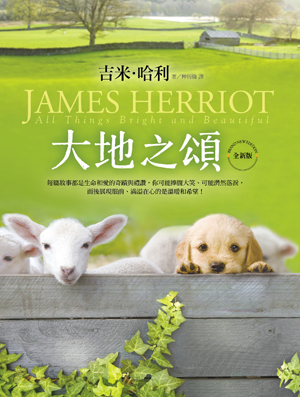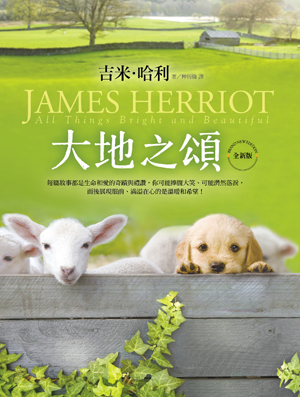內容試閱
我打開記事本察看下一個要跑的地方時,臉上不禁掠過一絲微笑。「湯太太,茉莉台地十四號。剪小鸚鵡嘴。」
感謝上帝讓獸醫業這麼富於變化。經過了剛才那頭野獸的折磨,我需要的是嬌小柔弱的小動物──當然,世界上絕不會有比澳洲小鸚鵡更無害的動物了。
門牌號碼十四號坐落於一列矮小的建築物之間。一次大戰以後,偷工減料的建築商最喜歡承包的這種劣質磚房像雨後春筍般出現在英國鄉下。我拿了一副剪子走向屋前的水泥引道,一位和藹的紅髮女人應聲打開了門。
「我是隔壁的涂太太。」她說。「我常照顧湯老太太。她今年八十多歲了。我才去幫她領了救濟金。」
她帶我進入狹窄的房間。「拿來了。」她對坐在角落的老太太說,並把救濟金登記簿和錢擱在壁爐架上。「還有,哈利先生來看妳的『披頭』。」
湯老太太點頭笑笑。「好。我可憐的小傢伙嘴太長了,吃東西的時候好費力,我為牠擔心死了。你知道,牠是我唯一的伴侶。」
「是的,我知道,湯太太。」我撇過頭看看窗口鳥籠中的綠色小鳥。「這種鳥學會說話以後將是最佳的伴侶。」
她笑著說:「可是披頭很少開口,我想牠大概是太懶了吧!不過我只要牠陪伴就好了,說不說話關係不大。」
那鸚鵡的喙真的太長了,它向後捲曲了一圈又頂在胸前,因此我想像得出進食對牠而言會有多不方便。不過這對我來說將是最簡單的手術,只要我一動剪子,披頭的生命就將得到解救。
我打開鳥籠,慢慢地把手伸進去。
「乖乖,披頭。」我邊吹口哨邊把牠逼到角落,再甩手指輕輕地將牠包住。我輕快地抽出手臂,另一隻手伸到褲袋中拿剪子,可是突然間,我愣住了。
那小鳥的頭不再是聳立的而是傾靠在我的手指上;不僅如此,牠的兩眼還緊緊閉著。我不解地看看牠,然後張開手。披頭一動也不動地躺在我的掌心中。牠死了!
我瞪著大眼看看牠一身晶瑩的羽毛,又看看牠乾澀的喙。我並沒有用力捏牠,更沒有對牠施加暴行,可是牠竟然死了!
我和涂太太交換了驚恐的一眼,但不敢面對湯老太太。當我終於鼓足勇氣回頭看著她時,她竟然在對我微笑。
我把涂太太拉到一邊。「她的視力怎樣?」
「噢,很糟。她從不戴眼鏡,而且她還中聽。」
「怎麼辦?」我的心跳聲震耳欲聾。「我該怎麼辦?如果我告訴她的話……像她這麼大把年紀的人,什麼事都可能發生的。」
涂太太很嚴肅地點點頭。「是啊,她那麼喜歡披頭。」
「只有一個方法,」我用氣音說。「再買一隻掉包。妳知道哪裡可以買到這種鳥?」
涂太太沉思片刻。「鎮郊的阿摩養了很多鳥,或許你可以試試。」
我清清喉嚨才開口說話,但發現我的聲音跟烏鴉叫差不多。「湯太太,我把披頭帶回診所,一會兒就把牠送來。」
於是我跟頻頻微笑、點頭的湯太太道別,捉著鳥籠衝回車子裡。三分鐘後,我已經在敲阿摩的門了。
「摩先生?」開門的是一位健壯的男士。
「對。」他露出遲緩而不堅定的笑意。
「聽說你賣鳥?」
他趕緊挺直腰桿,希望自己看起來更威嚴些。「沒錯。我是德祿鎮和霍頓鎮養鳥協會的會長。」
「好極了。」我上氣不接下氣地說:「有沒有綠色的澳洲小鸚鵡?」
「我有八哥、金絲雀、鸚鵡……」
「我只要澳洲小鸚鵡。」
「我有白色的、水藍色的、彩色斑紋的……」
「我只要綠色的。」
他的臉部掠過一陣痛苦的表情,好像我的態度使他覺得不安。
「唔……我得進去看看。」他說。
我跟著他那從容的步態走到後院,那兒繁多的鳥類著實叫我吃了一驚。
「哈!這兒有隻綠的。牠比其他的要老些,不過這小子很有語言天分,我教了牠很多話。」
「這些都不重要。多少錢?」
「不過……我還有更好的,來,隨我來……」
我一把拉住他。「我就要這一隻。多少錢?」
他噘著嘴好像很難決定似的,最後他聳聳肩。
「十先令。」
「好,把牠放進這籠子裡。」
駕車離去的時候,我從後照鏡中看見阿摩站在門口疑惑地站了好半天。
回到湯老太太家門口時,涂太太正在門口張望。
「妳想這個方法會不會見效?」我悄悄地問她。
「沒問題。」她回答。「她的腦筋已經不太靈光了。」
「我也這麼想。」我推開門走進客廳。
湯老太太又頻頻向我點頭、微笑。「那麼快啊?」
「是啊。」我把鳥籠掛回窗邊。「我想以後牠可以正常進食了。」
從那天起,一連幾個月我都不敢再伸手到籠中抓鳥。事實上即使現在,我都儘量要求主人來做這件事。每當我提出這一類請求的時候,人們都會用奇怪的眼神看著我;我打賭他們一定以為我是個天生就怕小動物的人。
當然,我也不敢再去湯老太太家了。但是過了很久以後的某一天我駕車經過茉莉台地時,一股好奇與衝動竟迫使我將車子停在十四號門前。
開門的是湯老太太。
「妳的……」我說。「妳的披……」
她足足看了我一分鐘才大笑起來。「我懂你的意思了,你是來看披頭的,對不對?哈利先生,你剪得太好了!來,請進!」
鳥籠還掛在窗前,披頭二世看到我走近趕緊在籠子裡表演了幾招翻觔斗。
牠的女主人高興得合不攏嘴,一副對牠這些小把戲很陶醉的樣子。
「你知道嗎?簡直不可思議。」她說。「牠完全變了。」
我嚥嚥口水。「真的?怎麼變了?」
「第一,牠學會了耍把戲,成天翻觔斗。第二──這才是最怪的──牠整天喋喋不休地說個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