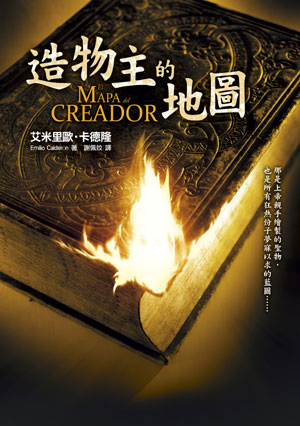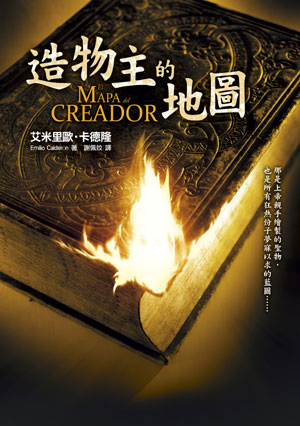內容試閱
「你知道路嗎?」聽她說話的語調就知道,她已經把嫻靜端莊留在學院牆內。
「知道,別擔心。」
「這條人行道真難走。」她說。只見她正小心翼翼踏過羅馬隨處可見的的圓石路。
我一看才發現她穿了高跟鞋,而且是那種可以穿去跳舞的高跟鞋。
「穿那種高跟鞋很容易扭傷腳。」我說。
「我只是覺得這樣看起來會比較正式、比較嚴肅。我爸總是說,談生意最重要的就是要嚴肅和正式。」
更不用說日常生活了,我心裡暗道,想起孟莎的爸爸法賓加斯先生永遠陰沉又嚴厲的模樣。他是個企業家,在沙巴第有家紡織工廠,很關心巴塞隆納的政治局勢。法賓加斯先生隨時隨地帶著一篇英國記者喬治‧歐威爾寫的文章;此人是個左傾分子,替人民陣線和共和政府說話;他在這篇文章中描述了在巴塞隆納的所見所想,說出他抵達這塊奇異大陸,看見資產階級消失,人們稱呼對方不再使用敬語,帽子和領帶變成法西斯主義者的標準裝扮等等的感想。只要有人問法賓加斯先生他為什麼選擇流亡,他就會提到歐威爾的這篇文章,然後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大聲念出來。為了避免對方搬出還不都是佛朗哥毀了法治社會這種論調,法賓加斯先生還會拿出另一篇報導。那是一九三四年六月九日加泰隆尼亞地區的國家主義報紙《原鄉》(La Nació)上的一篇文章,他在這個句子底下劃了線:「我們從來就不想歸屬於西班牙人的國度,因為聞到吉普賽人的味道就想吐。」指出文章之後他又會說:「這就預言了戰爭即將爆發。這就是為什麼佛朗哥決定拆穿敵方的真面目:一群危險的野蠻人。」如今,他人在羅馬,盡心盡力籌募資金,以助加泰隆尼亞脫離他所謂的「布爾什維克的無政府狀態」。
「妳喜歡羅馬嗎?」我問孟莎,仍然試著要炒熱氣氛。
「我喜歡這裡的建築勝過巴塞隆納,不過比較喜歡巴塞隆納的街道。羅馬的街道好像巴塞隆納拉維爾區的街道,只不過路旁換成了宮殿。而且都是好漂亮的宮殿!你呢?」她直率地問:「你喜歡羅馬嗎?」
「我打算一輩子都住在這裡。」我篤定地說。
雖然這個念頭已經在我腦中打轉好幾個月,但這還是我第一次說出口。
「住學院?」孟莎好奇地問。
「不是。戰爭結束,學院也差不多完了。我打算以後在這裡開一間建築事務所。」
說也奇怪,想當初是學院院長范因克蘭力邀我到學院研究法西斯建築,看能不能發掘對共和國有用的東西。後來院長在家鄉加里西亞過世,而共和國像一幢設計不良的建築,搖搖欲墜。多虧了我的研究題材,大使館書記奧拉拉才會信任我,至少表面上是這樣。他負責的一項任務就是當大使館的眼線,發現誰的思想或行為有政治嫌疑就去打小報告。
「你為什麼不想回西班牙?我就想回巴塞隆納。不管怎麼樣,西班牙戰後最需要的不就是建築師嗎?」
孟莎說得沒錯。佛朗哥如果贏了這場戰爭,就會需要研究法西斯建築的建築師。不過,佛朗哥需要什麼是一回事,我想做什麼又是另一回事。
「我沒有家人,沒有人在西班牙等我回去。」我說。
孟莎細細端詳我,默不作聲,像在請求我多說一點。
「我爸媽死了,祖父母也是,我又是獨生子。」
「可是一定有叔伯姑媽堂表兄弟姊妹什麼的……每個人都有吧。」
「有是有,可是他們住在桑坦德,我從沒見過。我叔叔阿姨搬進我祖父母的房子那時候,我們在馬德里見過兩次。但後來搞得很難看,他們和我爸媽的關係變得很僵。至於堂兄弟姊妹,他們對我就來說就像陌生人……」
「家族就像縮小版的國家;裡頭也可能出現叛徒。」孟莎脫口而出,說完嘆了一聲。
我看著她,大吃一驚。
「是我爸說的。我海米叔叔是紅軍。我爸不准我們提起他。」她又說。
「可是妳剛不就提了嗎?」我說。
「我可不希望我爸和我叔叔變成該隱和亞伯。」
本來想問她哪一個是哪一個,但又怕挑起的話題失控。如果過去幾個月我學到了什麼,那就是戰爭時期話語很容易引起誤解。「基本上你爸是對的。」我說:「國家就跟家族一樣。一旦家裡的成員對彼此宣戰,他們唯一在乎的就是增強武力,根本不管會造成什麼傷害。」
我們越過臺伯河上的希斯托橋,捏著鼻子以免聞到河流散發的惡臭。這條河就像橫過城市顏面的化膿傷口。有人在一邊盡頭畫了一個法西斯的標誌:一把斧頭貼著一捆木棍。那本來是古羅馬代表高官和教士的符號,後來被墨索里尼拿來當成政治運動的標誌。
我們走到納佛那廣場,停在四河噴泉前,那是貝尼尼最有名的噴泉。
「他們說代表尼羅河和拉布拉他河的兩個巨人之所以遮住眼睛,是因為不想看到布羅密尼的阿貢尼聖安格絲教堂。」孟莎說。這個傳言經常聽到。「看來兩個偉大的藝術家對彼此的敵意很深。」
「大家都這麼說,其實沒這回事。」我說:「這座噴泉比教堂還早完成。代表尼羅河的巨人之所以遮住臉,是因為他不知道自己從哪裡來。羅馬充滿了這一類為歷史添色的傳說。也許,這座古城因為這些傳說更有魅力,也需要這些傳說保持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