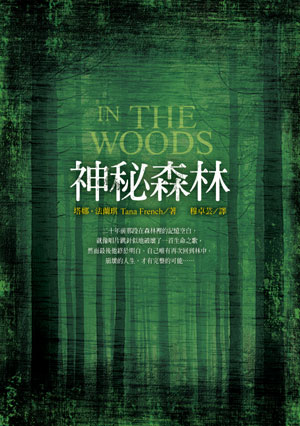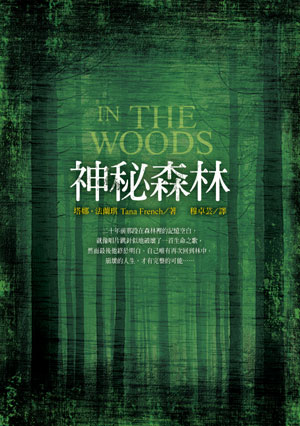內容試閱
凱西還沒加入重案組,我們就聽說她這號人物了,說不定更早,在她接受調任之前,我們就略有耳聞了。這裡的消息快得離譜,跟三姑六婆一樣有效率。重案組人少壓力大,只有二十名常任組員,任何風吹草動(誰要來、要走;工作太少、太多),組裡都會像艙熱症患者一樣陷入歇斯底里的狀態,開始結黨分派,流言四起。通常遇到這種事情,我都置身局外,但凱西要來重案組這項消息實在太轟動了,我想不知道都難。
凱西是女的也就算了,問題是她才二十八歲,而且剛從警專畢業沒幾年。在警界,重案組是菁英中的菁英,能進組裡的沒有一個是三十歲以下,除非他老爸是議員或大官。因此凱西進組裡那一天,所有人都跌破眼鏡。之前傳言說得天花亂墜,讓我以為她應該像電視影集裡的女警,長腿,洗髮精廣告般的秀髮,甚至穿著緊身衣。週一早點名,歐凱利組長介紹凱西給我們認識,凱西站起來,說了些場面話,很高興加入重案組,希望勝任組裡的高標準等等。她約莫中等身材,深色鬈髮,肩方身瘦,很像小男生。她不是我喜歡的型,我喜歡小女人,甜甜的,小鳥依人,一隻手就可以舉起來抱著轉的那種。然而,她有一種獨特的魅力,也許是她的站姿,重心側向一邊臀部,身體挺直但卻放鬆,很像體操選手。也許只是單純的神秘感。
不過,我還是跟凱西成了朋友,而這都得歸功於她那台一九八一年的乳白色偉士牌機車。車子雖然是經典款,但我就是覺得它像血統優良的雜種狗。我老是叫它高爾夫球車,故意惹凱西生氣,而她則是笑我買那輛白色爛吉普車是為了彌補男子氣概,還不忘補上「我很同情你女友」之類的鬼話。
要是她心情不好想找人吵架,就會譏諷我的車是「艾克摩比」雙輪車。那天是九月,外頭狂風暴雨,高爾夫球車好死不死選在這時候故障。我當時開車正要離開停車場,看見她這位小姑娘穿著紅色雨衣,簡直跟「南方四賤客」裡的阿尼一個模樣,身旁小機車和她一樣濕淋淋的,被剛剛開過的巴士濺了一身水,氣得她對巴士破口大罵。我把車停在她面前,搖下車窗問:「需要幫忙嗎?」
她瞪著我大吼:「你覺得我需要嗎?」說完,她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竟然開始大笑。
我花了快五分鐘試著發動那台偉士牌,結果卻愛上凱西了。她穿著特大號雨衣,看起來只有八歲,感覺腳上應該套一雙瓢蟲圖案的長雨鞋才對。紅色帽簷下是一對棕色大眼睛,雨水沾濕的睫毛細細尖尖的,還有一張小貓臉。
隔天早上進辦公室,我和她已經是朋友了,就這麼簡單。兩個人都無心插柳,醒來卻發現友誼早就綠意成蔭了。
我們接到凱薩琳這個案子是週三的早上,八月。根據我的筆記,時間是十一點四十八分,所以組裡其他人都去喝咖啡了,只剩我和凱西。「有考古隊員發現一具屍體,誰要去?」
「我們去。」凱西說。她伸腳朝我椅子一蹬,連人帶椅子回到她的桌前。
「為什麼?」我說:「找法醫處理不行嗎?」警探只有特殊狀況才會出動,通常是屍骨落在泥煤沼裡,骨肉保存完好,跟剛死的屍體沒有兩樣,才會讓人覺得需要特別處理。
「不行,」局長說:「屍體還很新鮮,年輕女性,看起來是謀殺。員警要我們過去,屍體在納克拿里,離這裡不遠,所以不用留守或過夜。」
路上,凱西從書包裡掏出光碟盒遞給我──開車的人挑音樂。我假裝自己忘了帶光碟,在盒子裡看到第一張像是重金屬音樂的就挑出來放,而且把音量調大。出事那年夏天,我離開納克拿里鎮,之後就再也沒有回去過。潔咪的寄宿學校入學日來了又過了,幾週後換成我進寄宿學校,但不是她原本要讀的那一間。我唸的學校在威特郡,是我父母親所能負擔距離最遠的學校。耶誕假期我會回家,但我們家已經搬到雷斯力普,在都柏林另一邊。我們一開到中央有分隔島的幹道,凱西就掏出地圖找到正確出口,並且一路指示方向。車子行駛在坑坑洞洞的馬路上,兩旁路肩綠草叢生,樹籬護欄沒有修剪,枝枒不停喀喀敲打車窗。
我當然希望自己還記得當時在森林裡究竟發生了什麼。少數知道這件事情的人,全都不約而同建議我嘗試催眠回溯法,但我就是很排斥這麼做。我不喜歡新世紀,只要感覺到一點氣氛就馬上心生戒備。我不是討厭它的學說或做法,起碼我從旁觀察覺得還滿有道理的,我討厭的是搞新世紀運動的那群人,他們老愛在宴會上把你逼到角落,大談他們怎麼發現自己是碩果僅存的幸運兒,又為什麼應該得到幸福。我很擔心做了催眠之後,會像第一次讀到美國作家凱魯亞克小說的十七歲少年一樣喜不自禁,滿足地以為發現了真理,開始在酒吧裡四處拉人傳教。
山丘側邊的緩坡上有一大片原野,屍體就是在這裡發現的。放眼望去,整塊地都被剷平,土壤也被翻攪過了,到處都是考古隊員留下的神秘記號:壕溝、巨大的土丘、組合房屋、零零星星的粗糙石牆,看起來很像瘋子搞出來的迷宮,感覺非常超現實,又宛如核彈爆炸現場。原野一邊是茂密的樹林,另一邊是一道牆,從樹林一直延伸到馬路,牆外可以看到樓房整齊的三角牆。緩坡上緣接近矮牆的地方,鑑識科的人已經用藍白警用膠帶拉了一圈隔離現場,所有人正圍著不知道什麼東西。這些傢伙我差不多全都認識,但他們身穿白色連身服,戴著手套東翻西找,再加上一堆不知名的精密儀器,整幅場景看起來非常詭異,充滿了不祥的感覺,讓人懷疑是不是和美國中情局有關。環顧四周,只有兩樣東西像童書插圖一樣,一眼就認得出來,讓人安心放心。一個是馬路旁邊低矮的石灰白小房子,黑白兩色的雜毛牧羊犬趴在房子前面,腳掌不時微微抖動;另外就是爬滿常春藤的石塔,微風吹來,常春藤翻動飛舞,有如陣陣波浪。沉鬱的河水切過原野一角,河面上波光粼粼。二十年前,原野還是一片森林,如今只剩幾排樹木。牆後是樓房屋子,我當年就住在其中一間。
我沒想到這裡會變成這樣。我從來不看愛爾蘭新聞,永遠都是同一群反社會政客反覆說著讓人頭痛的陳腔濫調,嘰嘰聒聒,有如快轉唱片發出的噪音。我只看國際新聞,距離會讓事情變得單純,給你幻覺,讓你心安,認為世界不盡然和愛爾蘭一個樣。我確實輾轉聽說有考古隊員在納克拿里附近挖掘探勘,引起不少爭議,但我沒有注意詳細情形,也沒打聽確實地點。我沒想到這裡會變成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