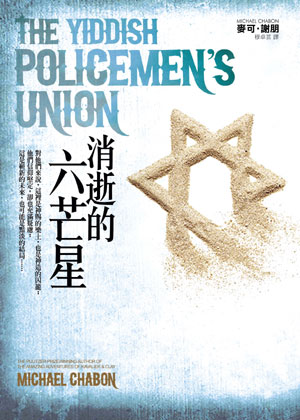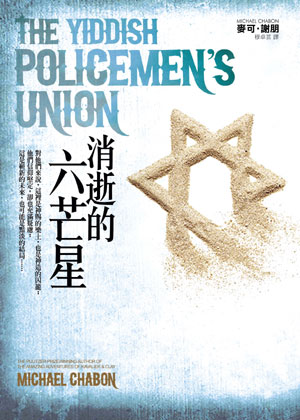內容試閱
席卡市中心有間舊俄羅斯孤兒院,過去二十七年,警察總局就暫時棲身在後方空地上的十一棟組合建築裡。藍茲曼和謝梅茲把車開到碎石空地上時,隔了一兩秒才注意到台階上的女人。女子撐著黑傘,身穿鮮橘色連帽毛大衣,帽緣是圈
耀眼的綠染合成皮草。一綹紅色鬈髮從綠染皮草間鑽出,垂在女子臉上。
那女子現在怒目皺眉走向車子,從遠處看來,藍茲曼覺得這女子比黑咖啡還要烈上三、四倍,而且今天早上已經有人惹毛了她。藍茲曼和她結婚十二年,在兇殺組共事五年,一眼就能分辨她的情緒。
「別跟我說你早就知道了。」他對謝梅茲說,一邊熄掉引擎。
「我真不知道,」謝梅茲說:「希望閉上眼,再睜開後發現一切都不是真的。」
藍茲曼試了。「沒用,」他遺憾地說:「給我們一分鐘。」然後下車。
「請便,慢慢來。」
藍茲曼花了十秒走過碎石空地。頭三秒,賓娜看來很高興見到他,接下來兩秒,她露出焦慮而又可愛的表情。最後五秒,她擺出鬥嘴的架勢,等著看藍茲曼想不想吵架。
「操,現在是怎樣!」藍茲曼實在不想讓她失望。
「忍受你前妻兩個月,」賓娜說:「之後我就不曉得了。」
兩人離婚後,賓娜去了南方一年,參加培訓女警探的領導課程。回來後,她接下艱鉅的亞科維警局兇殺組警探職務。藍茲曼從妹妹葬禮後就沒再見過她。
「看到我不高興嗎,梅爾?」她說:「你不對我這件皮大衣說點什麼?」
「顏色跟妳很搭,」藍茲曼聽見自己勉強擠出一句:「跟妳眼睛很合。」
賓娜聽到他的讚美,彷彿接過一罐搖過的汽水:「所以你被嚇到了。沒聽說費森菲爾的事嗎?」
「他是費森菲爾啊,我能聽到什麼?」藍茲曼想起施平格昨晚也問了一樣的問題。這時,他突然懂了!枉費他還是逮到醫院殺手波多斯基的人。「費森菲爾閃了!」
「前天晚上繳回徽章,昨晚飛澳洲墨爾本,他小姨子住那兒。」
「所以我變成妳的下屬了?不會吧?」
「這年頭什麼都有可能。」賓娜說。
這時她臉上的線條突然變得柔和,藍茲曼這才發覺她和自己在一起有多緊張,謝梅茲過來時,她整個人已完全放鬆下來。
「大家都到齊了!」她說。
藍茲曼回過頭,只見搭檔就在身後。謝梅茲手腳非常輕,關於這點,他當然歸功於自己的原住民血統,但藍茲曼認為是他那雙穿了雪靴,整個貼著地面的大腳帶來的表面張力神效。
「哎呀呀!」謝梅茲親切地說。打從藍茲曼頭一回帶賓娜回家,謝梅茲和賓娜就像立刻有了默契或說共識,知道怎麼開藍茲曼玩笑,讓他彷彿四格漫畫裡的人物,嘴裡叼著根炸彈開花的雪茄,氣得七竅生煙。賓娜伸出手,兩人握了握。
「歡迎回來,藍茲曼警探。」謝梅茲靦腆地說。
「是探長,」賓娜說:「還有,我又姓回凱費許了。」
「葬儀社的人要來了。」藍茲曼說的是美國內政部派來的交接小組,管轄權移交的前鋒部隊,負責監督這場歷史葬禮,安排屍體下葬。藍茲曼心想,這樣如果後來事情出了差錯或者搞砸,只要光明正大怪罪到猶太人身上就行了。
「有位史培德先生,」賓娜說:「應該星期一,最晚星期二會出現。」
「費森菲爾,」藍茲曼一臉嫌惡。只有這種傢伙才會在葬儀社的探子來訪前三天溜之大吉。「希望他走一整年霉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