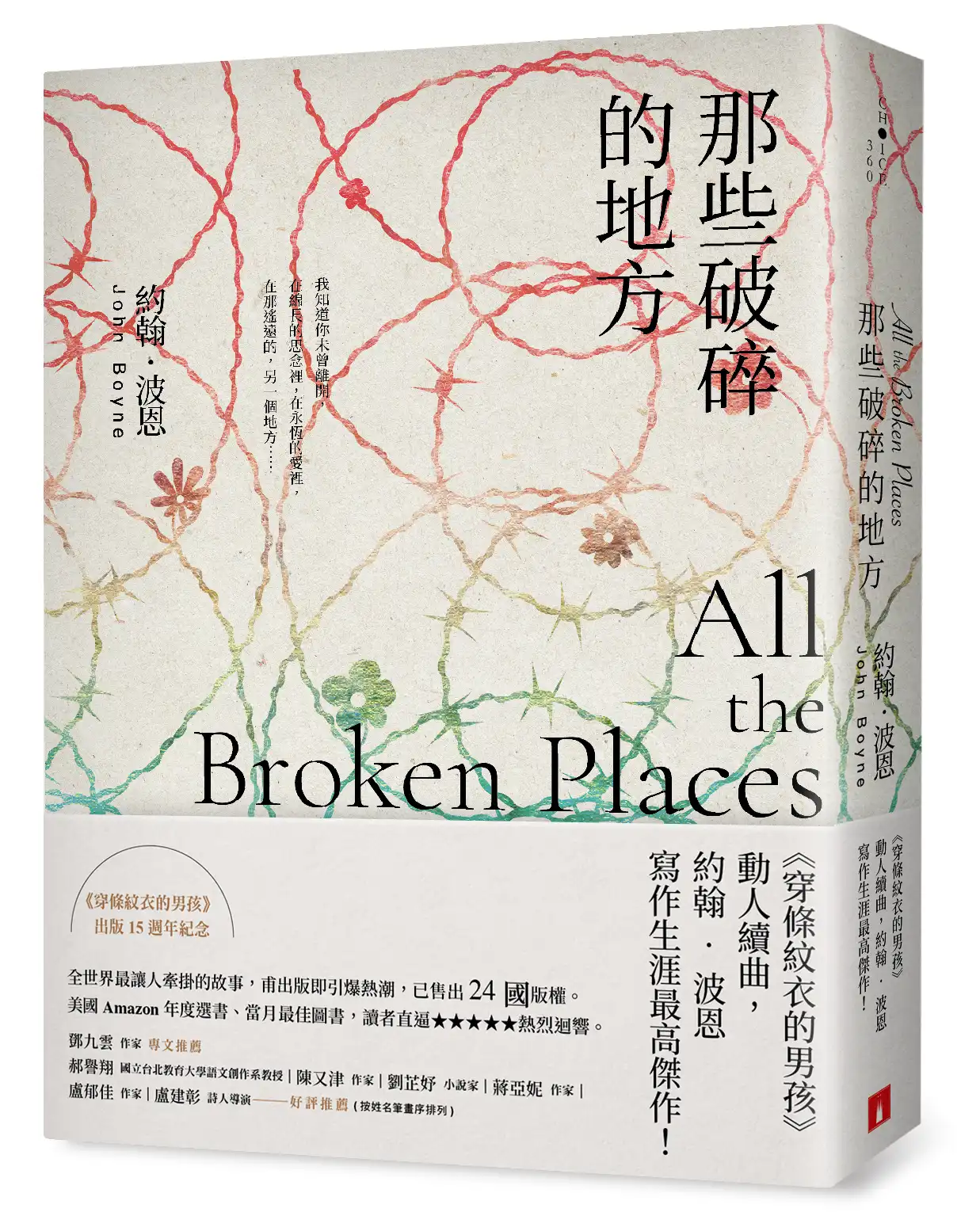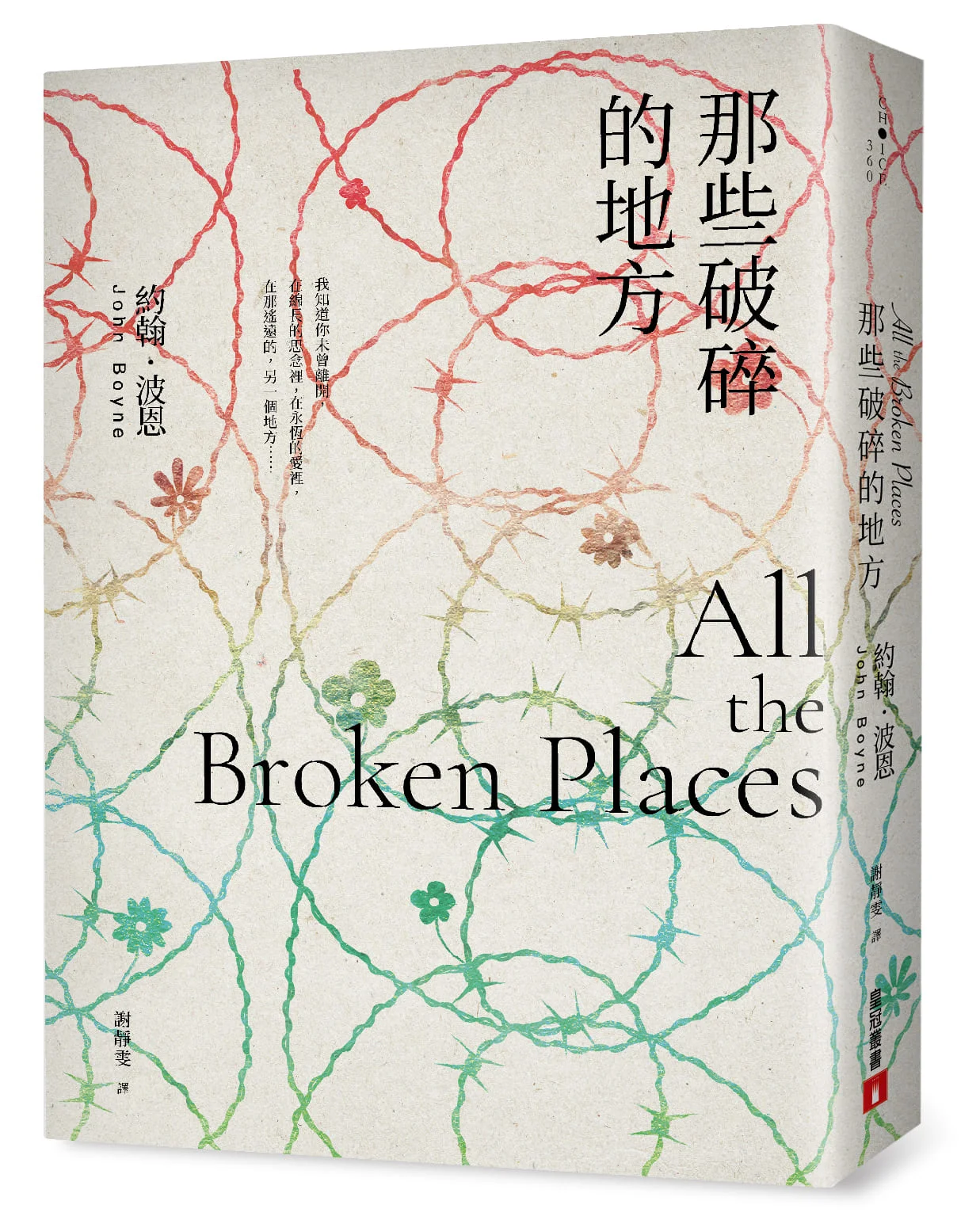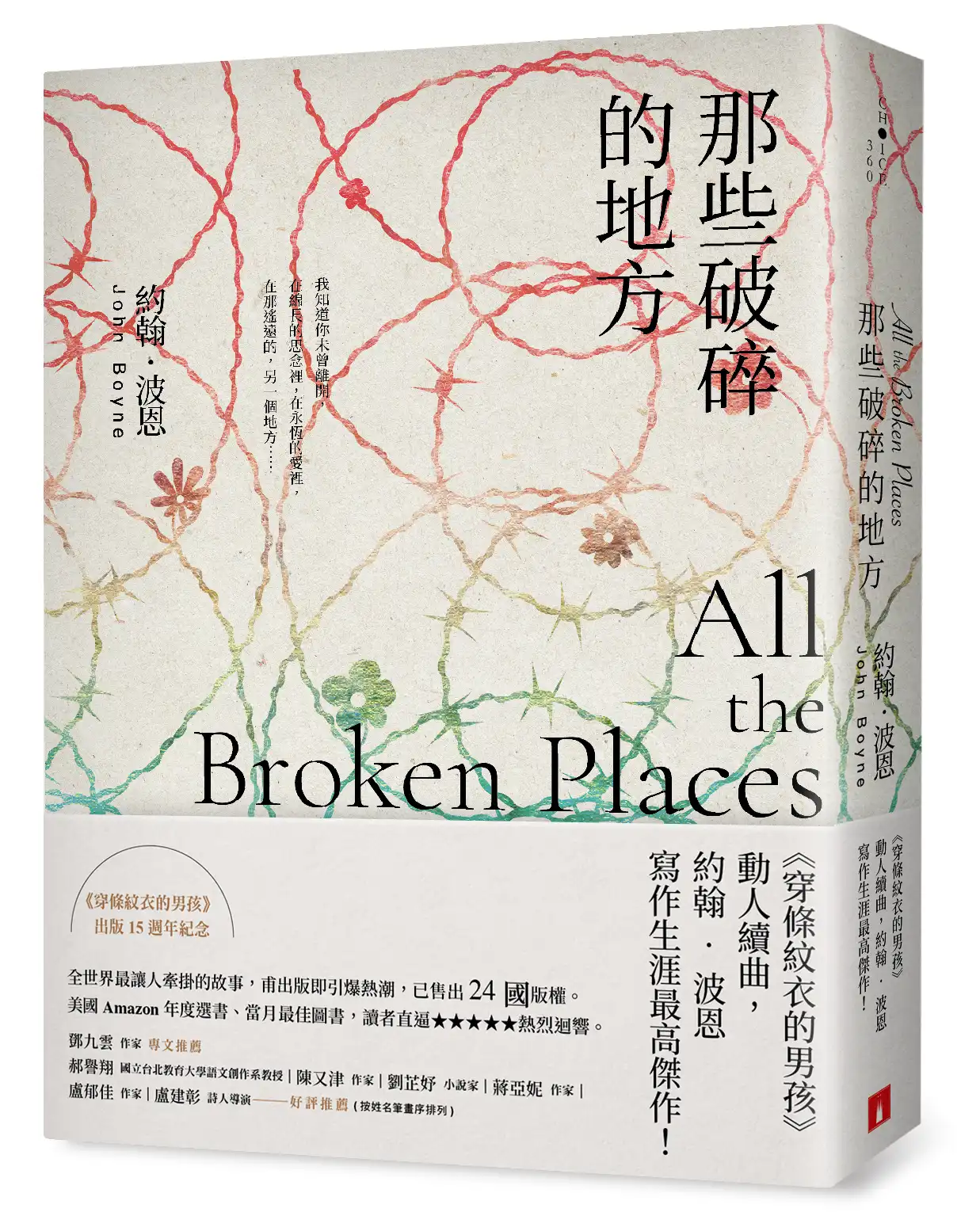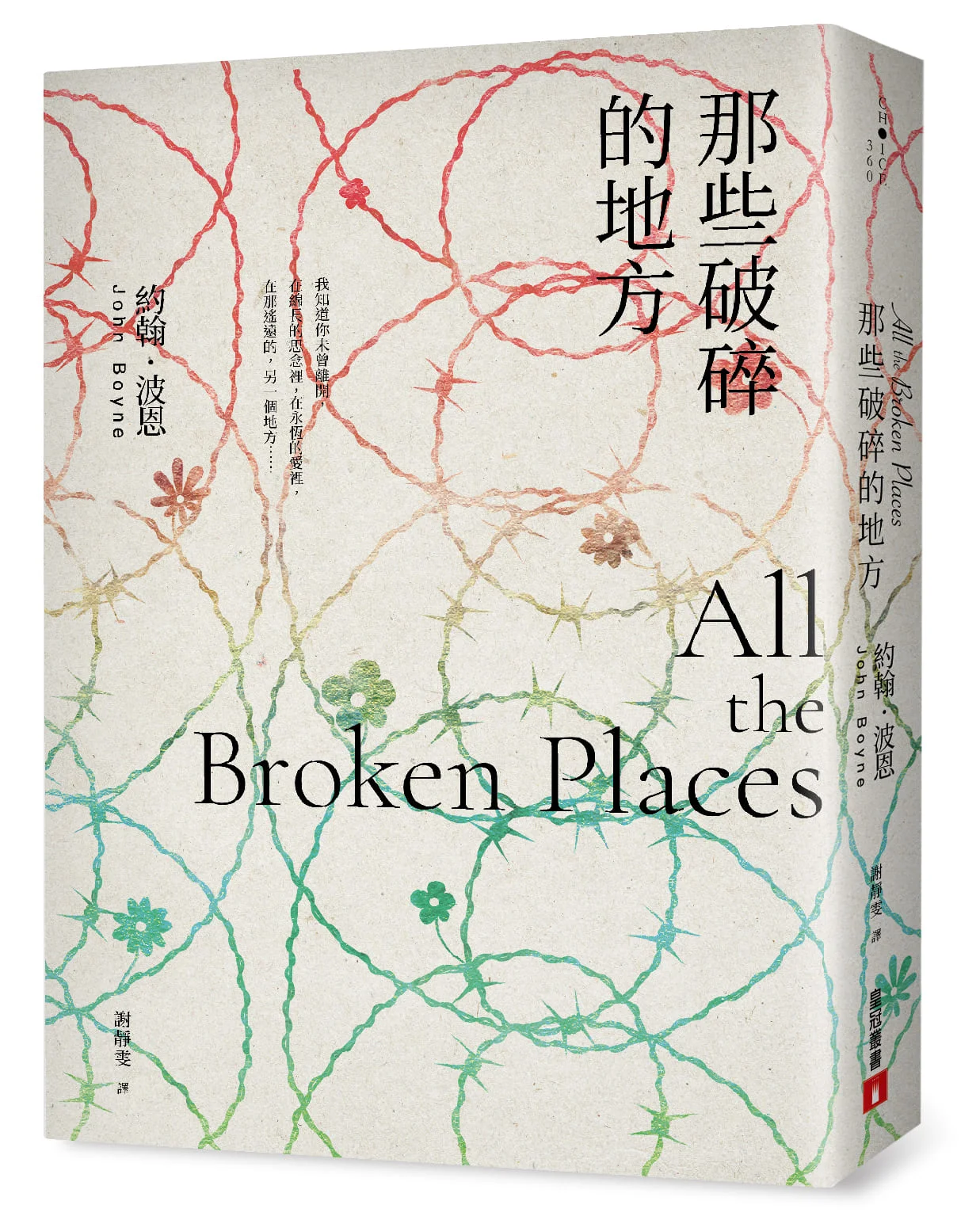內容試閱
凝視殘忍
作家 鄧九雲
七宗罪裡排序第一的是「傲慢」(pride)。如果把這個形容詞套在希特勒身上是毫無違和,但似乎有種隔靴搔癢的失準度。那麼試試「殘忍」(cruel)呢?我認為無論是中文還是英文,在語感上都更逼近那段大屠殺的歷史之殤。
有足夠勇氣的人們能承認自己驕傲、嫉妒、憤怒、懶惰、貪婪甚至是好色,但有多少人能說出自己是殘忍的?更或許,殘忍的複雜性其實是難以覺察。可是我深信,每一個人或多或少肯定都有殘忍的經驗,只是可能還沒機會為那些行為命名,就已埋藏在記憶深處罷了。
閱讀完《那些破碎的地方》,我開始翻攪記憶,為自己的殘忍命名。
第一個稱之為殘忍的記憶,是凝視殺雞。印象中早期傳統市場的雞肉攤,後面會關著一整籠探頭探腦的雞。小時候跟長輩去市場採買的記憶,全都是自己傻傻站在那,看著肉販如何把雞從籠子裡一把抓出來,在脖子上快速劃下一刀放血,然後丟進熱水裡涮燙擠下去毛——後面的畫面我就不記得了,連雞是何時斷氣的我都說不出來。不到五歲的我,綁著兩根稀疏的沖天炮,就那樣張著嘴巴看呆了。後來的我每次回想這段記憶,總是好奇為什麼面對如此血腥暴力的畫面我沒有別過頭去,反而眼睛像鎖住了一般。我甚至不記得有感到害怕或不舒服,嚴格來說那感覺中心回想起來是「空的」。
麻煩再重看一次我的敘述——每當我回想凝視殺雞,腦中出現的畫面是小小的「我」與被殺的「雞」。不單只有雞,我的身影也在那敘事中。我像是進入某種解離的第三隻眼,正在觀看專心凝視殘忍的自己。我凝視的存在,成了殘忍的共犯。
第二個稱之殘忍的記憶稍長許多,是得知曾熟識的人痛苦自殘。中學讀女校時被一位學妹親睞,她發生什麼事都想跟我分享,每天下課鐘聲一打,她就會衝到我班上的走廊叫我。當時才十歲出頭的我們,沒有人能明白那份渴望見到對方幾乎佔據一切的感覺究竟是什麼。我們當然都知道愛情的存在,但狹隘的社會與環境讓我們以為那只會/能存在於異性之間。
有一天,我實在受不了學妹每節下課的打擾,以及那些我想像出的流言蜚語。於是我非常嚴正地告訴她,請再也不要來找我。剩下共校的兩年裡,我都把她當透明人一般,卻沒有告訴任何人每次彼此擦身而過時,我的心臟都不知為何瘋狂地在跳。幾年後來得知她曾在那段時間數度自殘自己,無論去追究那是否單純因為我的拒絕,或是我需不需要為另一個人的行為負起責任,我都心知肚明經歷家庭破碎與身份探索的她,曾把我當成傾訴一切的對象。我接受她的依賴,卻又在毫無邏輯與警示之下截斷那傾靠。她會倒,是否也在我預料之中?我將那段記憶命名為殘忍,並拒絕用任何「不懂、無知」當成藉口為自己解套。
這兩份自白,能否能讓你意識到,殘忍其實離我們很近很近。在神話與童話裡,總是充滿了各種殘忍的劇情與懲罰。或許因為從口耳相傳的文化故事裡過於熟悉殘忍的各種面向,彷彿被神允許的殘忍是如此深重,於是我們很難毫不猶豫地將殘忍視為一種罪。更別說去辨認出那間接、旁觀的視角,並將之承認為一種共犯存在。
這也呼應了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提出的「邪惡的平庸」——解釋一個普通人如何成為極權主義體系的演員,上演著殘酷的劇碼而樂此不彼。美國政治理論家Judith N. Shklar在《平常的惡》(Ordinary Vices)裡提出,殘忍是有別於亞里士多德提出的「變態的獸性」。老練的人會告訴我們不要細談惡,因為論惡最終都會走入「厭世」的絕境。一旦厭世,抽離就是對社會的一種毀滅——產生消除厭惡之人,留下強壯沒美好的部分的慾望——最終成為一位政治暴君。
然而戲劇與歷史註定得凝視殘忍。古典悲劇踩在「肉體殘忍」,而喜劇則是仰賴「道德殘忍」。本書作者約翰波恩說了,「每個死於屠殺的人的故事都值得述說。」當然也包括那些活下來的,倖存者們,以及所謂的「共犯」。
《那些破碎的地方》是《穿條紋衣的男孩》的續篇。後者以這家族的弟弟為視角,前者是姊姊,在大戰八十年後的現在,以九十二歲的高齡回望過去。那些留著罪人血液的後代,是如何背負著另一種創傷活過來的?如果你像我一樣沒有讀過《穿條紋衣的男孩》的故事就開展這本書,那絕對會是加成享受的閱讀經驗。享受這用詞恐怕不恰當,因為這是充滿歷史硬殤的故事。他們必須不斷被說,直到其中那種複雜的人性與情緒真相能更精準地被逼近。我佩服作者顧慮到像我這樣首次的閱讀者,用高明的敘事手法,同時推進過去與現在,不但補齊了《穿條紋衣的男孩》裡的空白,也更深刻探索那些「一生無法消化的痛苦」。為了不讓自己爆雷,原諒我用如此私密的經驗自白切入。
最後我想提一下《那些破碎的地方》裡現在敘事線中,作者用家暴人物象徵暴君的原型。他的身份是一位電影製作人,而他的老婆是一位貌美卻不能再演戲的演員。作者這樣的設定讓人玩味。他提出另一個重要的悲劇元素,就是「階級」。製作人大於演員,男人大於女人。我非常關心作者試圖靠近的那個殘暴最後的「出口」為何?我們很難否認法國哲學家蒙田所說的:以殘忍的方式厭惡殘忍,是有效的方式。
關於這「出口」,我並沒有明確的答案。但我想分享曾經在進行「家族排列」的治療活動時,家排師說過一件事——家族裡若有嚴重精神疾病的家人,代表那家族裡,有人直接或間接殺過人。而因為我們距離第二次世界大戰還不到百年,要追溯到完全無關的機會幾乎是微乎其微,這也說明了集體意識的現象。用另一個角度來說,那是我們的共業。那些沒有辦法消化的苦痛就是「創傷」,世世代代存於我們的血脈之中。唯有透過不斷不斷地講述,每說出一個故事,那箝制業的枷鎖,終究能夠一點點鬆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