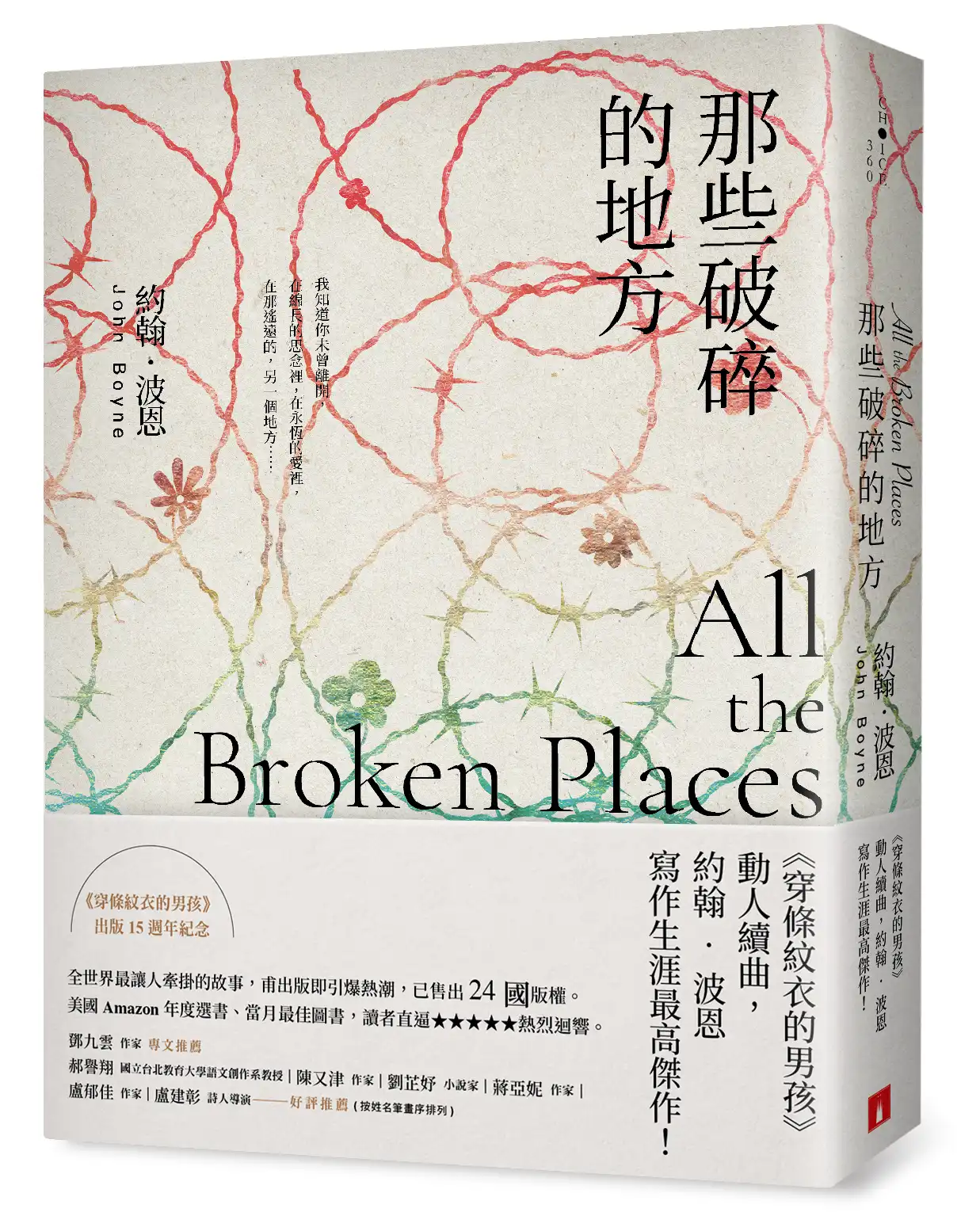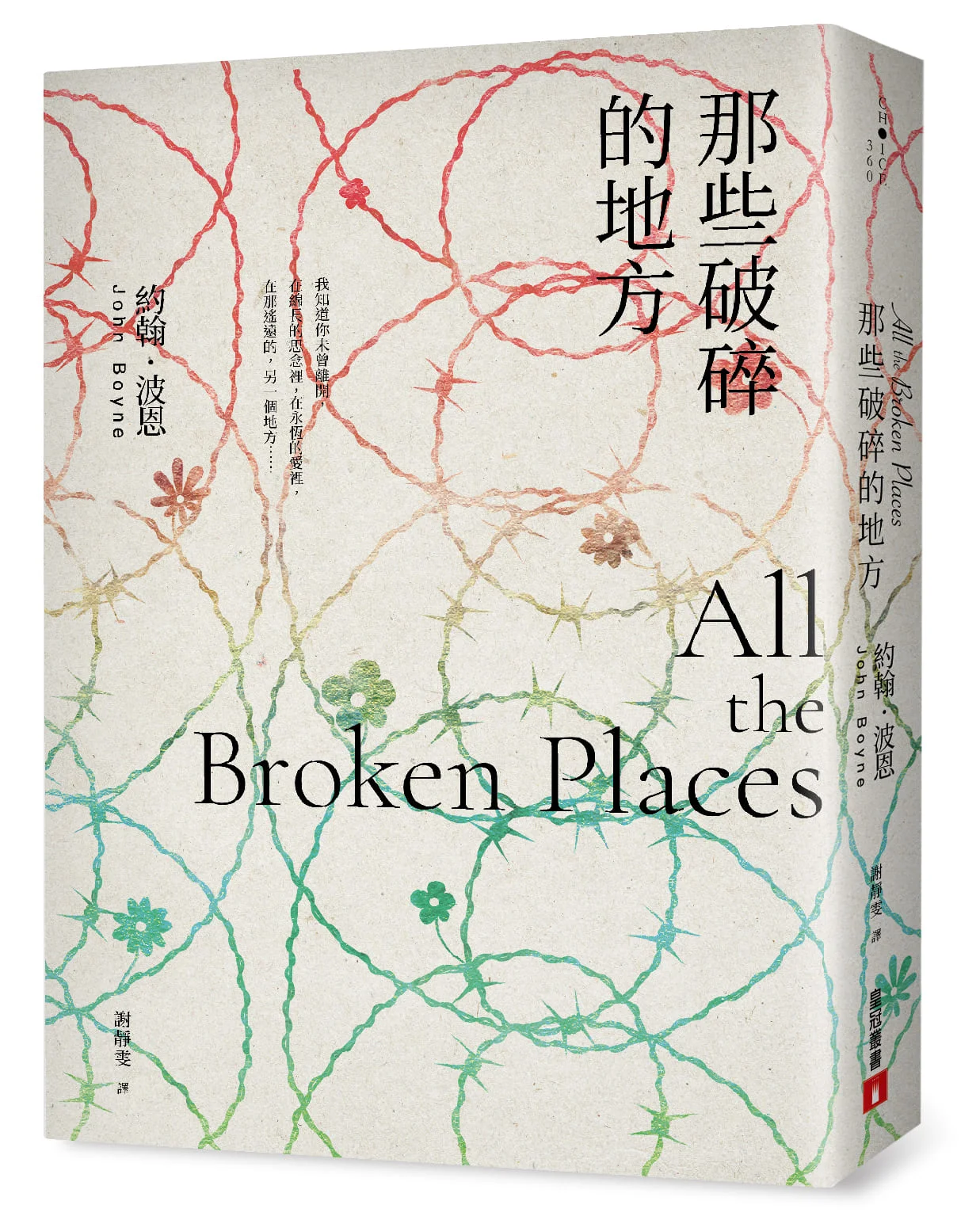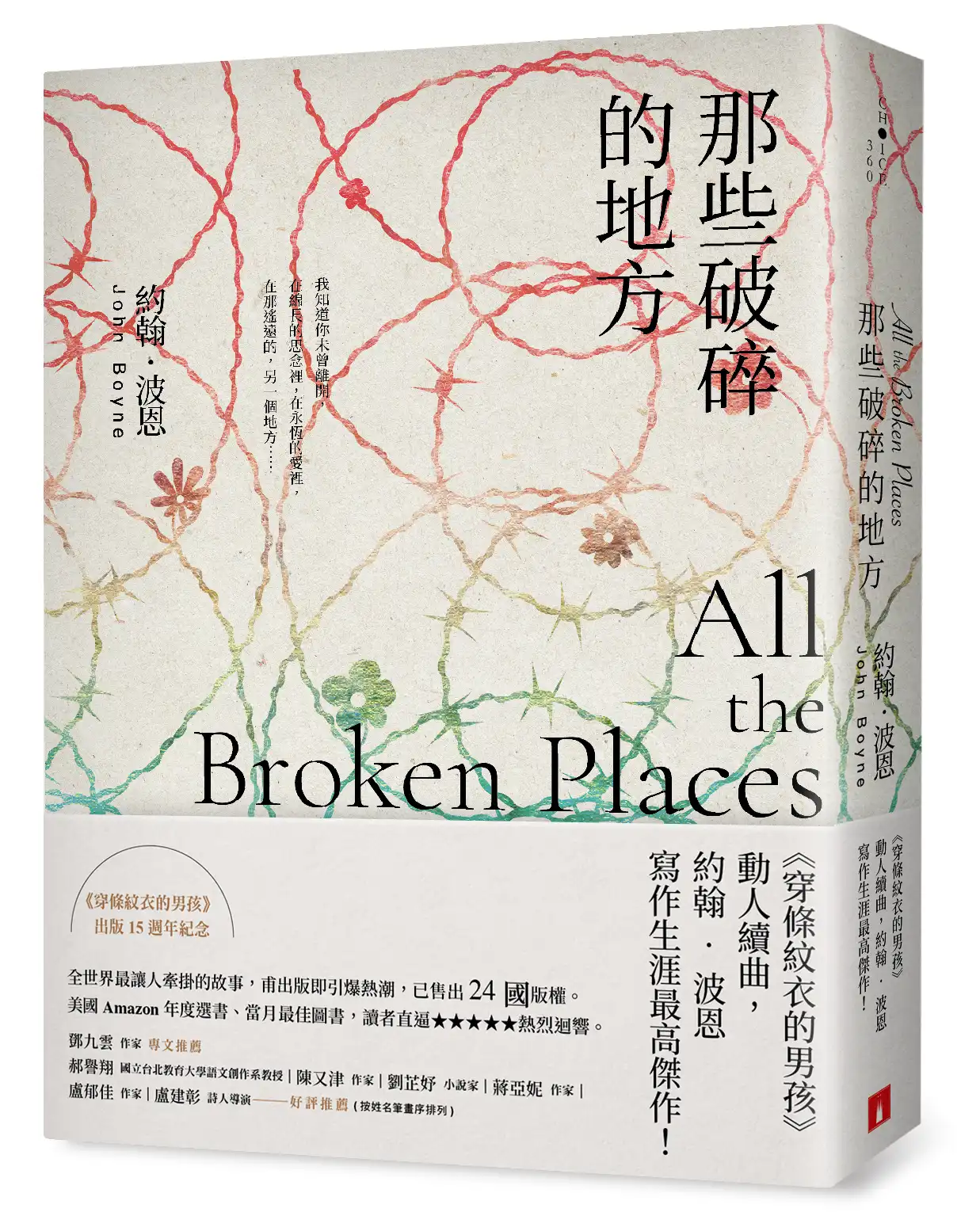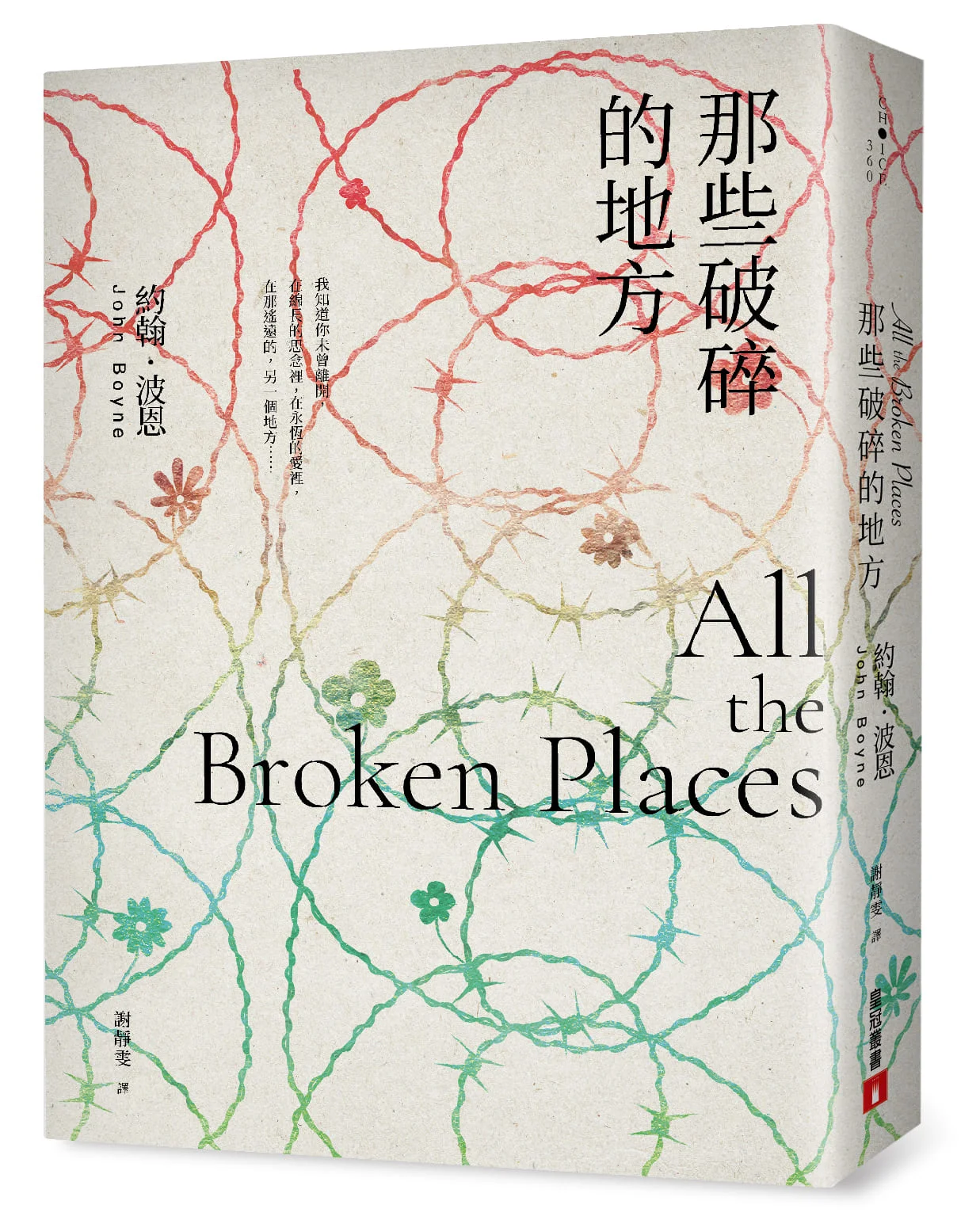內容試閱
第一部
惡魔的女兒
倫敦2022/巴黎1946
1
如果每個人因為自己沒做的善事而有罪,有如伏爾泰提議的,那麼我這輩子都在想辦法說服自己,說起所有的惡行,我都是無辜的。這一直是個方便門,讓我得以承受幾十年來遠離過往的自我放逐,視自己為歷史失憶的受害者,卸除共犯的罪名,並且免於受到責難。
不過,我最終的故事始於也終於開箱刀這個微不足道的小東西。我的開箱刀幾天前壞掉了,我發現廚房抽屜非得放一把這種實用的工具不可,於是前往當地的五金行買把新的。我回來的時候,仲介留了封信給我,冬市苑的每個住戶都收到了類似的信件,客客氣氣通知我們每個人,我樓下的公寓即將出售。前任居民李察森先生住在一號公寓三十年之久,但聖誕節以前不久過世了,住處於是騰了出來。他女兒是語言治療師,住在紐約,就我所知,她並不打算回倫敦。於是我只好接受不久之後就會被迫在大廳跟陌生人互動,甚至必須假裝對對方的生活有興趣,或是不得不吐露一點關於自己的小細節。
我和李察森先生向來維持著完美的鄰居關係,因為我們從二○○八年起就不曾交換過隻字片語,他入住的早年歲月,我們一度關係友好,他偶爾會上樓來跟我先夫艾德格下盤棋,但我跟他素來只是相敬如賓。他總是稱呼我為「芬斯比太太」,我則稱他為「李察森先生」。我最後一次踏進他的公寓,是在艾德格過世四個月之後,他邀請我共進晚餐,我接受了邀約,然後婉拒了對方發動的愛情攻勢。他對我的拒絕反應激烈,後來我們幾乎形同陌路,成了兩個同住一棟樓房的陌生人。
我位於梅費爾區的住處登記為公寓,但這有點類似將溫莎城堡形容為女王週末的避居處。我們這棟樓房的每戶公寓──總共有五戶,一戶在地面樓層,上面兩層則各有兩戶──占地一千五百平方英尺,在倫敦地產的黃金地段,每戶都有三間臥房、兩間半浴室,加上海德公園的景色,按照可靠的資訊來源,每戶價值介於兩百至三百萬英鎊之間。艾德格在我們婚後幾年拿到了一筆豐厚的財產,是終身未婚的姑姑所遺贈,他更想搬到倫敦市中心外更寧靜的地方,但我事先做了點研究,打定主意不只要住在梅費爾區,如果有可能的話,更要住進這棟建築。財務上來說,原本看似毫無可能,但是有一天,彷彿有如神助,柏琳達姑姑過世了,一切都改變了。我一直計畫要向艾德格解釋,我這麼急著住進這裡的原因,可是從來不曾說過,我現在還滿後悔的。
我丈夫非常喜歡孩子,但我只同意生養一個,並在一九六一年生下我們的兒子卡登。近年來房地產增值,卡登鼓勵我賣掉這戶公寓,在城裡房價較低的地區買個坪數小點的單位,但我想那是因為他擔心我可能會活到一百歲,急著趁年輕還能享受的時候,拿到他的那份遺產。他結婚過三次,現在第四次訂婚;我已經放棄認識他生命中的女性。我發現每每才認識她們,她們就被送走,然後新的款式就會進駐,我還得花時間學習她們的特性,就像新型洗衣機或電視機。孩提時代,他就用類似的無情方式對待朋友。我們經常通電話,他每兩週就會過來吃一次晚飯,不過我們的關係複雜,部分因為我在他九歲時從他生活中缺席整整一年。事實是,我跟小孩相處就是不自在,而我發現小男孩特別難相處。
我對新鄰居的顧慮不是他或她可能發出不必要的噪音──這些公寓隔音效果很好,即使在這裡那裡有幾個瑕疵,經年以來,我已經習慣透過李察森先生天花板傳上來的各種奇特聲響──但我痛恨自己井井有條的世界可能會被顛覆。我希望進駐的人不會有興趣認識住樓上的婦人。也許來個病弱殘疾的老人家,鮮少離開家門,每天早上有家務幫手來探訪。或者是年輕專業人士,星期五下午消失,返回自己週末的家,然後星期天深夜才回來,其餘的時間都在辦公室或健身房。有個謠言傳遍了這棟樓,說有個事業在一九八○年代到達顛峰的知名流行樂手考慮把那戶當成退休以後的住家,但令人高興的是,這件事並無下文。
只要房仲把車停在外面,護送客戶參觀那戶公寓,我的窗簾就會跟著掀動:我針對每個潛在的鄰居都做了點筆記。有個前景看好七十出頭的夫婦,說話輕聲細語,手牽手,問這棟樓能否養寵物──我在樓梯井上側聽──被告知不行時,似乎相當失望。一對三十幾歲的同志伴侶,從他們刻意仿舊的服飾、帶有凌亂感的外觀看來,口袋肯定頗深,但他們說這個「場域」對他們來說可能有點小,覺得自己不大能跟它的「敘事」起共鳴。一個長相不起眼的年輕女子說,有個叫史提芬的人會很愛這裡的挑高天花板,除此之外並未洩漏自己的意願。想也知道,我希望是同志──他們很適合當鄰居,而且不大有機會生兒育女──但他們似乎興趣最低。
然後,幾個星期過後,仲介不再帶人來參觀,待售訊息從網路上消失了,我猜交易已經談定。不管我喜不喜歡,總有一天醒過來就會發現搬家貨車停在外頭,有個人或幾個人正把鑰匙插進前門,住進我樓下。
噢,我真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