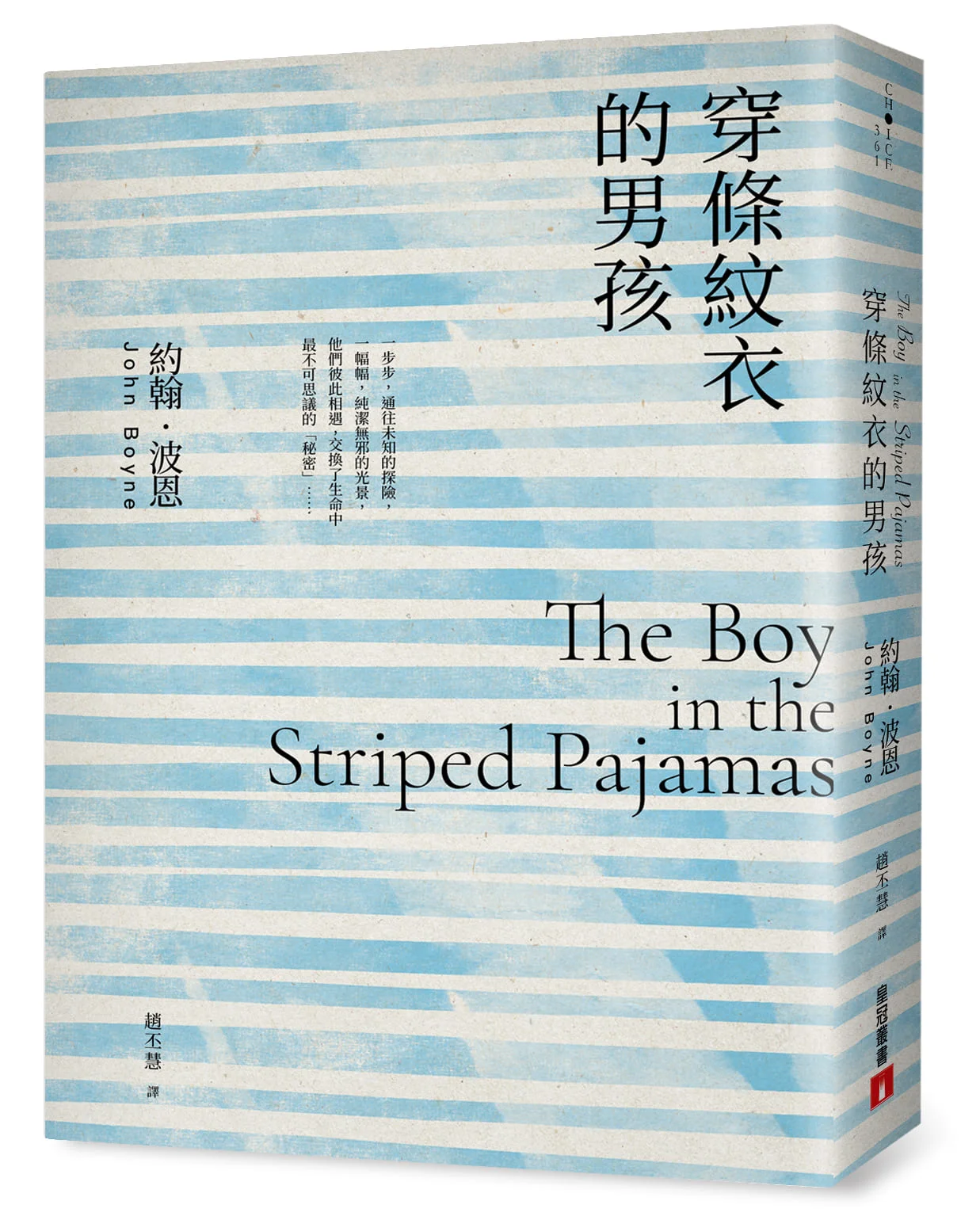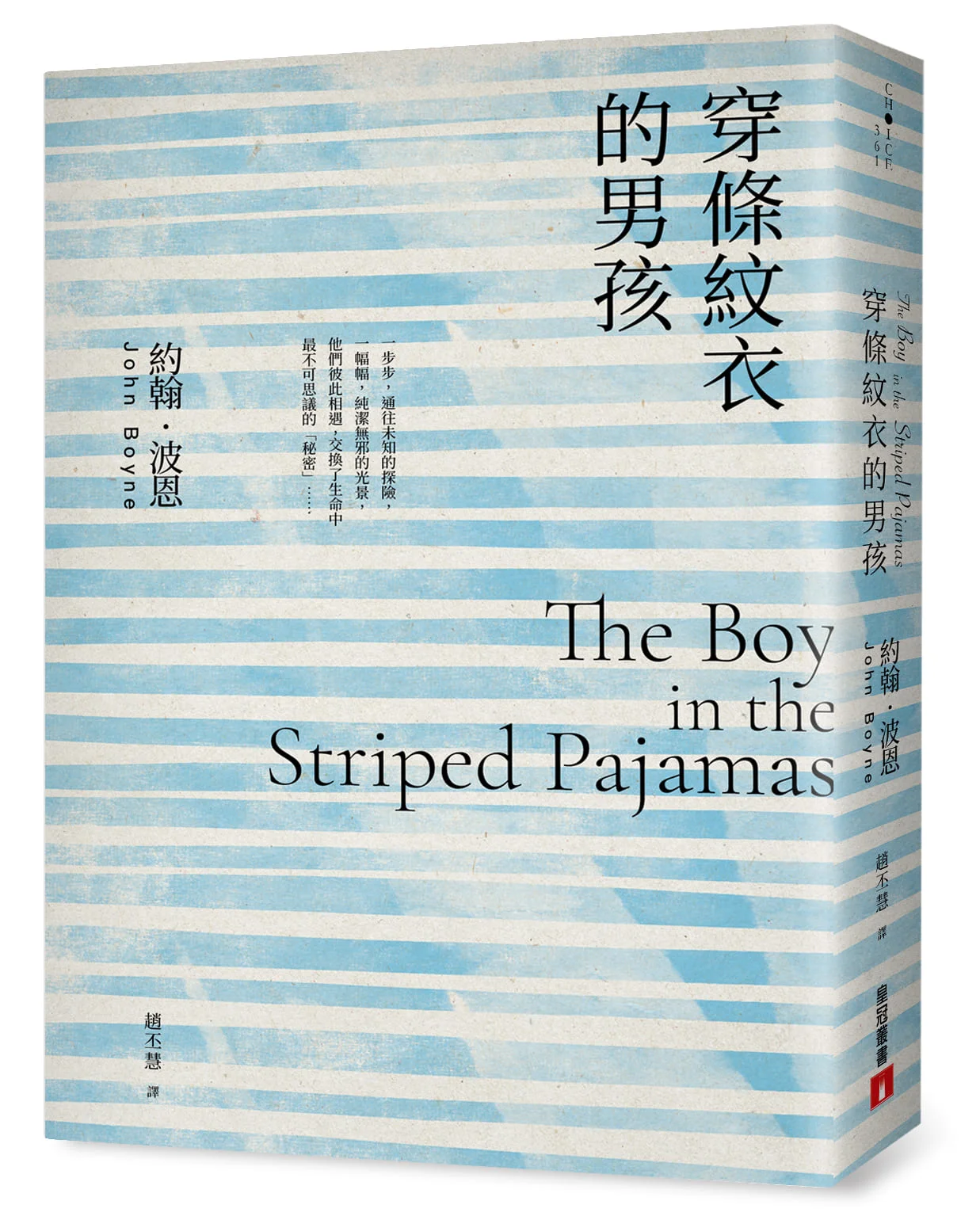內容試閱
「很抱歉,布魯諾。」媽媽說。「不過,你們的計畫只好等一等了,在這件事上,我們實在是別無選擇。」
「媽?」
「布魯諾,夠了。」她說,現在變得疾言厲色,同時站了起來,表示夠了就是夠了。「上個禮拜你不是還在抱怨這裡變了很多嗎?」
「我是不喜歡到了晚上就得把燈都關掉。」他承認。
「又不是只有你一個人得關燈,」媽媽說。「這是為了大家的安全。誰知道呢?說不定我們搬家了反而會更安全一點呢。好了,我要你上樓去幫瑪麗亞收拾你的行李。拜某人之賜,我沒有足夠的時間來準備。」
布魯諾點頭,難過地走開,知道所謂的「某人」是大人替代「爸爸」的用語,而且是他被禁止使用的。
他慢吞吞地上樓,一手扶著欄杆,心裡一面在亂猜,新工作那地方的新房子裡,會不會像這裡一樣有這麼好的欄杆可以讓他溜滑梯?這棟屋子的樓梯扶手從頂層──就在小閣樓的門口,如果他踮著腳尖、緊緊扶著窗台的話,就可以從這裡俯瞰整個柏林──一直延伸到一樓,樓梯口就在兩扇大橡木門前面。布魯諾最喜歡爬上欄杆,一路滑下來,一面歡呼。
從頂層滑到下一層,有他父母的房間,還有大浴室,那是他不可以進入的房間。
再從這一層滑到他的房間以及葛蕾朵的房間所在的那一層,還有一間小浴室,他應該使用這一間,不過事實上並非如此。
再滑到一樓,你從欄杆上飛出去,不是兩隻腳穩穩站住,就是被扣五分,你又得從頭來過。
這棟屋子最棒的地方就在樓梯的欄杆,另外就是爺爺、奶奶住得很近──他一想到這裡,就不由得猜想他們是不是也會一起來。他自己假設答案是肯定的,因為再怎麼樣也不能把他們丟下來不管啊。丟了葛蕾朵沒什麼關係,反正她是個討厭鬼,把她留下來看屋子反倒比較好。可是爺爺、奶奶呢?那可是另一回事。
布魯諾慢慢上樓回去他自己的房間,但是在進房間之前,他回頭望著樓下,看見媽媽進了爸爸的辦公室。辦公室正對著大餐廳,而且是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禁止進入的。他聽見媽媽大聲對爸爸說話,最後爸爸的嗓門更大,壓過了她,兩人的對話才結束,接著辦公室的門被關上,布魯諾什麼也聽不見了,所以他覺得回房間去,由他自己來收拾行李比較好,不然瑪麗亞可能會粗手粗腳地把他衣櫃裡的東西全都拉出來,就連那些他藏在衣櫃最裡面、屬於他個人、別人管不著的物品也會遭殃。
第二章:新房子
第一眼看見他們的新房子,布魯諾就睜大了眼睛,嘴巴圓得像個O字形,手臂又伸了出來。新房子的每一吋好像都跟他們的舊房子相反,他完全不敢相信他們真的要搬進去住了。
柏林的家位在安靜的街道上,左右是一連串跟他家一樣的大房子,不管什麼時候看起來都賞心悅目,因為每一棟房子看起來雖然差不多,但還是有那麼一點兒不同。而住在那些房子裡的男生,如果跟他是朋友,他們就玩在一塊;如果不好惹,那他就躲得遠遠的。但是,新房子卻是孤伶伶地矗立在一片空盪盪又荒涼的地方,放眼望去一棟房子也看不見,也就是說除了他們這一家之外,沒有別的鄰居,沒有男生可以和他玩,不論是朋友還是對頭。
柏林的房子很大,雖然他住了九年,照樣可以找到一些他並沒有真正探索完的角落,甚至有些房間他只能算是驚鴻一瞥,比方說爸爸那間列為絕對禁區的辦公室。新房子只有三層樓:三間臥室都在頂樓,但只有一間浴室;一樓是廚房、餐廳、爸爸的新辦公室(他已經猜到是老規矩:禁止進入,絕無例外);還有地下室,那兒是僕人睡的地方。
柏林的房子四周都是街道,街上大房子林立,朝市中心走,隨時隨地都可以看見有人在街上漫步,停下來彼此聊上幾句;也有人忙忙碌碌地,說沒時間停下來,今天不行,他們有一百零一件事情得辦。街上還有明亮的商店,以及蔬果攤,大托盤上堆著高麗菜、胡蘿蔔、花菜和玉米;有的攤子上,韭蔥、蘑菇、蕪菁和芽菜多得都溢出來了,有的擺了滿滿的生菜、四季豆、夏南瓜和防風草。有時他喜歡站在這些攤子前,閉著眼睛,吸入果菜的芬芳,香香甜甜和生氣蓬勃的味道混合,讓他吸到最後頭暈起來。但是新房子附近沒有別的街道,沒有人在漫步,也沒有人來去匆匆,而且絕對沒有商店或賣水果、蔬菜的攤子。要是他閉上眼睛,他只會感到空盪盪與寒冷,彷彿他是到了全世界最孤獨的地方、窮鄉僻壤的最中央。
柏林的街道上還會擺著桌子,有時他和卡爾、丹尼爾與馬丁放學後走路回家,會看見男人、女人坐在桌子旁,喝著泡沫飲料,大聲笑著;他總以為坐在桌子旁的人都是很風趣的人,因為不管他們說什麼,總是有人會笑。可是不知為什麼,新房子卻讓布魯諾覺得從來沒有人在裡面笑過,屋裡也沒什麼可笑的、沒什麼能讓人開心的。
「我覺得搬家不是好主意。」布魯諾在他們抵達後幾小時說,瑪麗亞正忙著在樓上把他的行李箱打開。(新房子的女傭也不止瑪麗亞一個,還有另外三個人,都瘦得像皮包骨,講話都壓低聲音。還有一個老頭子,布魯諾聽說他是負責幫他們準備每天的蔬菜的,也會在晚餐時服侍他們,他不但一臉不高興,還帶著點憤怒。)
「我們沒那個閒工夫胡思亂想。」媽媽說,打開一個盒子,裡面裝著爺爺、奶奶在她嫁給爸爸時送的一套六十四只玻璃杯。「某人幫我們做了決定。」布魯諾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就假裝他媽媽根本沒開口。
「我覺得搬家不是好主意。」他又說一遍。「我覺得我們最好把這裡忘了,回家去,就當作是上一次當學一次乖。」他又補上一句。他最近才剛學會「上一次當學一次乖」這句話,決定有機會就拿出來用。
媽媽啞然失笑,小心地把玻璃杯放在桌上。「我送你另一句話,」她說。「叫做既來之則安之。」
「我不覺得安得了。」布魯諾說。「我覺得妳應該告訴爸妳改變主意了,呃,要是我們今天要住在這裡,在這裡吃晚飯、過一夜,那沒關係,因為我們都累了。可是,如果我們想在明天的下午茶以前趕回柏林,那就應該明天一大早起床。」
媽媽嘆口氣。「布魯諾,你為什麼不上樓去幫瑪麗亞整理呢?」
「沒道理要把行李拿出來啊,我們不是──」
「布魯諾,照我的話去做!」媽媽嚴厲地說,因為顯然她打斷他的話就沒關係,而他可不能有樣學樣。「我們搬來了,在可預見的將來,這裡就是我們的家,我們得隨遇而安,懂了嗎?」
他不懂什麼叫「可預見的將來」,也誠實地說了出來。
「意思是我們現在就要住在這裡,布魯諾。」媽媽說。「沒得商量。」
布魯諾覺得胃痛,感到心裡似乎有什麼在漸漸擴大,那玩意兒從他心裡的最底層往上冒,冒到外在的世界,不是讓他大聲喊叫說這一切都錯了,一點也不公平,早晚有一天,有人會為這個大錯付出代價;要不就是害他嚎啕大哭。他不明白究竟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前一天他還高高興興地在家裡玩,有三個這輩子最要好的朋友,從樓梯欄杆上滑下來,踮著腳尖俯瞰柏林;現在他卻困在這個又冷又討厭的房子裡,多了三個說悄悄話的女傭、一個既不開心又氣呼呼的侍者,困在這個沒有人會再開心起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