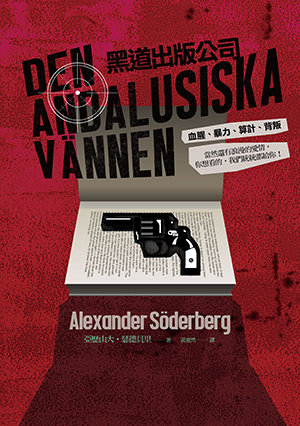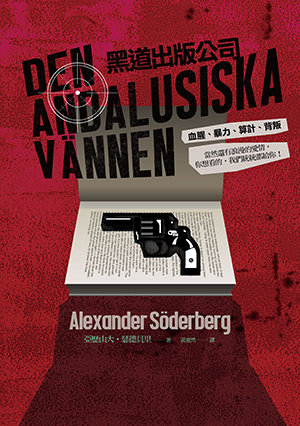內容試閱
【斯德哥爾摩,六星期前,五月】
她身上有種特質讓一些人說她看起來不像護士,她永遠無法理解這是讚美還是侮辱。她有著深色的長髮和一雙綠眸,有時候給人一種她正要放聲大笑的印象。她並沒有很愛笑;那只是外表看起來而已,彷彿她生來眼裡就含著笑。
她走下樓,樓梯在她腳下嘎吱作響。這間屋子興建於一九一一年,是棟相當小巧的黃色木造花園住宅,有鉛條窗、磨亮的古老拼花地板,和一個原本可能較大的花園,她頭一次見到這間房子就意識到,這裡是她在地球上的歸屬。
廚房的窗子敞開,迎向寧靜的春天傍晚,從窗戶飄進來的味道比較像是夏天,而不像春天。夏天應當再過幾星期才到來,但是暑熱提前來了而且不願離,現在熱氣就只是懸浮在那兒,沉重且完全靜止。她感謝並需要熱度,慶幸能敞開門窗,能自由自在地進出。
遠處有輕型機車的聲響,有隻畫眉在樹上唱歌,也有其他的鳥類,不過她不知道牠們的名字。
蘇菲拿出瓷器擺了兩人份的餐具,用最精緻的盤子,最講究的刀叉餐具,和最完美的玻璃杯,盡其所能地躲避上班日。她知道她將會獨自一人用餐,因為艾伯特只在肚子餓的時候進食,與她的時間很少重疊。她聽見他的腳步聲出現在樓梯上,運動鞋踩在老舊的橡木上;有點太過笨重、太過用力,艾伯特對於自己製造出的噪音絲毫不感到困擾。他走進廚房,她對他展露笑容;他回以稚氣的微笑,一把拉開冰箱門,盯著裡頭的東西,站了好半晌。
「艾伯特,把冰箱關上。」
他站在原地;她吃了一會兒,閒散地瀏覽報紙,然後抬起頭來,再說一遍同樣的話,這回聲音裡參雜了少許惱怒。
「我動不了……」他戲劇化地低聲說。
她大笑起來,與其說是因為他冷面滑稽的幽默感而發笑,不如說是因為他這人就是有趣,讓她感到快樂……甚至,驕傲。
「你今天過得怎樣啊?」她問。
她看得出來他快要笑出來了。她認得出那種跡象,他向來認為自己的笑話很好笑。艾伯特從冰箱拿出一瓶礦泉水,砰的關上門,接著跳到廚房的流理台上。他旋開瓶蓋二氧化碳發出嘶嘶聲。
「每個人都瘋了。」艾伯特說,喝了一小口水後,他開始將他所想到的一天生活片段逐一告訴她。在他開老師和其他人的玩笑時,她仔細地傾聽並且露出微笑,她看得出來他喜歡引人發笑,但忽然間他就說完了。蘇菲永遠搞不清楚話題將在何時結束,他就是突然打住,彷彿受夠了他自己和他的幽默感,她想要向他伸出手要求他留下來,繼續搞笑,繼續當個既友善同時又難以相處的人,但是這樣是行不通的,她以前試過但失敗了,因此她任由他走開。
他消失在走廊上。一陣短暫的靜默;也許他正在換鞋子。
「妳欠我一千克朗。」他說。
「為什麼?」
「清潔女工今天來了。」
「不要叫人家『清潔女工』。」
她聽見他拉上夾克拉鍊的聲音。
「那我應該叫什麼?」
她不知道。他從門口走出去。
「媽,親親。」他說,他的聲調突然變溫柔。
門關上,透過敞開的窗戶她能聽見他的腳步踩在外面碎石子小徑上。
「你如果會晚回來的話,要打個電話給我喔。」她大聲喊。
蘇菲繼續平常的生活。收拾桌子,整理一下,看點電視,打電話給朋友隨意閒聊──晚上的時間就過了。然後她上床,試著讀點床頭櫃上的書,書的內容是有關一個女人幫助布加勒斯特的街頭流浪兒童後,找到了新人生的故事。書枯燥乏味,那女人自命不凡,蘇菲與她毫無共通點。她闔上書,如往常一樣獨自在床上睡著。
八個小時後,時間是清晨的六點十五分,蘇菲起床、淋浴、擦拭浴室的鏡子,鏡面蒙上水氣時顯露出隱藏的字︰「艾伯特,AIK」和一大堆其他難以辨認的字,都是他邊刷牙邊用指頭寫上去的。她告訴過他別再那麼做,不過他似乎完全不管,在某種程度上她挺喜歡如此。
她站著吃個簡單的早餐,一面看早報的頭版。很快就到了該出門上班的時間。她高聲對艾伯特喊三次該起床了,十五分鐘後她騎著腳踏車讓早晨和煦的空氣喚醒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