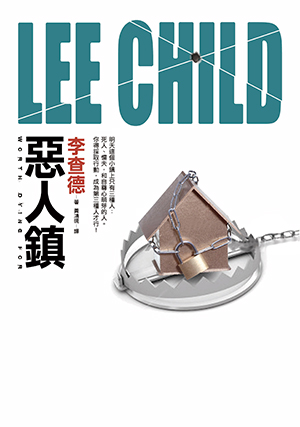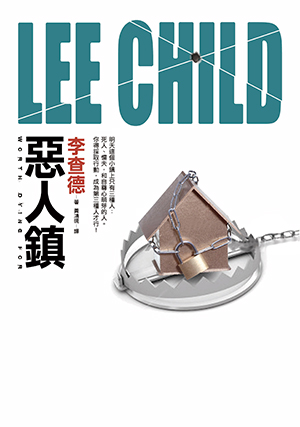內容試閱
就在這時,電話響了。
事實上是兩支電話響了,共用一個號碼的兩支話機,一支話機放在接待櫃檯,另一支放在吧台後方的置物架上。染髮男身兼數職,分身乏術。他接起電話說:「阿波羅客棧您好。」自信滿滿,聲音清亮,熱情洋溢,彷彿接到的是旅館營業第一晚的第一通電話,他聽了一陣子後把話筒壓到胸前說:「醫生,是找你的。」
李奇下意識地轉頭尋找醫生。沒人啊?結果他旁邊的酒醉男說:「是誰?」
染髮男說:「是鄧肯小姐。」
酒醉男說:「她怎麼了。」
「鼻血流個不停。」
酒醉男說:「跟她說你沒看到我。」
染髮男幫他扯完謊,掛掉電話。酒醉男趴倒吧台,臉幾乎和酒杯杯緣一樣高。
「你是醫生?」李奇問。
「要你管。」
「鄧肯小姐是你的病患?」
「算是。」
「你還打發掉她?」
「你是哪根蔥?道德委員會的人嗎?她不過是流鼻血罷了。」
「是鼻血流不停,有可能是很嚴重的狀況。」
「她今年三十三歲,身體很健康,沒有高血壓和血液相關疾病的病史,也沒嗑藥。沒什麼好慌的。」酒醉男舉杯,含一口,嚥下肚,含一口,嚥下肚。
李奇問:「她結婚了嗎?」
「怎麼?這年頭婚姻變成流鼻血的原因之一了嗎?」
「有時確實如此。」李奇說:「我當過憲兵,有時候我們會被叫到基地外或基地內的眷屬區去看看。受家暴的女人會服用大量的阿斯匹靈止痛,但阿斯匹靈也會降低血液的凝固性,所以她們下次被打就會血流不止。」
酒醉男不發一語。
酒保別過頭去。
李奇說:「怎麼?這種事在這裡常發生嗎?」
酒醉男說:「她只是流鼻血。」
李奇說:「你怕被捲進別人的家務事裡?」
沒人說話。
「她可能還受了其他傷,而且是肉眼看不太出來的那種。」李奇說:「她是你的病人。」
沒人說話。
李奇說:「鼻子流血跟其他部位流血沒兩樣,只要血流不止就會昏倒,像中刀傷失血過多那樣。如果她今天受的是刀傷,你就不會置之不理對吧?」
沒人說話。
「反正這件事與我無關,你的狀況也不好。你甚至醉到不能開車去找她,不管她家有多近都不行。不過你該打通電話找別人過去看一下。」
酒醉男說:「沒有別人了。急診室在六十英里外,但他們不會派救護車來載流鼻血的人。」
李奇又喝了一口咖啡,酒醉男沒動他的杯子。他說:「我當然不能開車,不過我到那裡之後就沒問題了。我是個好醫生。」
「既然你都說自己是好醫生了,我可不希望看到你做出壞決定。」
「比方說,我知道你有什麼問題,我是說身體上的問題,至於心理方面的問題,我就不予置評了。」
「說話別太超過啊,老兄。」
「不然是要怎樣?」
李奇不發一語。
「她只是流鼻血而已嘛。」酒醉的醫生又強調一次。
「你會怎麼治療?」李奇問。
「局部麻醉,用紗布塞住鼻孔。不管她有沒有服用阿斯匹靈,紗布的壓力都能止住她的血。」
李奇點點頭,他在軍中看過別人這樣處理。他說:「走吧,醫生,我開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