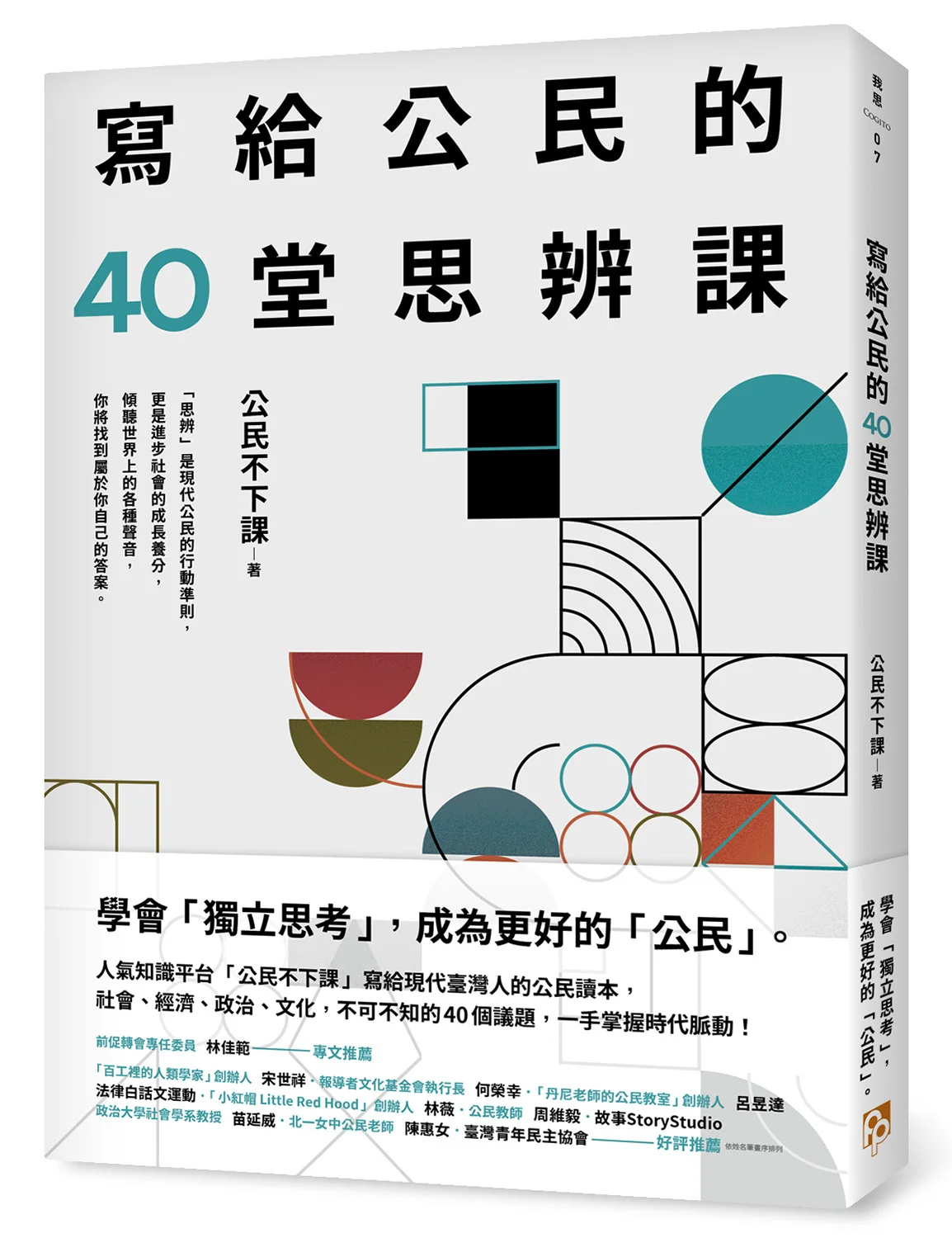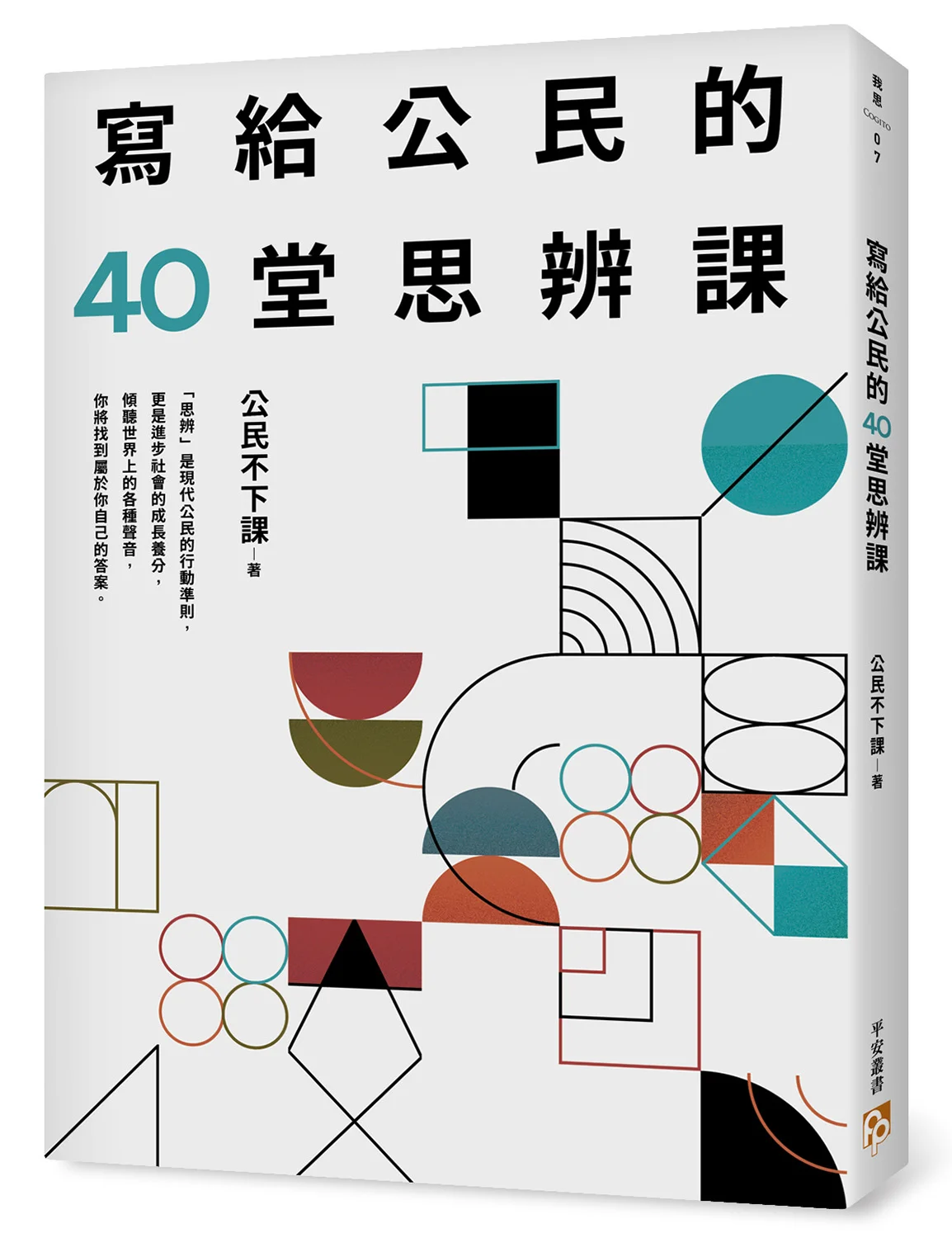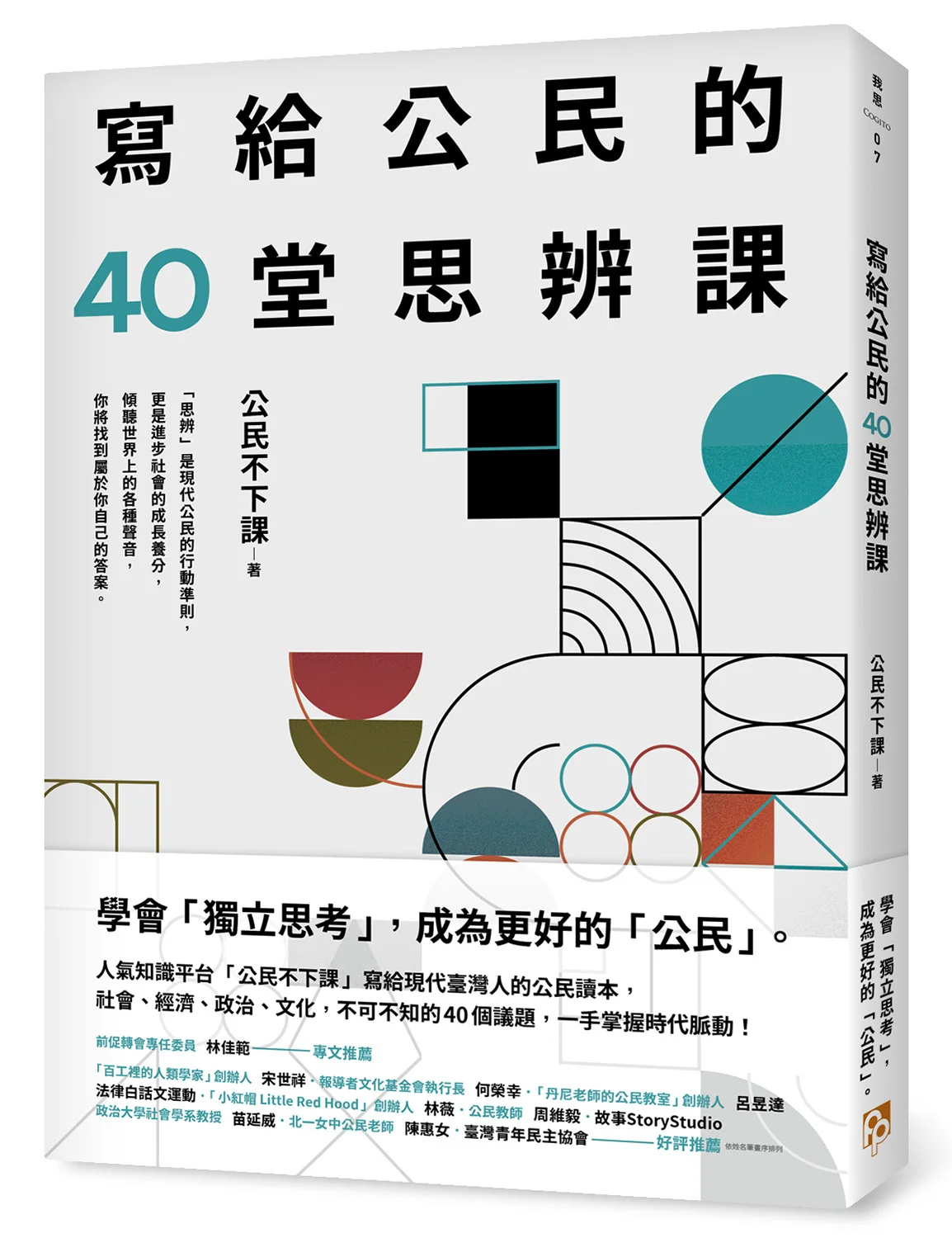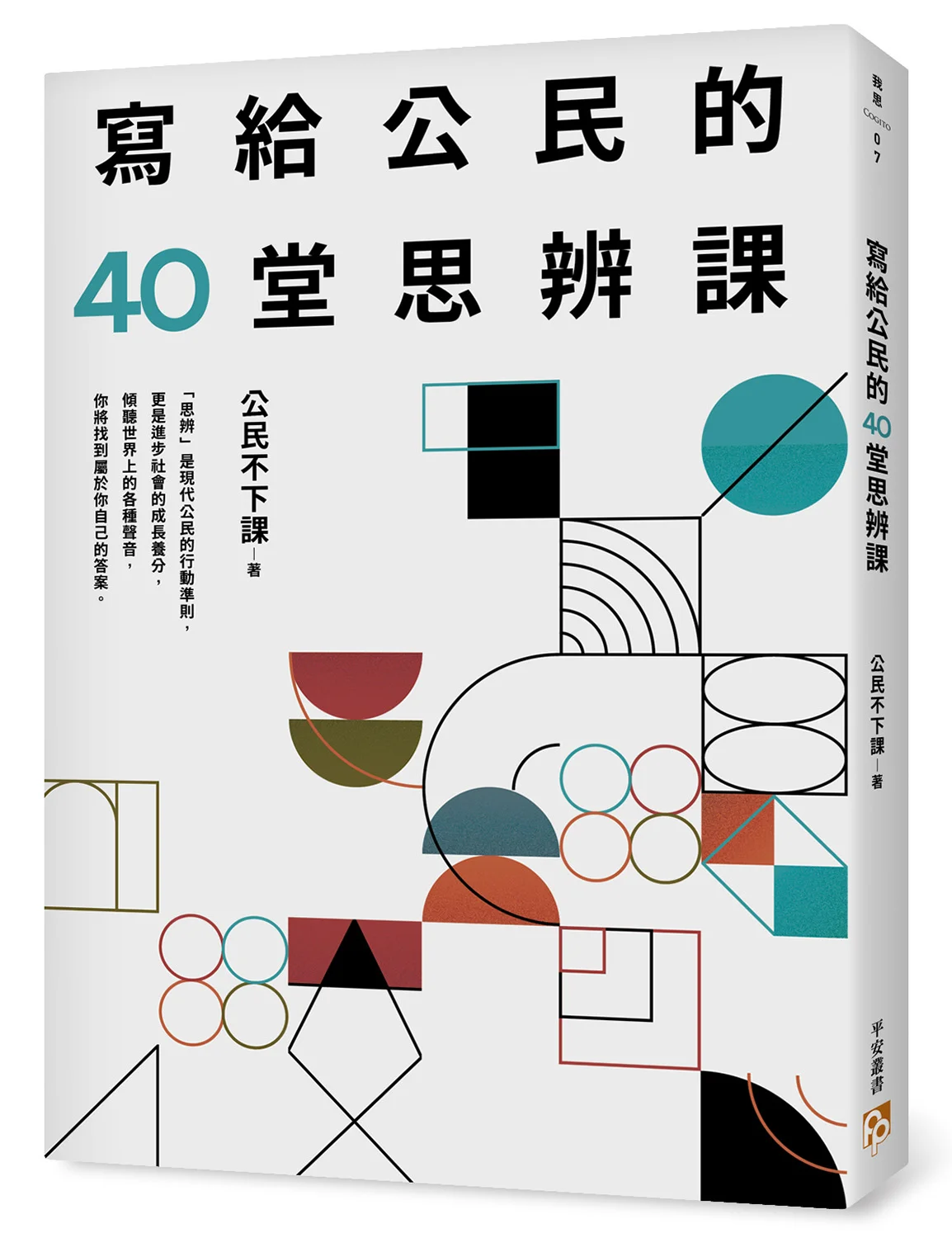內容試閱
瘟疫與國家治理── 傳染病大流行下的社會
瘟疫與社會變遷:我們與傳染病的鬥爭史
二○一九年,新冠肺炎造成全球大流行,顛覆了許多人的生活,也預計成為二十一世紀改寫人類歷史的重大事件。回顧傳染病史,皆大大影響了人類的歷史進程。十四世紀的黑死病(鼠疫)造成了近兩億人死亡,動搖了歐洲傳統的封建佃農制度,大量減少的人口使工資上漲,促使技術革新;教會的失能則引發了宗教改革。
而今日對付傳染病的重要武器─ 社交隔離、戴口罩、公衛管理等也在黑死病的時代誕生。十五世紀開始,廣泛且反覆流行的天花造成了約三億五千萬人死亡,大量美洲原住民染疫後使歐洲人成功殖民美洲。天花也促成了人類史上的第一種疫苗誕生:明清時期的中國,透過種人痘使人體獲得免疫力、十八世紀英國醫師則進一步改種牛痘減少不良反應。但強制接種也促使「反對接種牛痘者聯盟」成立,認為強制接種有害人權,開啟了反疫苗運動的先聲。十九世紀英國倫敦的霍亂,則帶來了第一波的衛生下水道革命,現在仍是開發中國家對抗傳染病的利器。
人類在一次次與傳染病鬥爭的過程中獲得了更多的工具與知識,也顯示了傳染病複雜地交織在政治和社會的脈絡中。是否能成功擊退傳染病,甚至會影響到政權的存續。疾病的治療是醫學,瘟疫的管控卻考驗了政府與社會間的信任與合作。本文試圖從國家治理的角度出發,思考在瘟疫蔓延之下,如何凸顯國家與社會的複雜脈絡中治理的缺失。
再次肆虐的傳染病:一九四六年臺灣衛生行政癱瘓
臺灣在日本時代時,建立起「隔離、消毒、預防接種」等基礎衛生觀念,公共衛生及環境清潔受重視,與衛生條件相關的霍亂及鼠疫受到很好的控制。然而,戰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由於生活環境惡化,加上很多傳染病自中國傳入臺灣,已控制住的狂犬病、鼠疫及霍亂又開始猖獗,甚至天花都發生大流行。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天花更達五千個病例,死亡率也高達三成。嘉義布袋因霍亂而遭政府封城,在沒有任何醫療照護的狀況下,死亡率逼近六成。
柯喬治(George H. Kerr)所著的《被出賣的台灣》一書即指出,瘟疫的橫行、與瘟疫防治中官員的腐敗也是二二八事件的遠因之一。時任衛生局局長的經利彬向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領取了抵抗瘧疾的「抗瘧劑」,結果卻在事後阻止公單位發放抗瘧疾藥片,因為他已成立私人公司來販賣類似藥劑以從中獲利。
戰後臺灣瘟疫蔓延,可歸納為幾個因素:一是因為日治時期,日本政府所強力推行的疫苗注射等西方傳染病防治觀念,缺乏與民眾之間的政策溝通,使衛生習慣的訓練未能深入民間,一旦高壓的殖民政府撤出,衛生習慣就故態復萌了。戰後的人力、物力不足,也促使垃圾和水肥難以迅速清運至市郊。最後,傳染病爆發後官員怠惰的處理、腐敗與利己的心態,加上外來政權對本土人民的不信任感,都促使瘟疫不能在初期獲得掌握。
西非伊波拉病毒:殖民史下的社會與國家對立
非洲大陸上有許多文化、地理、種族上都歧異性頗大的國家,它們最大的共同點是近代的殖民歷史,也形塑了多數非洲國家治理的形式。戴倫.艾塞默魯、詹姆斯.羅賓森指出殖民體制屬於榨取型制度,少數菁英壟斷政治經濟利益,卻和在地社會、文化、族群嚴重脫節、國家治理能力低落。不幸的是,獨立過後的獨裁者卻繼承了這種制度,使權力集中在少數菁英集團,導致政治腐敗,公衛與醫療基礎建設薄弱,進而讓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度低,對醫療體系的信任度也低。
二○○○年前後,伊波拉疫情爆發,疫區周圍不時出現居民和軍警的衝突,社會與政府間的不互信成為病毒攻擊的弱點。賴比瑞亞在疫情擴散時實施了區域宵禁,動用軍警管控民眾流動。其首都蒙羅維亞(Monrovia)發生了居民攻擊一處收容疑患伊波拉患者的醫療中心的事件,民眾搶奪設備以及沾染血液的床單床墊,並造成病患和醫護人員逃跑四散。在獅子山第三大城凱內馬( Kenema),數千民眾因為對治療伊波拉醫院的不信任,試圖攻入一個醫療院所內,並揚言火燒醫院,放走病人。獅子山政府於是在疫區部署大量軍警,以防社會衝突失控。
人民的不配合與不信任,使疫情的管控更加艱難。如發現伊波拉病毒的比利時科學家皮特(Peter Piot)指出:「民眾對當局高度不信任。信任必須恢復,倘若沒有信任,就無法對付伊波拉這類傳染病。」
新冠肺炎:比較全球性的治理「 破口 」
相較於其他傳染病,新冠肺炎的1~2%死亡率已經相對「溫和」,然而它快速傳播的特性碰上了全球化時代,引起了一場不僅是在健康公衛領域,更是經濟與政治的浩劫。同時,也因為其全球化、快速傳播的特性,使我們得以觀察出這場疫情暴露了哪些國家的治理缺失。
在疾病最早爆發的中國,在資訊等於權力的獨裁者困境下,吹哨者們的預警無法傳到大眾手中,手段強硬的封城又使民眾大批逃離武漢,失去了第一時間控制疫情的時機。然而,迅速且有效率的中央政府介入之後,中國成為了世界上最快控制疫情的國家之一,顯示威權政體有弊也有利。
在疫情爆發前的二○一九年十月,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布全球健康安全指數,最能對抗流行病的國家中,美國和英國分別奪下了第一名與第二名的寶座。然而,在真正的疫情底下,兩國在大流行初期的確診數與死亡率卻「領先」各國。這顯示了,最強的製藥能力、最好的研究大學與實驗室、最先進的醫療機構不是對抗大流行最重要的能力。英美兩國新自由主義的政府在關鍵時刻都缺乏整合與分配資源的力量,使國家實力成就了私人的富裕而非公眾的福祉;大流行敲響了治理的警鐘,使政府「向左走」,透過紓困方案重新投資於公眾、整合機構以應對危機,預計將永遠改變英美政治的面貌。英美兩國強大的生物科技實力也創造出了最有效的疫苗,成為了結束這場疫情的關鍵。
在亞洲,如印度與東南亞各國,疫情帶來的最大挑戰是醫衛基礎設施的不足,以及中央政府的施政能力無法覆蓋整個領土範圍,快速經濟發展所造成的「兩個社會」:城市中產階級與傳統農民社會難以同軌規制。相較之下,南韓、新加坡、臺灣等政府施政能力能貫穿全境,也帶來較佳的防疫效果。但性工作者、外籍移工等卻因為弱勢,被排除於主流社會之外,當疫情出現「破口」,就會威脅到整體社會的安全。日本則因為戰後如痲瘋病強制隔離、缺乏人道對待等侵害人權的歷史,使政府權限大幅度的縮減政策,連基礎的隔離都沒有相關罰則,「緊急狀態宣言」的強制力也有限,使疫情在高低峰之間反覆。
貫穿所有國家防疫問題的,是國家內部原先的不平等。國際組織樂施會(Oxfam International)在《不平等的病毒》(The Inequality Virus)報告中指出,弱勢族群中如女性、有色族裔、貧窮社區居住者較容易染疫,是全球性的現象;他們的工作更有可能無法遠距上班、較難申請有薪病假、無相關防護知識或衛生設備、負擔不起醫療費用等。換個角度來說,一個更注重平等與關懷弱勢的系統,也是面對疫情時最有韌性的防護網。
過去歷史上每一次的瘟疫大流行,都證明了人類有能力在創傷中持續前進與創造文明;新冠肺炎大流行是迎來大衰退的起點,或是社會轉型的開始,關鍵都在我們手中。
失控的駭人傳染病,往往直攻國家治理、基礎設施,以及社會信任網絡的罩門。傳染病的演化和傳播,是政治、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交織的結果。傳染病的爆發,是對一個國家的總體期末考,考驗我們的國家政策透明度、資源在地區間與階級間的平等程度、國家與國民之間的溝通的誠意、國民對政府的信任感等等。
疫病的流行永遠都不會消失,我們社會如何鍛鍊出和持續演化的疾病共存的能力,是每個政權與社會永遠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