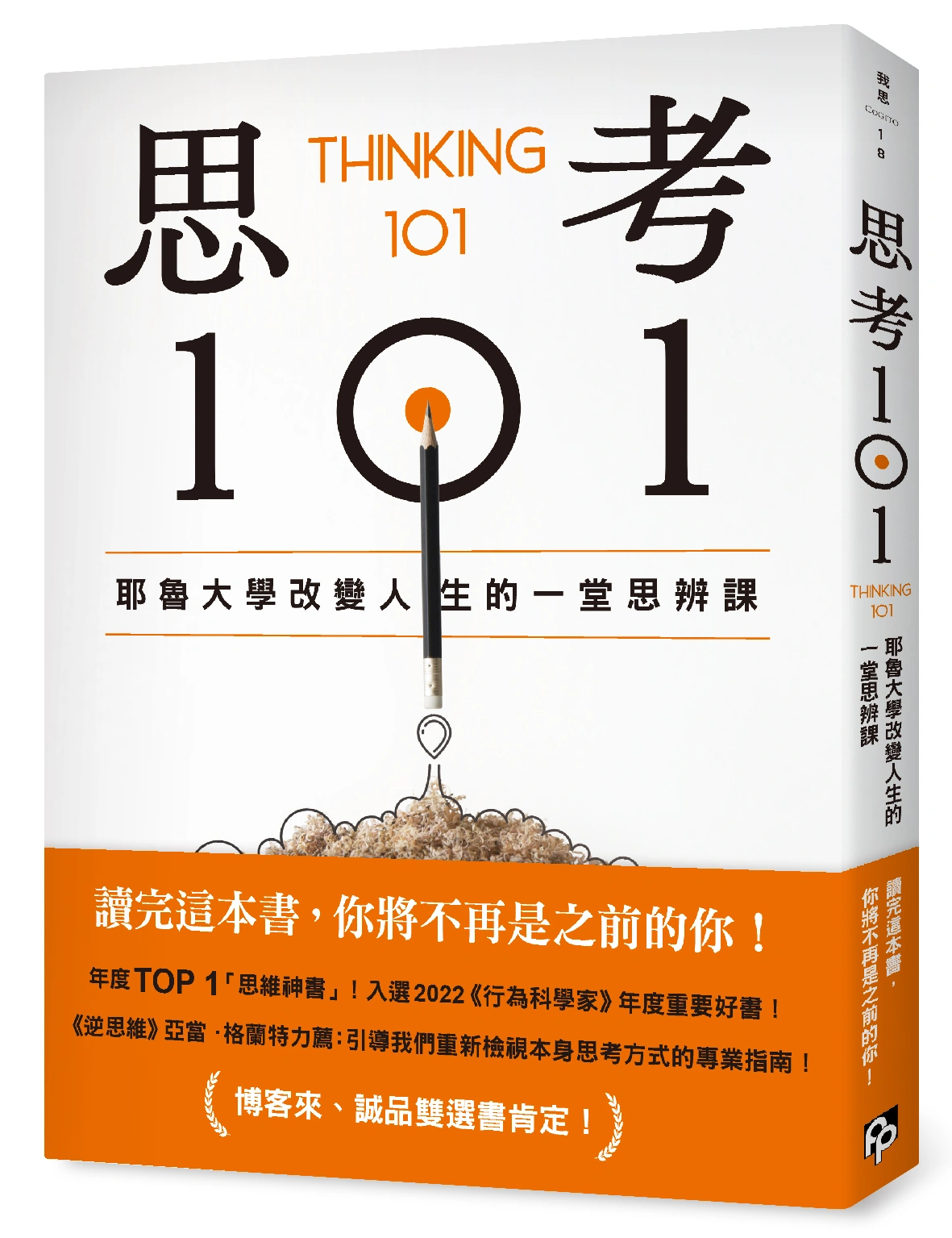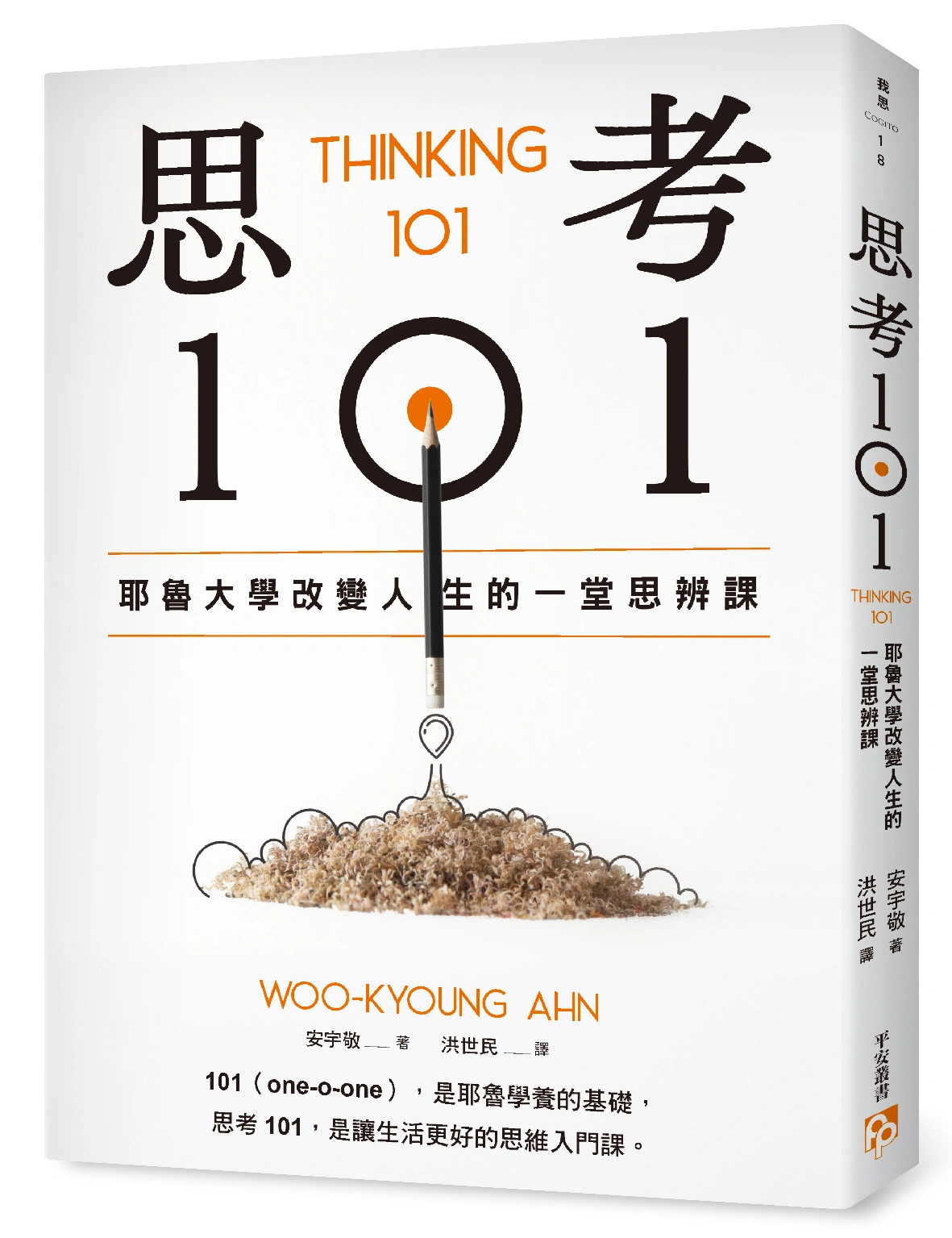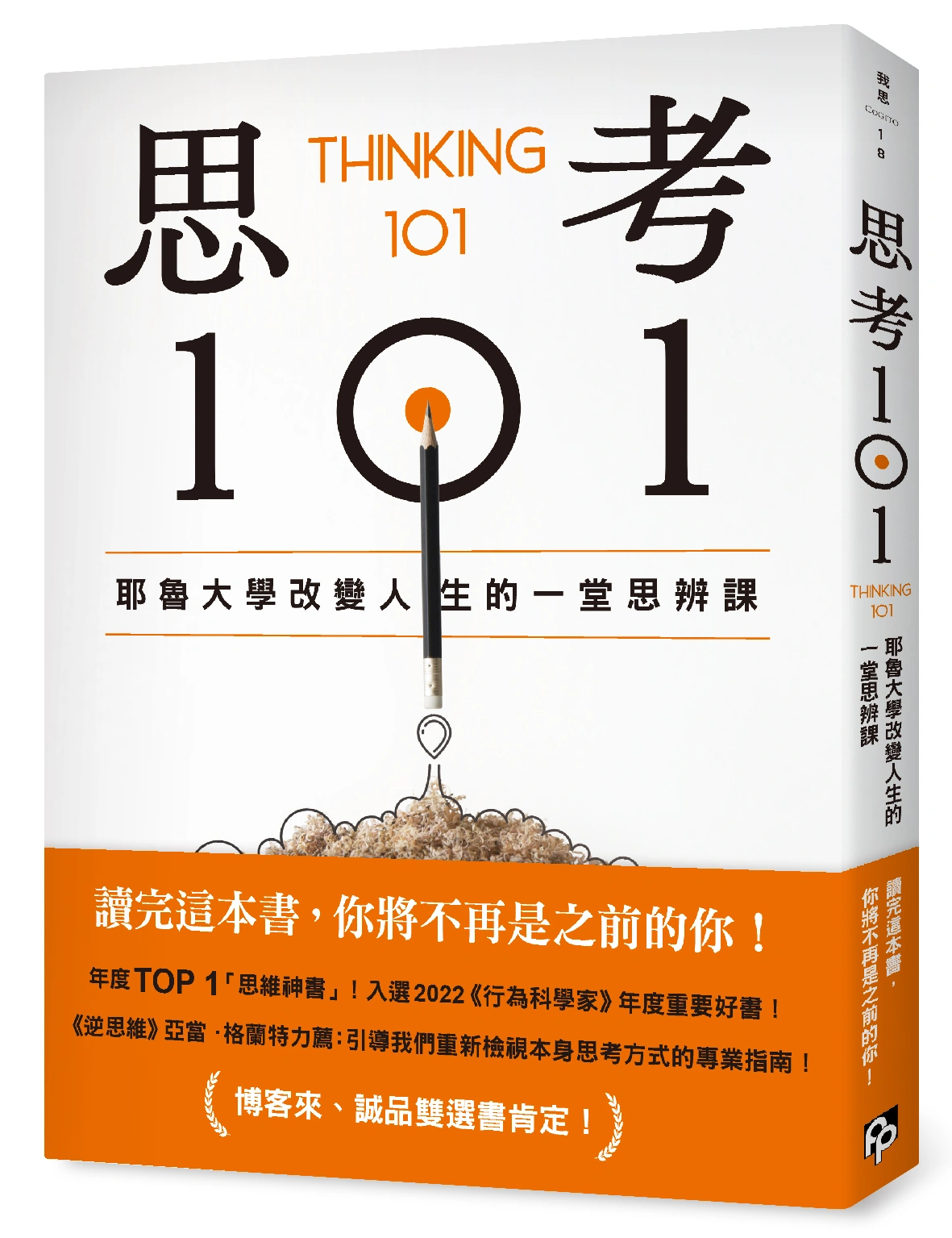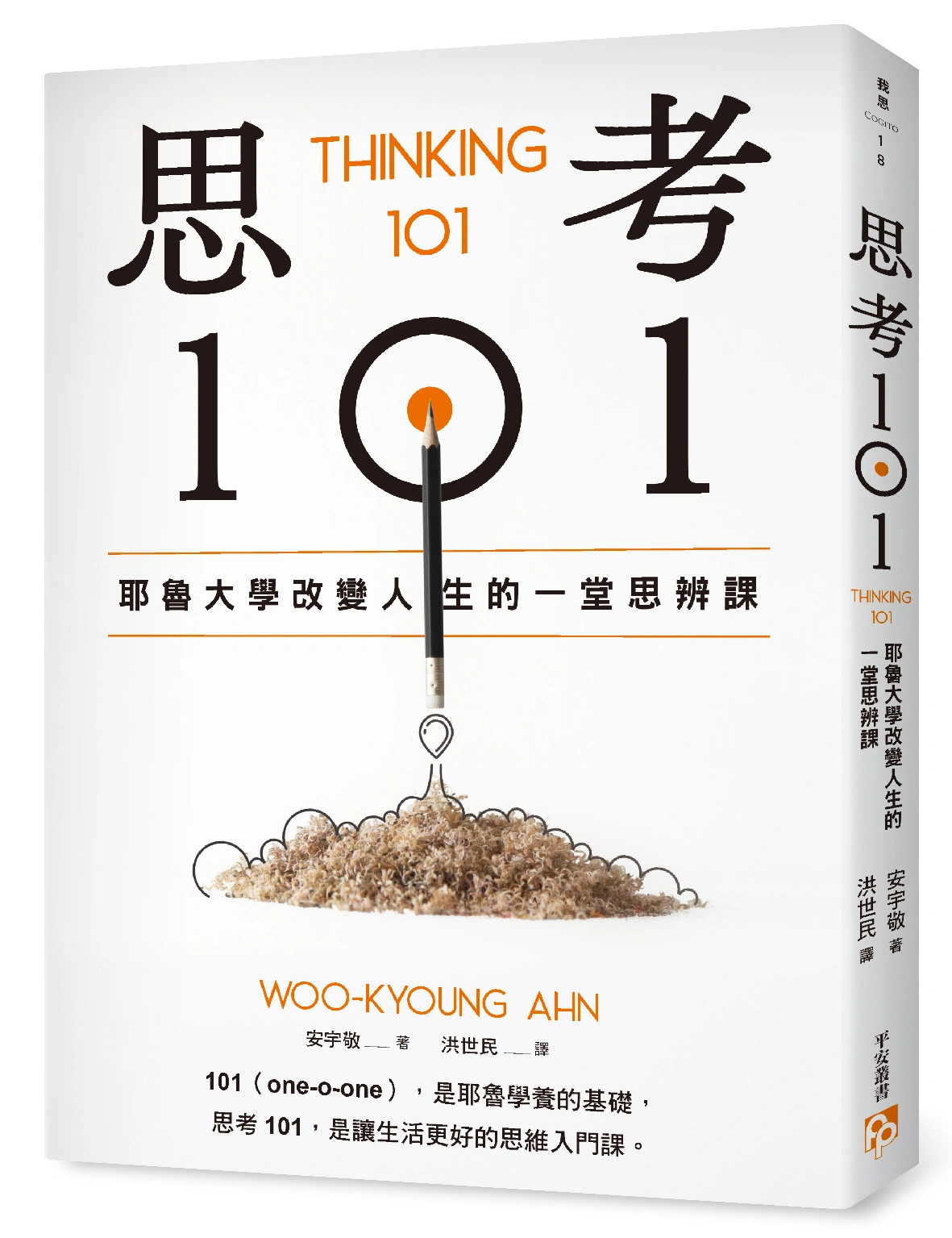內容試閱
序
當我在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念研究所、做認知心理學研究時,我們的實驗室團隊成員不時會去喝啤酒配墨西哥玉米片,那是請教指導教授事情的絕佳時機,特別是問一些不會在正式的個別會談上提起的事。其中一次聚會,我鼓起勇氣問他一個卡在我心裡好一陣子的問題:「你覺得認知心理學真的能讓世界變得更好嗎?」
我覺得我的問題問得有點莫名其妙;我已將一生投入這個研究領域,現在才問似乎有點晚了。但就算我在世界各地的認知科學會議上報告我的發現,並順利在受推崇的心理學期刊發表,我仍舊難以向我的高中好友解釋我的研究對現實生活的影響。那一天,我煞費苦心讀了一篇論文,作者的首要目的,似乎在展現他們有多聰明伶俐地處理一個現實世界不存在,又百轉千迴的問題,這使我終於鼓起勇氣,在啤酒幫助下發問。
我們的指導教授向來以含糊籠統出名。如果我問他:「下一次實驗我該做A還是B?」他若不是回答一個撲朔迷離的「好」,就是反問:「你覺得呢?」但這一次,我問他的是簡單的是非題,所以他選擇簡單的回答:「能。」接著我和我的實驗夥伴坐在那裡沉默了五分鐘,等他進一步闡述,但他卻沒有再開口。
在往後的三十多年裡,我試著透過研究那些我希望能在現實世界中應用的疑難雜症,來自己回答那個問題。我從二○○三年起在耶魯大學擔任心理學教授,而在該校研究期間,我檢視了幾個可能害我們迷路的偏誤──並發展出可直接應用於日常生活情境的矯正策略。
除了選擇研究的特定偏誤,我也探究一連串於現實世界發生,可能對我和我身邊的人,包括學生、家人、朋友造成困擾的「思考的難題」。我見過很多學生因為低估把某項作業留到以後才做的痛苦,拖拖拉拉不肯馬上做;我聽一個學生說她遭到一名醫師誤診,因為醫師只會問那些符合他既有假設的問題;我注意到有人把遇到的一切困境通通歸咎於自己,因此悶悶不樂,因為他們只看到事實的一面;而有些問題,其實是其他從不認為自己有錯的人所引起的。我親眼目睹幾對伴侶以為自己的溝通清楚無礙,但其實完全誤解對方的意思。
我也見到所謂「思考的難題」如何造成個人生活以外的麻煩。這些根本謬誤和偏見會引發林林總總的社會議題,包括政治兩極化、氣候變遷下的共謀關係、種族剖繪、警方濫射等……幾乎每一個源於刻板印象和偏見的問題都是因此而生。
我開了一門名為「思考」的課,告訴學生,心理學可以如何幫助他們認清和處理現實社會的問題,幫助他們對人生做出更好的決定。那應該相當切合現實需要,因為光是二○一九年,就有超過四百五十名學生選修。他們似乎都渴望心理學能帶給他們指引,因而口耳相傳。然後我發現一件奇妙的事:很多來校園參訪的學生家人跟我說,修我這門課的學生會打電話回家報告,他們正在學習怎麼處理人生的課題──甚至有人開始提供家人,包括父母自己的建議。也有同事告訴我,他們聽到學生在餐廳激烈辯論課堂上介紹的一些實驗的意涵。每當我和非心理學專業的朋友講到課堂上討論的議題時,他們會問我可以去哪裡學到更多。以上狀況全都顯示,大家真的想要也需要這種類型的工具,所以我決定寫一本書,讓其中一些課題更廣為人知。
我選了八個我覺得與我的學生和其他人(包括我自己!)每天切身相關的主題。每一章探討其中一個,而雖然我會在必要時提到分布在本書各處的內容,但這八章要用哪一種順序閱讀都可以。
我討論的固然是思考的謬誤和偏見,這本書卻不是在講人到底有什麼毛病,之所以會發生「思考的難題」,是因為我們的大腦是以非常特殊的方式建構的,大腦之所以如此建構往往有相當充分的理由。推論更是我們的認知高度演化後的副產品,讓人類這種物種能夠倖存到今天,且在世界欣欣向榮。因此,這些難題的解決之道未必那麼容易找到。事實上,不論要消除哪一種偏見,都是無比艱難的。
另外,如果我們想避免這些謬誤和偏見,光是加以認識和提醒自己別犯,是不夠的。就像失眠一樣;失眠一發生,你會很清楚問題出在哪裡──你睡不著。但叫失眠的人多睡一點,絕對不是解決失眠的方法。同樣地,這本書介紹的一些偏誤,你或許已經耳熟能詳,我們仍須提供比光說「別去做」更好的處方。所幸,有愈來愈多研究證實,我們確實有可行的策略來做出更好的推論。這些策略能幫助我們設想我們無法掌控的事,甚至告訴我們某些乍看頗具希望的解決方案,到頭來可能會怎麼招致反效果。
這本書以科學研究為基礎,主要資訊來自其他認知心理學家,但也有一些來自我自己進行的研究。我援用的許多研究都被視為經典,禁得起時間考驗;其他研究則呈現這個領域最新的成果。如同我在課堂上所做的,我會從各種不同生活層面,舉出形形色色的例子來闡明每一個論點。這麼做是有理由的,而你會明白為什麼。
所以,回到我問指導教授的問題:「認知心理學能讓世界變得更好嗎?」這麼多年來,我已經更堅定地相信,答案就是「能。」我的指導教授回答得非常貼切:能,絕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