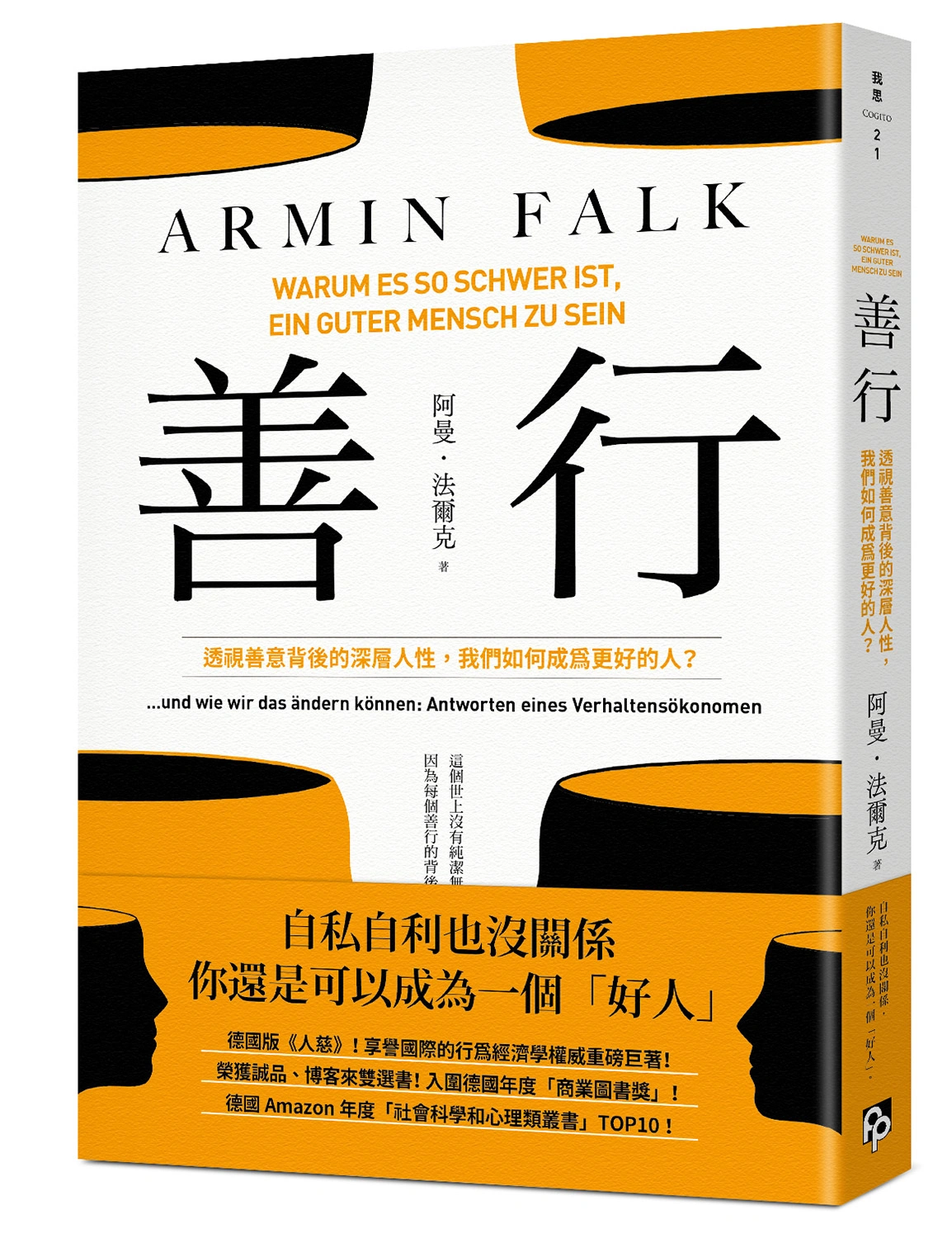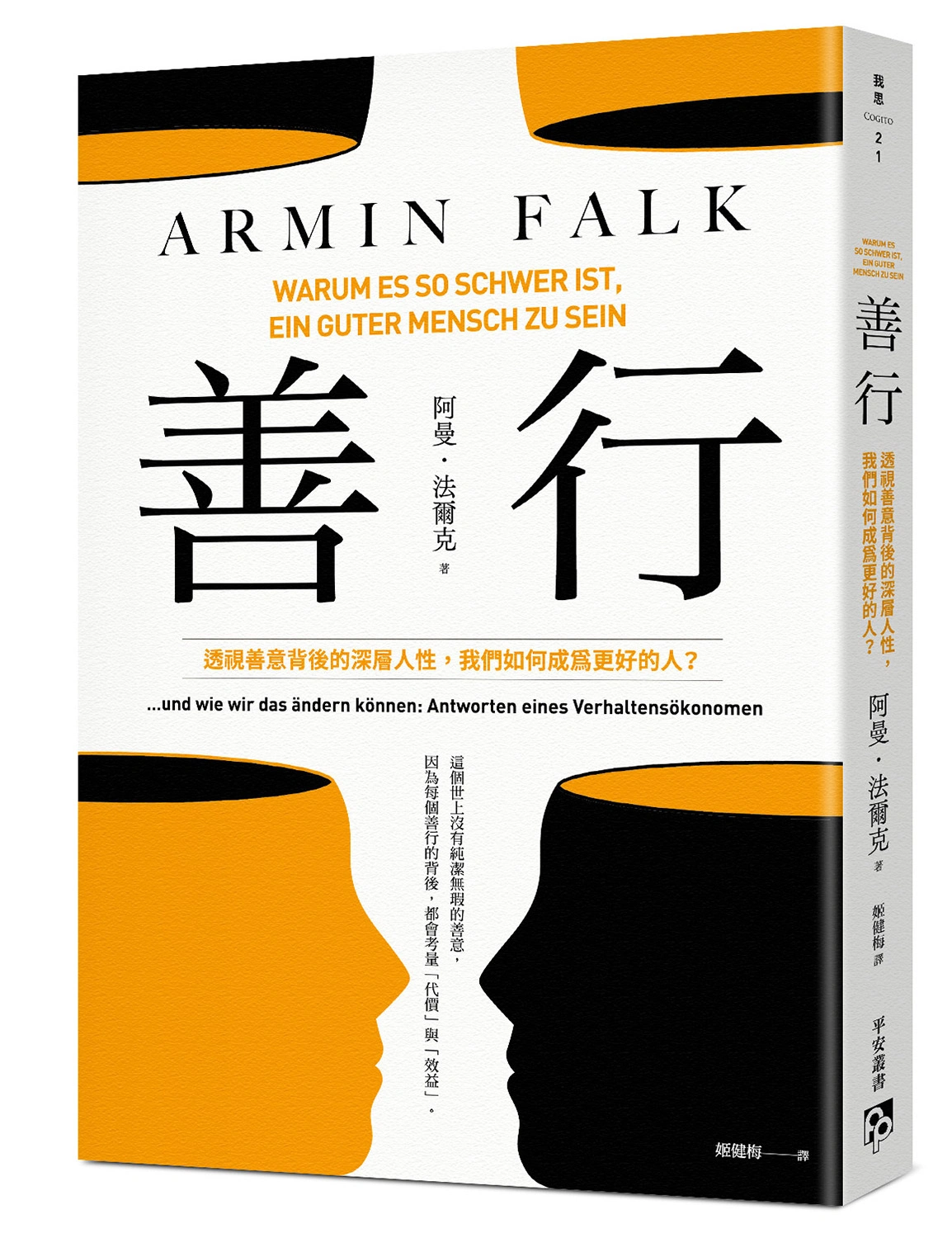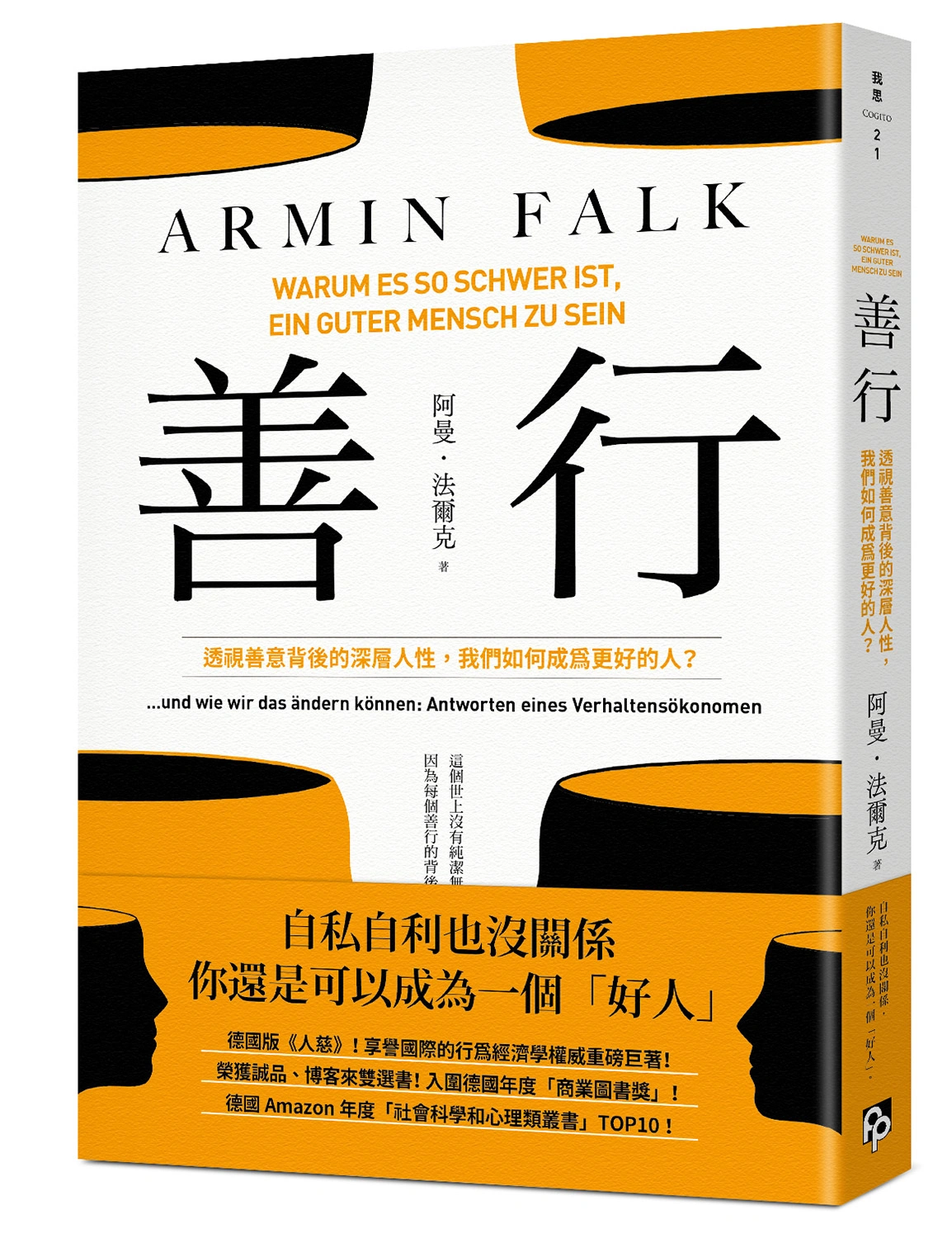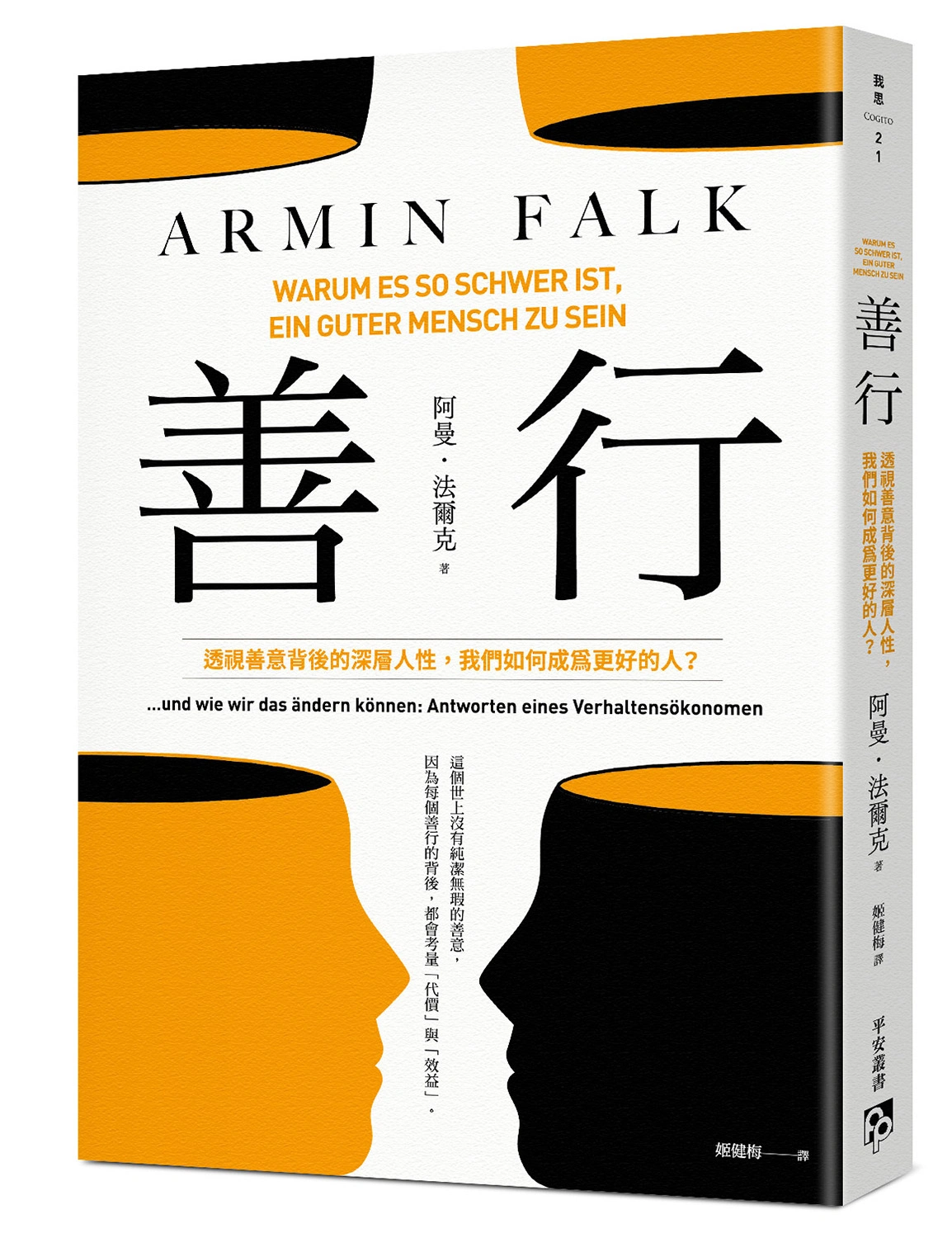內容試閱
道歉
想在自己和別人面前顯得無可指責,這個願望還在另一種情況下對此書的核心問題起了重要作用。這使我們猶豫著不願承認錯誤,不願意去向我們對不起的人道歉。「我做錯了,請原諒。」「我很抱歉。」這幾句話我們往往很難說出口,即使我們很清楚自己做了糟糕的事。為什麼會這樣呢?我思考了很久,尤其是因為一聲道歉能帶來這麼多好處─不只是對對方,而也是對我們自己。
道歉能創造真正的奇蹟,道歉能療癒被不當行為毀掉或威脅到的人際關係,能化解情緒緊張,有助於化解衝突,讓自己擺脫過去犯下的錯誤,克服羞慚和愧疚的感覺,而且道了歉,受到損害的一方才能夠原諒。這不僅對做錯事的人有好處,讓他能坦然面對自己的錯誤,更重要的是,道歉有助於讓受到損害的人擺脫受害者的角色,不再糾結於自己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之前所發生的事不再能定義受害者,讓他可以有機會重新開始。
道歉能夠解除情緒上的緊張,並且有助於重建由於不公正行為而可能受損的人際關係,這不僅在朋友和熟人圈裡能發揮作用,在經濟關係上亦然。我以前的博士生約翰尼斯.阿貝勒(Johannes Abeler)以購物網站eBay上的交易為例所做的一項研究就證明了這一點。為了這項研究,一家每月交易量大約一萬次的公司願意對顧客的負面評價作出不同的回應,研究的目的是想了解,不同的反應是否會影響顧客收回負評的意願。研究者選出了三種不同形式的回應:一封正式的道歉函,一個金錢上的小小補償(二.五歐元),和一個稍微大一點的金錢補償(五歐元)。在道歉函中,公司坦白承認犯了錯誤,對此感到遺憾,並且請求顧客原諒。在這三種回應中,該公司都表示希望顧客能收回負評。
在收到道歉函的顧客中,有45%收回了他們的負評,是收到金錢賠償(這至少也隱含了道歉的意味)的顧客的兩倍,也就是說:道歉的力量勝過了金錢。
既然道歉有這麼多好處,為什麼我們經常沒有勇氣去道歉呢?我再三思考這個問題,而我認為關鍵就在於自我形象和外在形象。這些話很難說出口:我犯了一個錯誤,為此感到後悔,並且請求原諒。道歉等於主動承認自己不是個好人,同時直接打擊了「我是個好人」這個幻覺。在某種程度上,主動摧毀正面的自我形象和前文中所描述的情況正好相反,亦即假裝沒看見、迴避和壓抑。這意味著徹底打破正面的自我感知和自我呈現,這是在承認自己的不完美,因此明顯違反了想要擁有一貫良好之自我形象的願望。
但微妙之處在於:正因為道歉給道歉者造成成本,道歉才有效果,並且在受害者身上達到了道歉的目的。因為我們的溝通只有在對溝通者造成成本時才值得信賴(這是個體經濟學的一個卓見)。這也是為什麼只有誠實、由衷、完整的道歉才能產生正面的效果。隨口說說的Sorry根本沒有用,而且效果正好相反,言不由衷的道歉只代表了一種虛假的認錯,只遮掩了不想為其不當行為負責的意圖,只會使情況變得更糟。在政治界經常可以聽到:「如果給你這種感覺,我很抱歉。」這種「道歉」把責任推在對方身上,推給了對方的反應。
例如,我們不能用「我們很遺憾,如果我們的發言引發了負面的感受」來為種族歧視的話語道歉,不管對方有什麼反應,種族歧視的話語就是種族歧視的話語,而我們必須為了這番話而道歉。道歉要有效果,前提永遠是承認錯誤、感到抱歉、請求原諒。這對自我形象而言是三次打擊,但這是唯一的辦法。
渴望得到讚賞也會使人犯下道德錯誤
人想要被喜愛,也想要受到自己和他人的尊重、稱讚和認可,想要得到認可有助於我們去行善,如同前文中所述,但是想要得到認可是否也可能產生相反的效果呢?有沒有可能,正好是我們對於正面自我形象的追求導致了在道德上可議的行為?
這個問題的答案取決於我們以何種方式贏得良好的自我形象,毫無疑問,道德上無可挑剔的行為很重要,但是自我形象能夠只縮限為道德上無可挑剔的行為嗎?我們的形象是否就只取決於我們的行為與道德觀相符?還是說,還有其他的動機也起了作用,例如想要在自己的工作上出類拔萃,不管是身為科學家、記者、政治人物還是經理人?我們不也想要在自己投身的領域被視為真正的專家嗎?不也會因為自認為完成了某件偉大而值得佩服的事而沾沾自喜嗎?當然。但是,如果想要把工作做好這個願望和道德有所牴觸的話該怎麼辦?如果雄心壯志和虛榮心誘使我們去做道德上可議之事?
也許你曾經思考過,在內心最深處驅動科學家的是什麼?他們夢想著什麼?他們殷切希望的是什麼?他們的願望往往是想要做出偉大的發現:一個能夠改變世界的偉大主意,不管是戰勝一種疾病,促進和平和繁榮,深入了解複雜的社會法則或物理法則,或單純只是使人類更了解自己。
想像這樣一位研究者:年輕、受過良好訓練、充滿雄心壯志。美國的格羅夫斯中將(Leslie R. Groves)在一九四二年向這位研究者提出了一個他無法拒絕的提議:領導有史以來最龐大的聯合研究計畫,坐擁人類史上最高額的研究經費,聚集了最頂尖的物理學家、數學家、化學家和工程師,為了創造出前所未聞的東西:原子彈。那想必很誘人,能向自己和世人證明人類的才智。因此,羅伯特.奧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同意了,後來和數百名熱情的傑出研究者共同完成了一件技術上的傑作(他們稱之為「小玩意」〔Gadget〕)。之後的故事就是歷史了,在「艾諾拉.蓋」(Enola Gay)號轟炸機按下發射鈕之後,名為「小男孩」(little boy)的原子彈造成了數十萬名孩童和父母被殺死或受到輻射,那是人造的地獄。
在原子彈被投擲到廣島和長崎之後大約四十年,羅伯特.利夫頓(Robert Lifton)和葛瑞格.米歇爾(Greg Mitchell)訪問了當年參與「曼哈頓計畫」的工作人員,發現有許多人罹患了心理疾病。那些研究人員尤其認為在長崎投擲鈽彈是不正當的,引發了道德衝突,導致了憂鬱、內疚、恐怖和震驚。當他們被問到參與研發這個威力巨大的炸彈的動機,他們表示是因為他們想要創造出某種偉大的東西,能夠參與有史以來最重大的發明,這吸引了他們參與這項工作。例如,舉世聞名的物理學家理察.費曼(Richard Feynman)就曾針對「曼哈頓計畫」表示:「……我們懷著好的理由開始,然後就努力工作,以達成某件偉大的事,那是一種喜悅,是一種熱情。而你就不再去思考了,就這麼簡單。」澳洲物理學家奧利芬特(Sir Mark Oliphant)也說過類似的話。他說,在戰爭中他從研究人員身上了解到:「如果研究工作令一個人感到興奮,那麼他就會去研究所有的東西」,他又說:「讓醫生去研究化學武器,讓物理學家去研究核子武器」一點也不難。而奧本海默自己是怎麼說的呢?「如果你面前有個『在技術上誘人』(technically sweet)的東西,你就會動手去做。」
舉這個例子的重點並不在於去詆毀「曼哈頓計畫」的工作人員不道德,這個複雜問題的政治評價有許多層次,而且已有許多文獻記載,重點在於指出,想要製造出良好的自我形象,不同的嘗試之間有著潛在的衝突。一方面想要擁有正面的道德認同,另一方面想要做「好」自己的工作:想要大放異彩,想要出類拔萃、既聰明又成功。英國哲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27就已經觀察到:認為自己「有能力」、「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能夠帶給我們喜悅。在他列出的十四種快樂當中,他稱之為「技藝的快樂」(Pleasure of Skill),指的是確知自己具有能力達成某件事。經濟學家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28將之簡稱為「求勝動機」(mastery motive)。就其本身而言,希望自己合乎道德和想要出類拔萃這兩個動機都是人類行為的重要驅動力,可是,如果這兩種動機起了衝突,這會對道德產生什麼影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