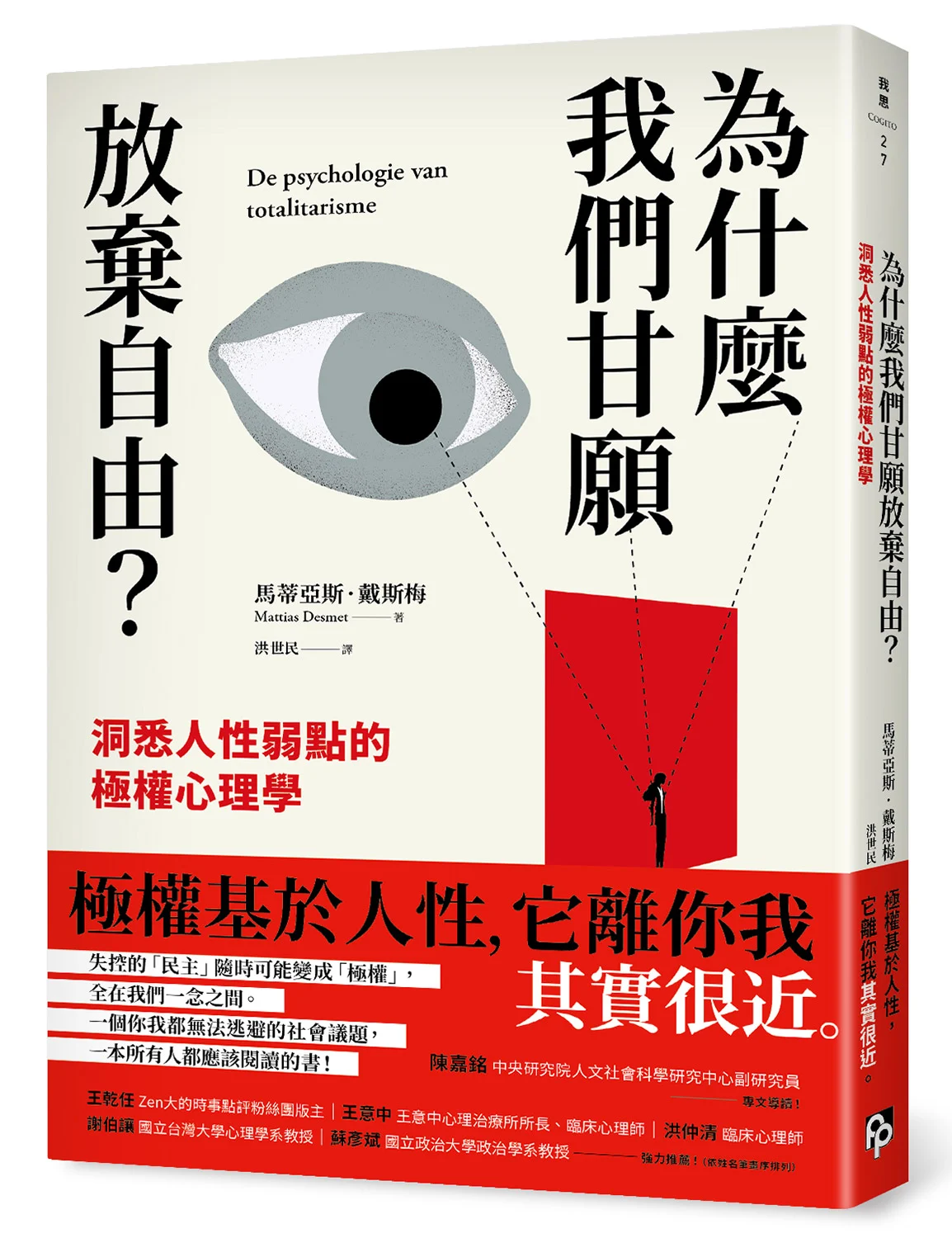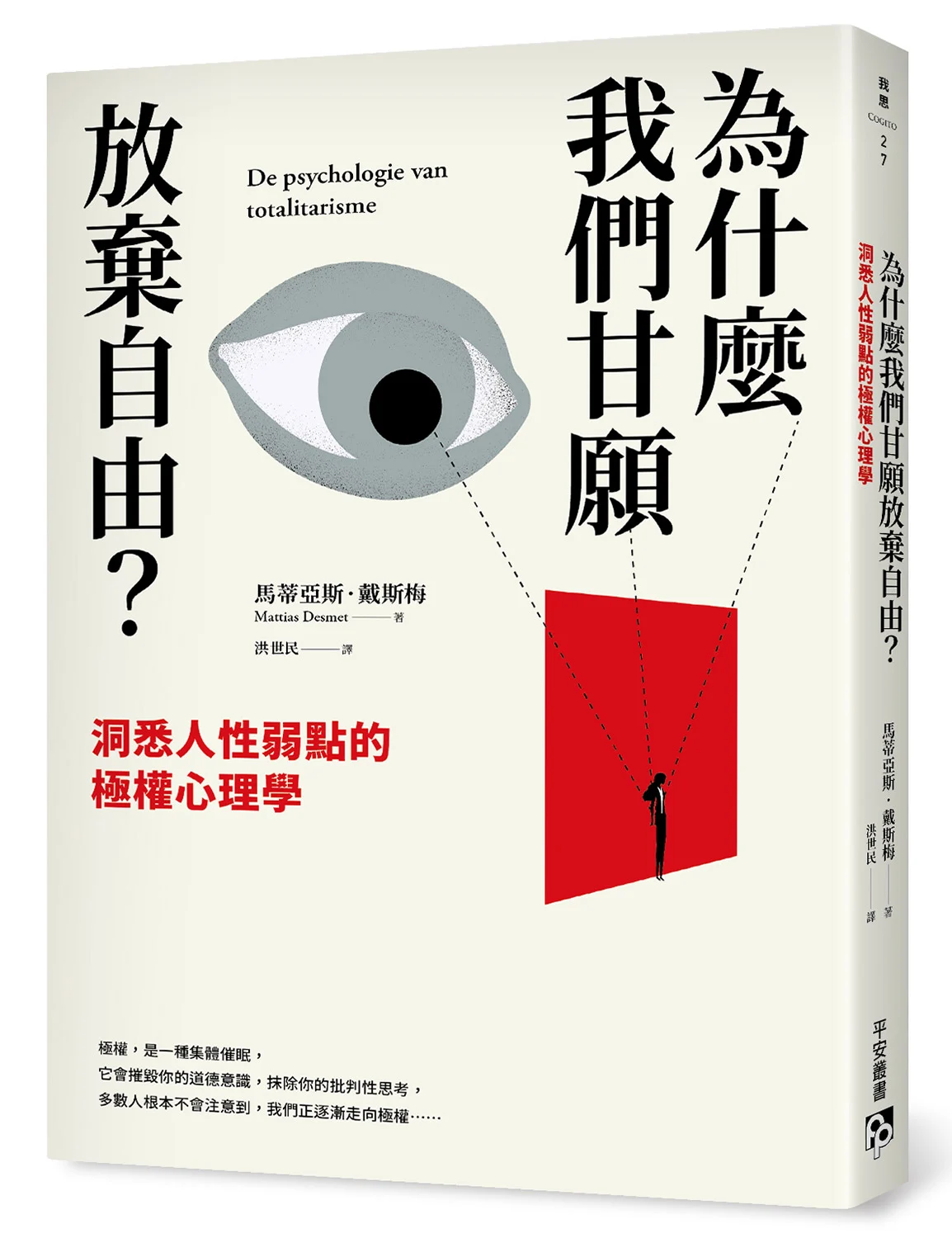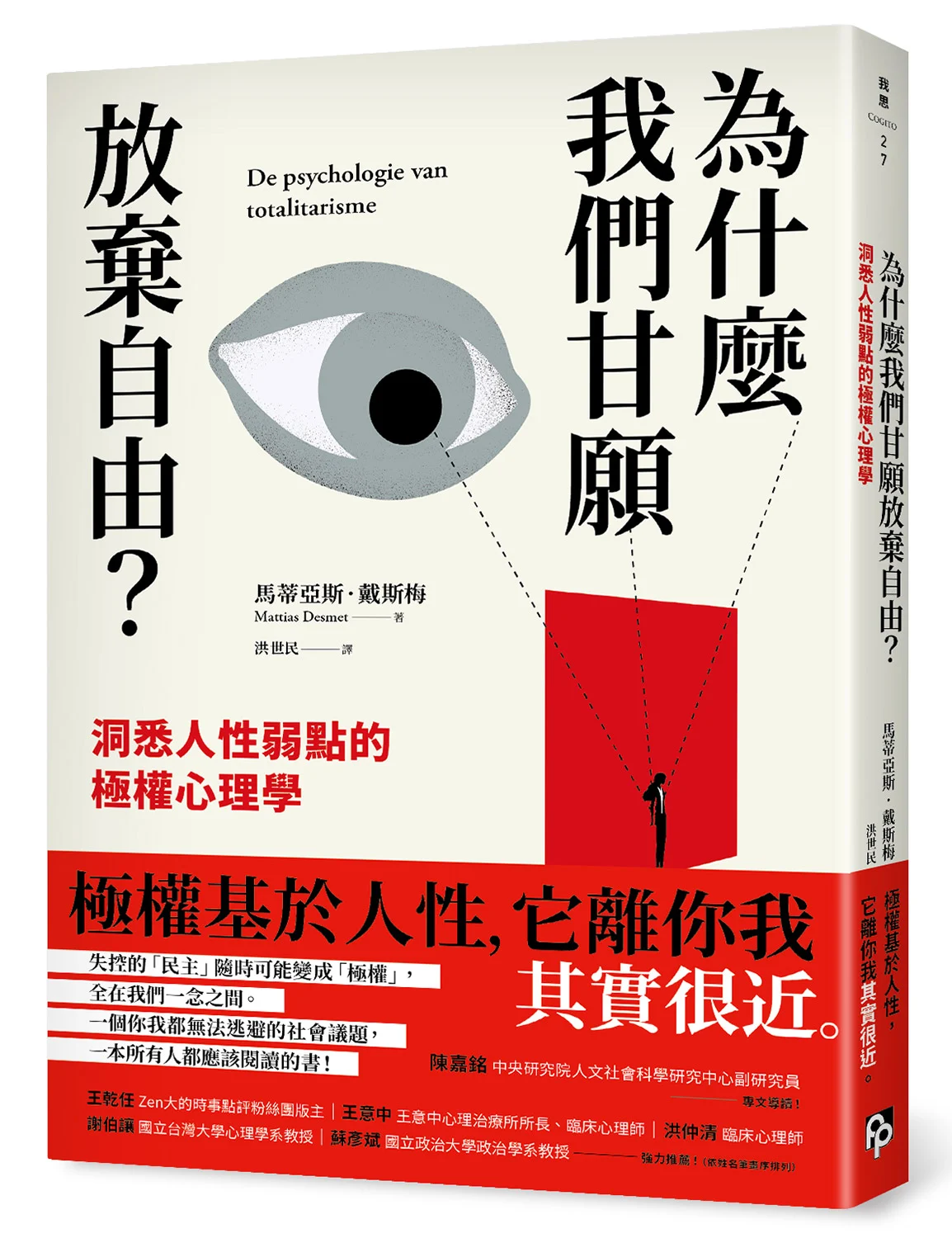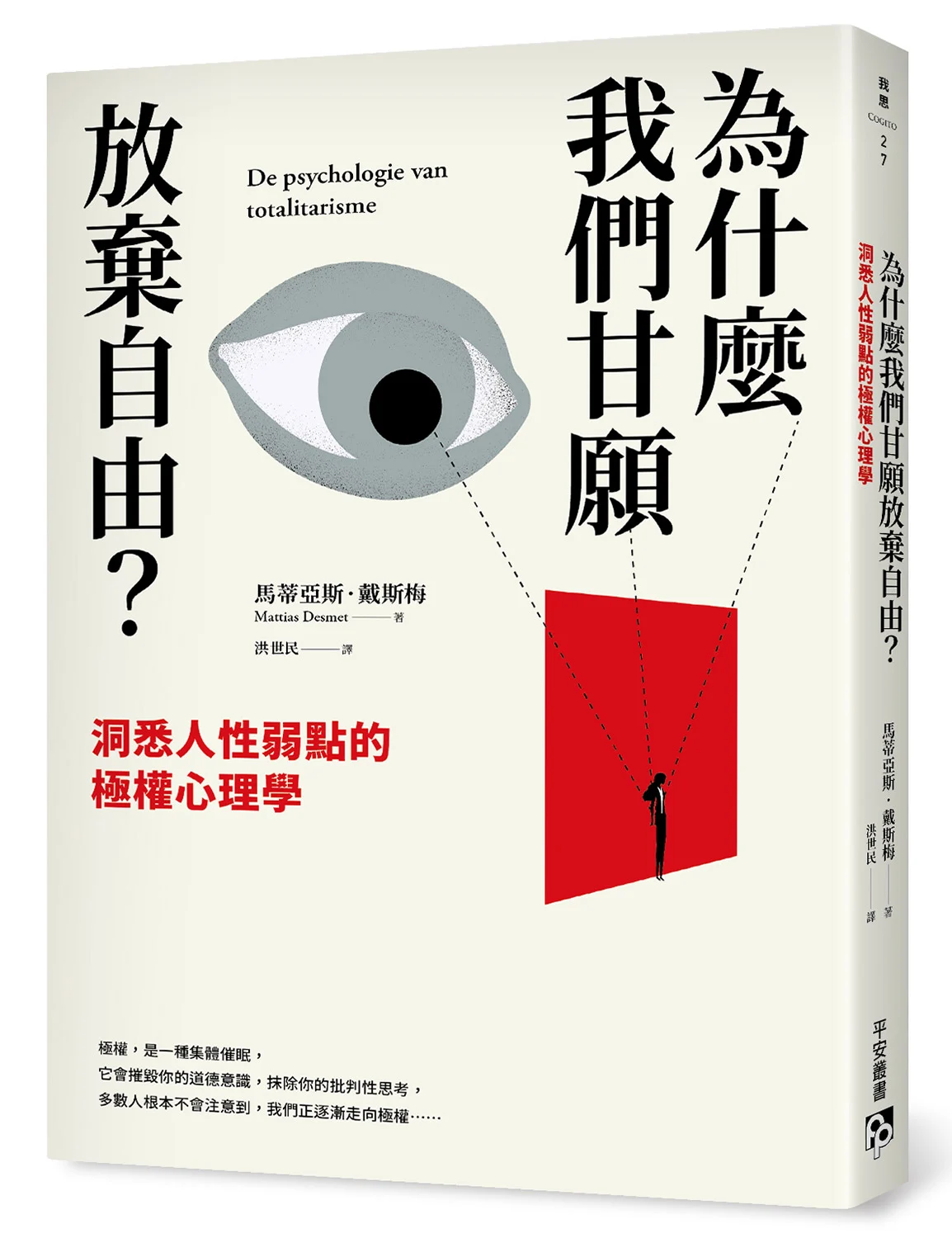內容試閱
引言
我要寫一本探討極權主義的書──這個想法在二○一七年十一月四日第一次浮現。或者說是那天第一次出現在我的科學日記本裡:我在那本筆記本草草記下所有可能會對往後文章或寫書有用的東西。
當時,我人在法國阿登、一對朋友擁有的一間小木屋作客。一大清早,當旭日照亮周圍的樹林,我會打開日記,寫下前一晚冒出來的念頭。也許是自然環境的平靜安詳讓我比平常更敏感,但在那個星期一早晨,我突然極其明顯、強烈地感覺到,一種新的極權主義已經播下種子,使社會結構變得僵硬。
早在二○一七年,這個現象就不容否認了:政府對私生活的掌控正急遽增強。我們的隱私權正受到侵蝕(特別是九一一之後)、非主流的聲音受到愈來愈嚴格的審查和壓抑(特別是氣候辯論的脈絡)、維安部隊發動侵入行動的次數大幅增加等等。
而這些事態發展的背後不只有政府而已。「覺醒」(woke)文化的迅速崛起,和日益蓬勃的氣候運動,都醞釀出要求建立新型態、超嚴格政府的呼聲──且呼聲來自民眾本身。恐怖分子、氣候變遷、「直男」、乃至後來的病毒,都被認為太過危險、無法以舊有方式對付了。用科技對人口進行「跟蹤及追蹤」已愈來愈為民眾接受,甚至被認為勢在必行。
德國猶太裔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洞悉的反烏托邦世界已隱約出現在社會的地平線:新極權主義已然崛起,而這種極權不再以諸如史達林(Joseph Stalin)或希特勒(Adolf Hitler)等浮誇的「群眾領袖」為首,而是由愚鈍的政府官員和技術官僚領軍。
那個十一月早上,我草擬了一本書的藍圖。我打算在書中探討極權主義的心理根源。當時我想知道:二十世紀前半,極權主義為何會化為一種國家形式崛起?還有:極權國家和以往的古典獨裁政府有什麼差別?而我認識到,這個差異的本質在心理學範疇內。
獨裁政府是以一種原始心理機制為基礎,也就是運用獨裁政體的嚴酷潛能,在人民之間營造恐懼的氛圍。反觀極權主義則根源於「集體重塑」(mass formation)這種隱伏的心理過程。唯有徹底分析這個過程,我們才能了解「極權化」的人口會有哪些驚人的行為,包括個人過分願意為了集體(即群眾)的團結犧牲個人利益、極度不容忍不一樣的聲音,以及明顯容易受到偽科學的思想灌輸和政治宣傳影響。
集體重塑基本上是一種群體催眠,會破壞個人的道德自我意識,剝奪個人批判性思考的能力。這個過程本質是隱伏的,民眾會在毫無戒心下淪入魔掌。套用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 的說法:多數人甚至不會注意到政府正轉向極權。我們通常把極權主義和勞改營、集中營和滅絕營連在一起,但這些只是一個漫長過程令人眼花撩亂的最後階段罷了。
在我第一次寫下那些筆記後,有愈來愈多和極權主義有關的東西出現在我的日記本裡。它們紡成愈來愈長的線,有條不紊地連結我關注的其他學術領域。例如極權主義的心理問題涉及科學世界在二○○五年爆發的一場危機,而我的博士論文就廣泛探究了這個主題。當年,草率、謬誤、偏頗的結論,乃至公然造假,在科學研究方面變得如此普遍,使比例高得驚人的研究報告,做出錯得離譜的結論──某些領域甚至高達85%。其中,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最引人入勝的莫過於:大多數研究員完全相信他們的研究或多或少正確。不知怎地,他們就是不明白,他們的研究不但沒有使他們更接近事實,還創造出虛構的新現實。
這當然是個嚴重的問題,尤其當代社會可是將科學信仰列為理解世界最可靠的方式呢。另外,前述問題也與極權主義的現象直接相關。事實上,這正是漢娜.鄂蘭揭露的:極權主義的暗流,是由盲目相信一種統計數值的「科幻」、「極度輕蔑事實」的信仰構成:「極權統治的理想臣民不是忠貞的納粹或忠貞的共產黨人,而是心中不再有事實與虛構之分,不再有真偽之別的民眾。」
科學研究品質不良暴露出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我們的科學世界觀有重大缺陷,而這些缺陷的惡果,遠遠延伸到學術研究領域以外。這些缺陷也是深刻集體不安的起因,而最近數十年,集體不安在我們的社會愈來愈顯而易見。今天,民眾對未來的看法已沾染悲觀、缺乏遠見,且一日勝過一日。就算文明沒有被升高的海平面沖走,也一定會被難民橫掃一空。委婉地說,社會的「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啟蒙的故事,已不再走向昔日的樂觀進取。大多數人口已受困幾近完成的社會孤立之中;我們看到因精神受苦而缺勤缺課的人顯著增加;精神藥物的用量迭創新高;宛如流行病的倦怠癱瘓了公司行號與政府機構。
二○一九年,這種困境在我自己的專業環境更是昭然若揭。我見到身邊好多同事因心理問題離開工作,因為病情使他們連基本日常運作都無法進行。例如那一年,我需要有人簽署某份合約,才能啟動一項研究計畫,結果花了將近九個月才拿到簽名。負責審核和批准合約的大學部門面臨嚴重缺勤問題:永遠有人因心理疾患請病假,結果合約就是無法敲定。那段期間,所有社會壓力指標都急遽上升。熟悉系統理論的人都明白這句話的涵義:系統正走向臨界點。它已來到自我重整、尋求新平衡的邊緣。
二○一九年十二月底,在前面提過的同一間阿登小屋裡,我斗膽向一群朋友提出一個小小的預言:近期某一天,我們一覺醒來,就會置身不同的社會。這個預感甚至慫恿我採取行動。幾天後,我去銀行還清了我的房屋貸款。這是否為明智之舉,取決於你的觀點。或許從純經濟或稅務觀點來看並不明智,但我不在意那些。於我最重要的是,我想要奪回我的自主權;我不想有欠債和與金融系統通同一氣的感覺。在我看來,社會之所以將走入那條死胡同,金融系統也扮演重要角色。銀行經理聽我說了故事;他甚至認同我的看法。但他堅持要知道,我為什麼如此毅然決然。我們聊了一個半小時,仍不足以填補他的問題裡的空洞。最後,眼看已經超過打烊時間很久,我便離開,留下他繼續納悶,而他的分行,不久後將永遠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