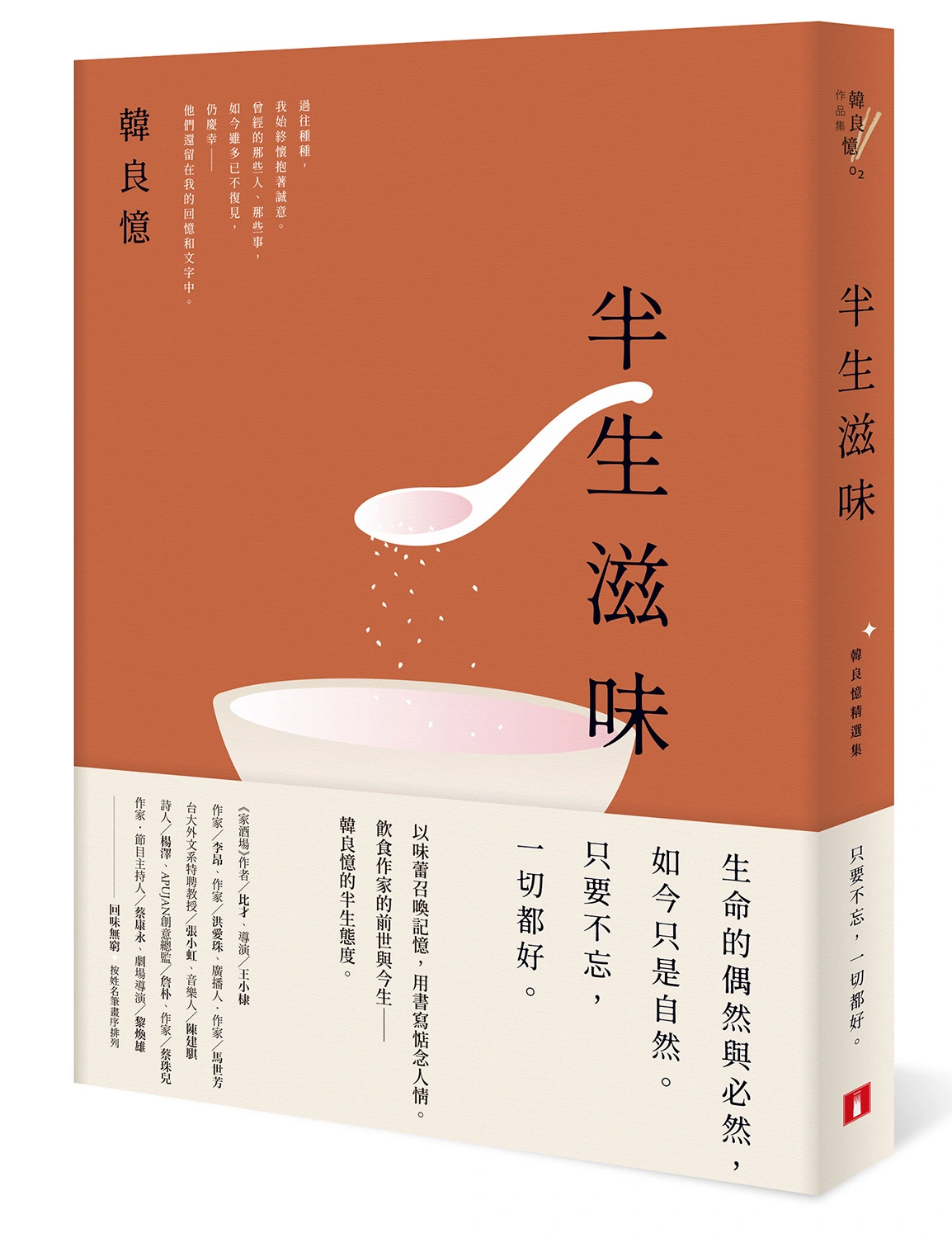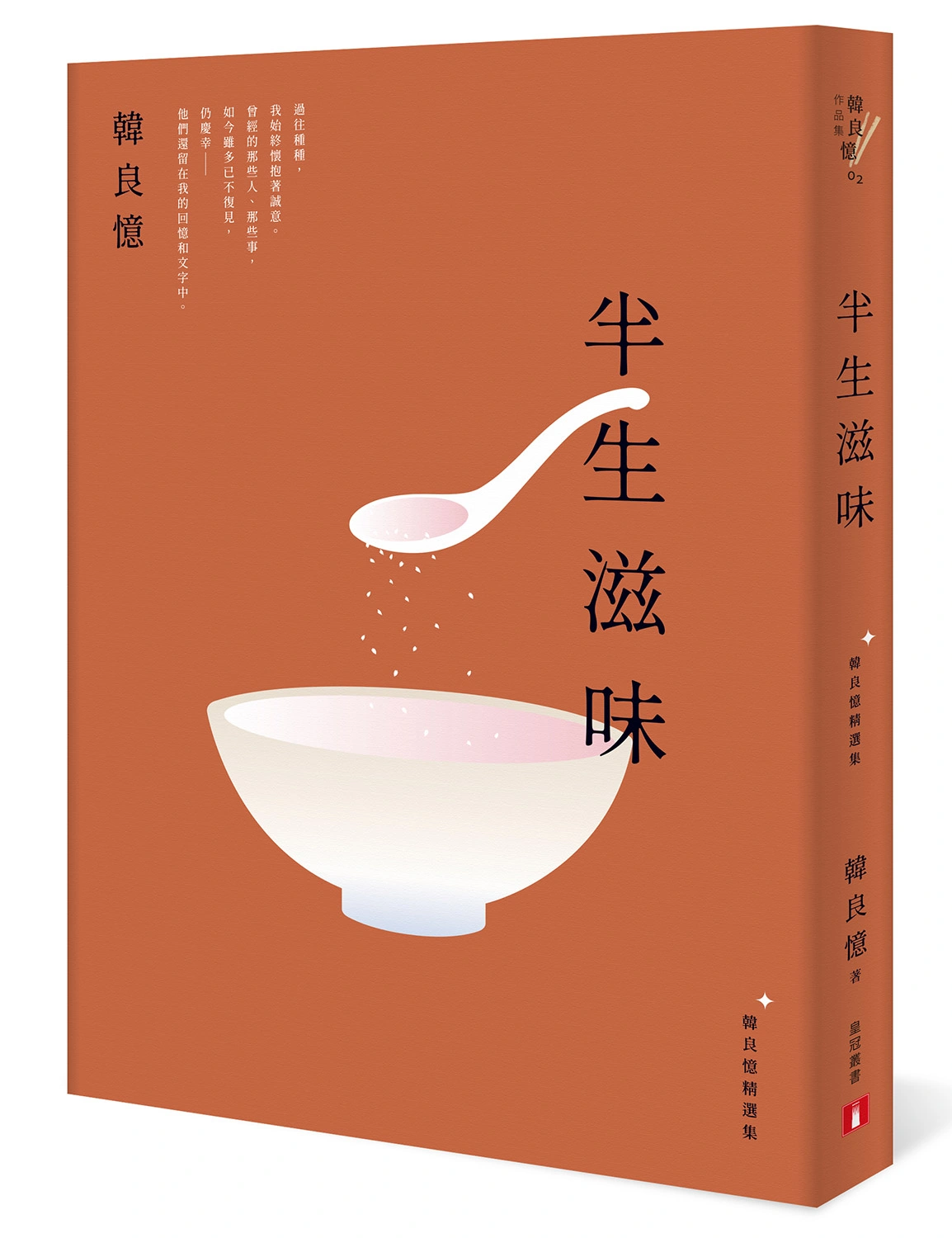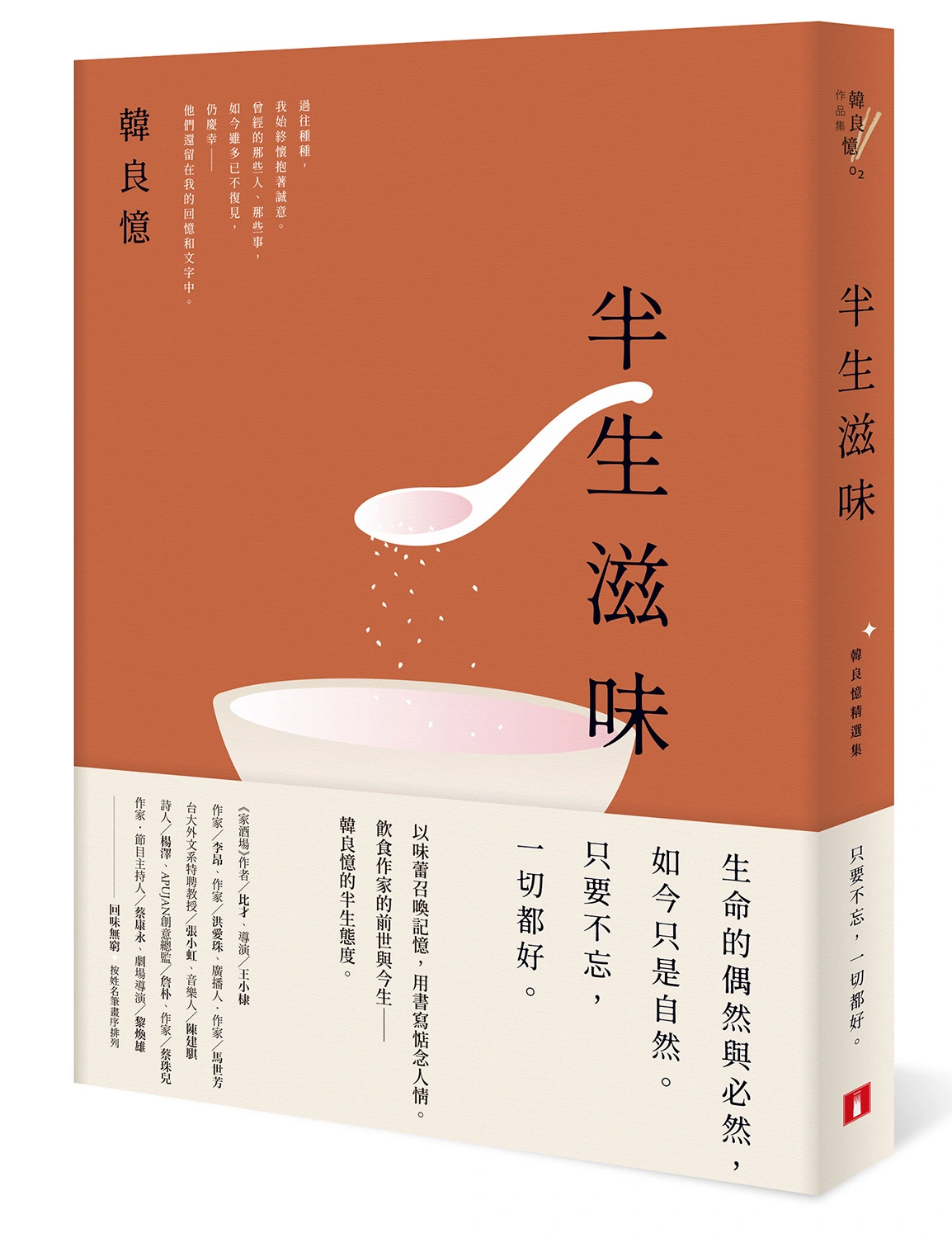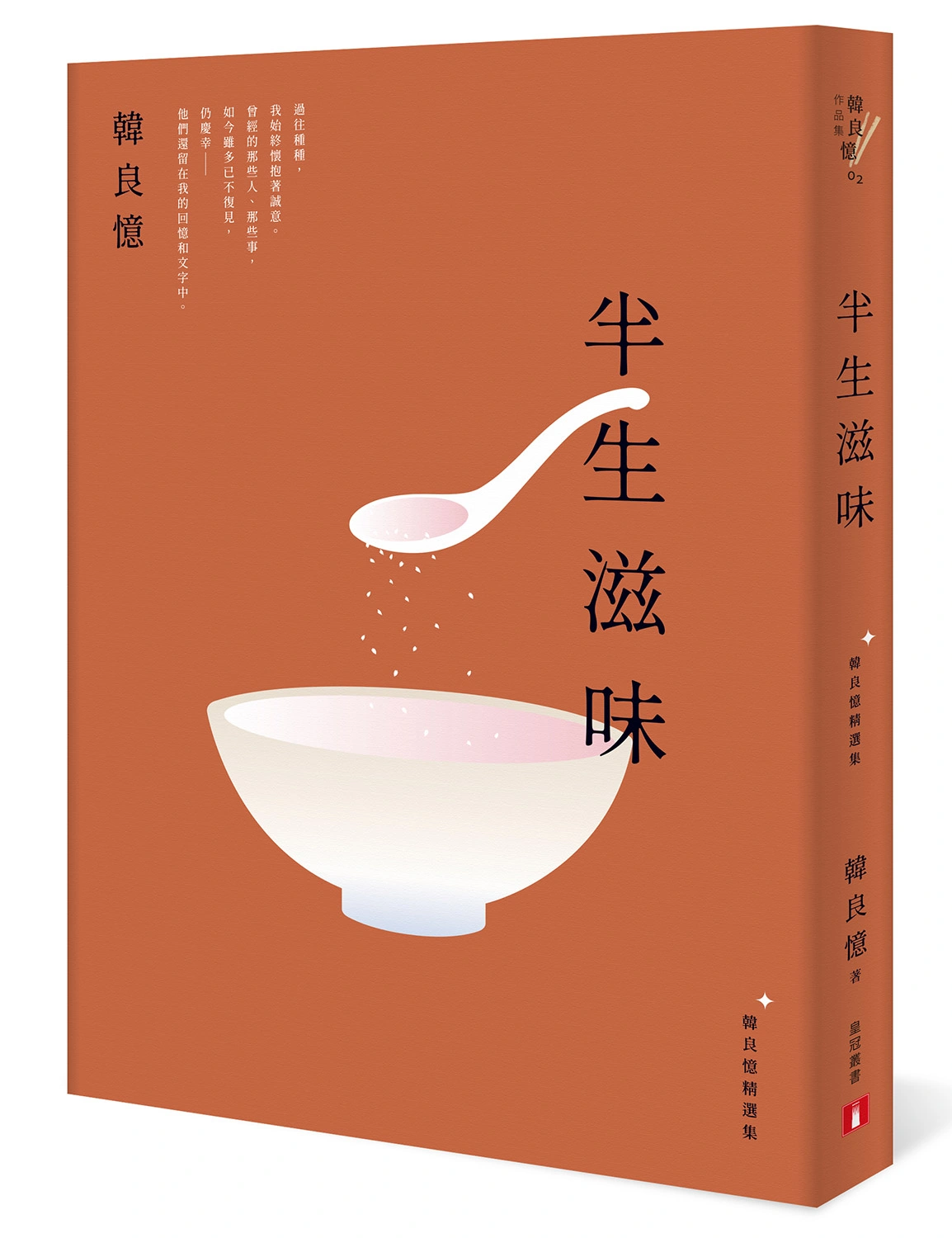內容試閱
所謂飲食作家的前世
一九九二年秋天一個有風的傍晚,有個失意的人半夢半醒地躺在離地面約二十公分的床墊上,一隻小老鼠旁若無人地爬上她散落在枕上的髮絲,人鼠之間的距離不到兩公分,此人倏地彈起,尖叫出聲,聲音之淒厲,把老鼠也嚇得吱吱叫著往牆邊一竄,轉瞬不見蹤影。人鼠雙方在幾近魂飛魄散之餘,誰也沒料到,就在那一剎那,這個人的人生從此轉了彎,一兩年後,她竟然成了所謂的作家──儘管在那之前,她尚需歷經一段類似狗仔隊的生涯。
而那個人,當然就是我。
還記得當時我一個箭步衝到浴室,狠命搓洗我那一頭被鼠爪沾污的及腰長髮,邊洗邊認真考慮要不要乾脆找家髮廊把頭髮剪掉算了。在用了快半罐洗髮精後,我頭上包著浴巾,坐在小客廳裡,終於下定決心,剪髮非解決困境之道,釜底抽薪之計是,搬家。
就在那鼠輩闖進臥室的幾個月以前,我和大學時代開始交往的男友因第三者的介入而分手。他把私人物品通通搬走後,我一方面耽溺在自艾自憐當中,一方面也一直在考慮著要不要搬離租處,屋裡有太多感傷的回憶了。
然而我從小便是個意志不堅、欠缺行動力的「豎仔」,始終拿不定主意,就這樣猶豫不決,一天拖過一天,直到那一晚,那隻鬼使神差的老鼠當頭棒喝,猛然嚇醒了我:再不割除惰性,再這樣渾渾噩噩過日子,我就完蛋了。正好親戚有間小公寓空著,看我一副可憐模樣,便宜租給我,過了數日,我搬進台北東區邊緣的大樓住宅。
新家並不大,家具設施卻齊全,尤其是開放式廚房完全可用「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來形容,流理檯、瓦斯爐、冰箱這些基本設備就不必說了,甚至連一般家庭沒有的烤箱也有,還是那種安在爐台下的歐美式大烤箱。不過,我因為情傷仍未平復,無心下廚,小廚房就被我晾在那兒,充其量拿來做做簡單的早餐或下碗麵,直到有天夜裡,我輾轉反側到自己都受不了,索性起床泡茶吃點心,偏偏餅乾受潮,沒法吃,而我橫豎睡不著,就參考食譜書,利用手邊現成的材料,烤出了一大盤甜餅。
這一烤,烤出了興趣,只因為烹飪是多麼令人驚喜的一件事,你只要有一點麵粉、油、糖和兩顆雞蛋,按部就班地操作,就可以像施展魔法般變出香噴噴的餅乾。烹飪又是多麼叫人安心的一件事,一條魚永遠是一條魚,不論紅燒、清蒸或乾煎,它絕對不會變成炒青菜或麻婆豆腐,我這個烹魚的人唯一能做的,就是用心、專心燒好這一盤魚,而在這洗切炒煮的過程中,我心底種種的糾結似也慢慢地打開了,那或是烹飪這件事對我最好的回報;曾經惶恐又失意的我,總算在廚房裡找到我的「小確幸」。我從此樂在下廚,也在無心插柳的情況下,為後來的食物書寫奠定了基礎。
精神既已振作,我決定為改變人生跨出下一步。說來也巧,任職的《聯合晚報》當時恰好有個採訪記者缺,我提出申請,就這樣從內勤的編譯,搖身一變為成天得跑來跑去的影劇記者。由於專長是英語,又愛聽音樂,愛看電影,遂主跑外語音樂、外語電影線,兼及表演藝術。
算我運氣好,跑線不久就碰到大新聞,麥可.傑克森將在一九九三年九月來台演出,那時這位「流行樂之王」疑似戀童的新聞尚未爆發,聲勢如日中天,他來台肯定是各報互相較勁的大事。主管一聲令下,「天王」人還沒來台北,我就一連寫了六篇連載稿,概述其人截至當時為止的星海生涯。前不久麥可猝逝,我那六篇稿子被編輯從檔案中翻出,登上電子報,我一看簡直要臉紅,哪裡是「本報記者韓良憶特稿」,根本就是英翻中資料整理。
過了三個月左右,天王來了,他的好友「玉婆」伊麗莎白.泰勒也帶著當時的丈夫同行。各報紛紛派員進駐他們下榻的五星旅館,其中包括《聯晚》,只不過「大報」都是好幾位記者團體作戰,晚報人力有限,就我這個菜鳥記者作先鋒。我拎著幾件換洗衣服住進了豪華大飯店,開始打起生平第一場真正的新聞戰。然而因為人單力薄,迫不得已只能另闢蹊徑,專去別的記者懶得去或判斷不必去的地方打探消息。
有一天傍晚,大夥全擠在飯店大門口、車道出口等候天王出飯店,我想他既要出門總得搭車,便一個人逛到地下樓停車場,那兒倒沒什麼人,只有同報系一位支援的記者、零星數位歌迷和飯店員工。我剛站定,還在東張西望時,電梯門開了,戴著墨鏡、一身軍服式標準打扮的天王走出來,視線似乎正朝我投來,我情急之下,開口便用英語蠢呆地說:「願上帝保佑你,傑克森先生。」他轉過頭來看著五、六呎以外的我,輕聲地說:「哦,謝謝你。」
「歡迎你來台北,你覺得這裡還好嗎?」我趕緊補上一句。
天王露出淺淺的微笑,「我很喜歡台北(I love it here, Taipei)。」(多麼制式的回答!)
他話才說出口,人就被保鑣簇擁著坐上了車。
短短幾句對話被我寫成新聞,成了第二天晚報的小「獨家」,文中卻未提到我從頭到尾都一副路人模樣,根本未對他表明我的記者身分,而今回頭一瞧,如此行徑和今日的狗仔隊似也相去不遠。
像狗仔也好,還算不上狗仔也罷,總之我在報社站穩腳步,煞有介事地當起影劇記者。彼時中國大陸市場尚未崛起,台灣消費能力高,對國際娛樂企業而言算得上亞洲重要的市場,我因而在短短不到四年的記者生涯中,有機會在海內外近距離接觸、專訪過不少外國大牌演藝人員,印象較深的有日本的動畫大師宮崎駿、英國歌手史汀和影星艾瑪.湯普森、美國的R.E.M.合唱團、爵士樂手溫頓.馬沙利斯、導演奧立佛.史東,還有丹佐.華盛頓、華倫.比堤、基努.李維等大牌影星,以及後來當上加州州長的阿諾.史瓦辛格等,真是族繁不及備載。
而同我「距離」最近的,還是麥可.傑克森,那距離甚且是零。
一九九六年十月,傑克森二度來台演唱,儘管當時他已備受醜聞困擾,但台灣歌迷依然熱愛這位天王,演唱會又是大轟動,這一回更南下高雄演出,台北的影劇記者緊追不捨,隨之前進南台灣,這一回還多了不少電子媒體,因為就在天王兩次來台間,台灣有線電視漸成氣候,成立了娛樂綜藝頻道,出現像《娛樂新聞》這樣的節目。
到了高雄後某一天,唱片公司透露天王下午可能到某賣場購物,眾家平面和電子媒體記者聞風紛紛前往,進入賣場就戰鬥位置。我呢,沒事人一樣,蹓躂到賣場後方的個人清潔用品區,磨磨蹭蹭,打算買罐洗髮精,南下前打包行李時忘了帶,而高雄好熱,晚上採訪完不洗個頭怎麼行?這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哇!
每一牌的洗髮精我都拿起來端詳檢查一番再放下,好不容易挑中一罐,才施施然走向收銀台。咦,怎麼整個賣場靜悄悄,方才鬧哄哄各就各位的記者那會兒全在外頭隔著玻璃窗向內張望。我往大門口一瞧,走進來的不正是戴著帽子和口罩的麥可.傑克森嘛,他的後方三呎處有位高大的光頭保鑣,亦步亦趨,四下打量。我頓時明白,這裡清過場,記者全被請出門外,僅餘我這個手拎著洗髮精的漏網之魚。
保鑣守在近門處,繼續警戒,我將錯就錯,做出一副逛大街的模樣,東摸摸西摸摸,在賣場裡晃蕩,逐漸朝天王方向前進。麥可買了一些光碟之類的物品後,走到鐘錶櫃前,離我只有三、四米,而保鑣仍在門邊。麥可開口向店員說了什麼,很小聲,不懂英語的售貨小姐一臉緊張的表情。
機不可失,我簡直是衝了過去,與他並肩而立,說:「可以的話,我來翻譯吧。」他看了我一眼,和善的眼神似乎有一點困惑,但仍緩緩地說:「請問這裡有沒有螢光的G-Shock?我想看看。」透過口罩傳來的聲音細細尖尖,有點有氣無力。
我照本宣科翻譯完畢,售貨員拿出一只錶,麥可接過去握在手中端詳,我一看機會又來了,一面伸手半遮錶面擋光,一面說:「你看,亮亮的,有螢光。」我的手蓋在麥可露在衣袖外的手上,那裡的皮膚白皙得近乎透明。此舉大約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天王輕輕說了聲謝謝便轉身離去,走出賣場。在將近十三年後,麥可.傑克森遽然離世後的此刻,那如同被風捲起般飄走的背影是那麼不真實,卻又猶在眼前。
這條新聞我發了,卻是輕描淡寫,並未按當時兩大影劇報的作風,炒作成「獨家貼身採訪」,倒不是我變得比較不狗仔了,而是對工作已生倦意,覺得影劇記者生涯原是夢,不時自我質疑這些消費明星名流的花絮、八卦,除了茶餘飯後可以閒嗑牙以外,對我、對別人有什麼意義呢?那一回與天王的零距離接觸,與其說是善盡記者職責,不如說是自覺地在演一場戲:窗外眾目睽睽,我至少該扮出認真採訪的樣子吧。
而就在那之前不久,我到當時開播不久的台北愛樂電台採訪時,很不務正業的花了大半時間和電台台長大聊特聊在家聽古典樂做菜的心得,意外博得青睞,應邀主持起一個名叫《羅西尼的台灣廚房》的節目,每週末晚上在空中播音樂講美食,偷渡我對吃東西這件日常生活要事的想法和態度,為我日後成為所謂飲食作家埋下伏筆。
麥可離開台灣的三個多月後,我辭去報社的工作,結束並不輝煌的類狗仔記者生涯,旋即在《中國時報》的〈娛樂週報〉版撰寫與電台節目同步同名的專欄。雖說在前此一年多期間,我已陸續發表過幾篇食物散文,這個固定的報紙專欄卻更大力地推了我一把,讓我正式踏進彼時尚有點冷清的飲食寫作江湖,也促成我日後出版《羅西尼的音樂廚房》這本食書,至於這片江湖後來竟會發展成當今這般百家爭鳴、各顯神通的盛況,則當然是我始料未及的事。
/
往事歷歷,歸根究底,我是不是該感謝那隻「相愛相殺」的小老鼠?
沒有牠的橫衝直撞,可能就沒有後來變成飲食作家的我。(但是,在此衷心祈願,鼠輩,不論死活,都離我遠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