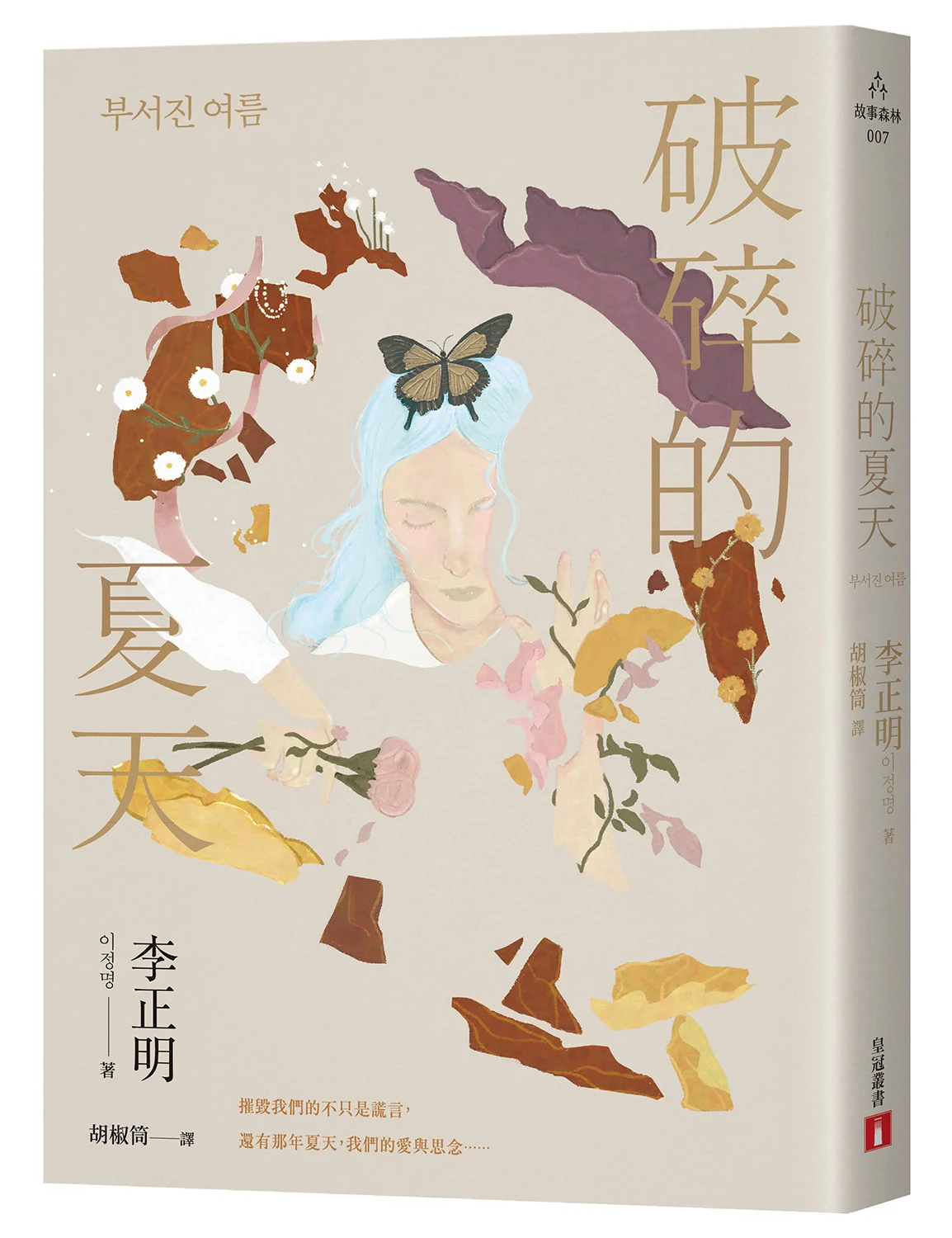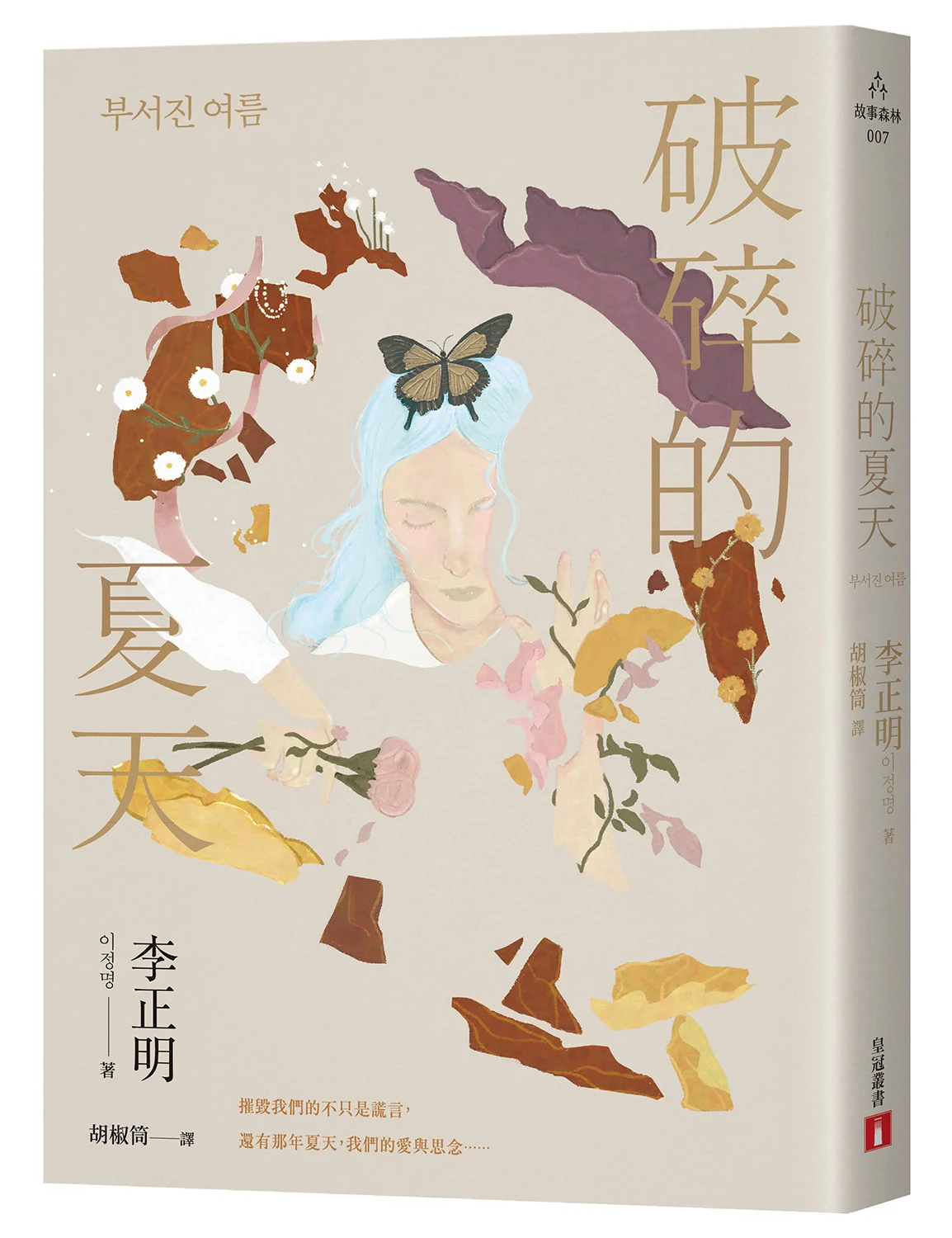內容試閱
四十四歲的第一個清晨,陽光悄然無聲地落在翰祖的眼皮上。翰祖拖著重若千斤的身體坐了起來,昨晚妻子為他蓋的毯子掉在了地上。妻子經常坐的椅子空著,可能她在酩酊大醉的自己睡著後回房睡覺了。
翰祖邁著懶洋洋的步子穿過院子,刺眼的陽光讓人睜不開眼。剛走進玄關,翰祖便察覺到了有別於以往的寂靜。電視沒開,也沒有播放音樂,更不要說妻子在廚房忙碌的腳步聲和茶杯的碰撞聲了。只是穿過院子而已,但陌生的感覺就像移動到了平行的世界一樣。難道妻子還沒起來?再不然是去買雞蛋或牛奶了?
「老婆!妳在哪裡?親愛的?」
家裡就像飯店一樣整潔,每個角落都一塵不染,翰祖隨手脫下的襪子和亂丟的外套也都被人清走了;廁所的鏡子擦得鋥亮,四四方方的天藍色毛巾整齊地疊放在置物架裡,就連廚房的洗碗槽也乾淨得不見一滴水;昨天用過的盤子和烤箱托盤也在櫥櫃裡閃閃發光。整個家就像出了趟遠門的主人剛精心打掃過似的。
翰祖開門走到院子裡,草坪上的積水浸濕了穿著拖鞋的腳踝。戶外的餐桌上也不見剩下的食物、空酒瓶和布滿污漬的桌布。桌子擦得乾乾淨淨。
「老婆!妳到底去哪裡了?真是的……」
三歲的拉布拉多犬羅斯科趴在臺階上觀察著他的眼色。十點二十分,早就過了早上餵飼料的時間。翰祖趕快取來飼料,羅斯科狼吞虎嚥地吃了起來。
「羅斯科!媽媽去哪裡了?嗯?我在問你,媽媽去哪兒了?」
羅斯科清空飼料碗,懶洋洋地伸了伸舌頭。翰祖依次查看了一樓的客廳、更衣室、客房和二樓的衛浴、臥房。他敲了敲妻子工作室的門,緩緩推開房門,但空無一人。一樓的機房、廚房一側的食材保管室和放置園藝工具的倉庫也都不見妻子的身影。翰祖走到車庫一看,妻子的車不見了,但地上沒有留下輪胎的痕跡。
恐懼席捲而來。雖然這可能是敏感體質誘發的草率推測,但某種確信始終無法從腦海中抹去。
妻子消失了。她不是暫時離家出走,更不可能馬上回來。翰祖無從得知妻子是離開他,還是拋棄他,又或者是從他身邊逃走了。不如報警?還是先去妻子經常去的地方看看?但她經常去的是哪裡呢?
翰祖下意識地拿起客廳的電話,但他不記得妻子的手機號碼。因為在他需要妻子的時候,妻子總是陪在他的身邊。妻子消失後,翰祖這才意識到自己對妻子一無所知,進而產生了絕望感。
過了半晌,翰祖這才想起了妻子的號碼。撥號音響起後,隨即傳來了清脆的電子音:
「您所撥的號碼暫時無法接聽。」
翰祖把電話摔在地毯上。雖然不知道妻子發生了什麼事,但恐懼和被置之不理的憤怒同時湧上了他的心頭。
翰祖思考了一下如果是妻子的話,會怎麼應對當下的狀況。妻子肯定會保持冷靜,就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一樣。她會先查看一遍家裡,然後給周遭的朋友打電話。但問題是,翰祖不知道妻子朋友的電話號碼,更不知道要打給誰。此時的翰祖根本沒有力氣出門尋找妻子。
因為宿醉,翰祖感到頭暈目眩、口乾舌燥。對他而言,妻子不在身邊就像幻肢痛一樣痛苦。他不知道妻子為什麼、去了哪裡?也不知道妻子為什麼選在自己的生日、最高拍賣價更新的日子?更不知道誰知道妻子的下落,以及她是否會回來、什麼時候回來、回來的時候自己是應該生氣,還是感激她?
下午,翰祖把羅斯科的狗鏈綁在腳踏車上,騎車去了經常和妻子散步的地方。翰祖心想,總不能一直坐在家裡等下去,回來的路上至少可以去妻子經常光顧的小店打探一下。書店兼唱片行、麵包店、小菜店和賣油漆、工具的五金行……
聽到店家們異口同聲地問:「今天怎麼一個人啊?」翰祖這才意識到在旁人眼中,單獨行動是很不自然的事。
「我們不是壞人,羅斯科,是不是?我們絕對不會遇到壞事的。」
翰祖一邊喃喃自語,一邊加快了腳步。他期待回到家時,妻子會像往常一樣迎接自己。羅斯科累壞了,垂著舌頭跟在翰祖身後。與期待相反,迎接他的只有寂靜與黑暗。汗水浸濕的襯衫緊貼在背上,翰祖也精疲力盡了。
翰祖走到畫室,餵羅斯科吃了飼料。即使一天沒吃東西,也不覺得餓,他只是覺得口乾舌燥。打開抽屜,映入眼簾的是剩有三分之一的威士忌酒瓶。翰祖倒滿酒杯,烈酒沿著食道火辣辣地流進胃裡,隨之全身就像通了電似的一陣酥麻。也許是因為烈酒上頭,突然某種想法從翰祖的腦海中一閃而過。
妻子有兩支手機,一支是自己的,另一支是翰祖的。她會幫埋首創作的翰祖接聽各種電話:策展人、評論家、記者和製作人,還有欣賞他作品的人、抗議不知道他在畫什麼的人、貸款廣告電話、房產仲介商、保險業務員和詐騙電話……
翰祖把自己關在畫室期間,妻子會處理各種日常瑣事和繁瑣的工作。從繳電費、通下水道、修剪花園、除草和搬家具等的家務事,到協調畫展日期、起草合約書、聯絡畫廊開會、安排媒體訪問、拍賣畫作和統計收益,甚至還要預定參加海外活動的機票和美食餐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