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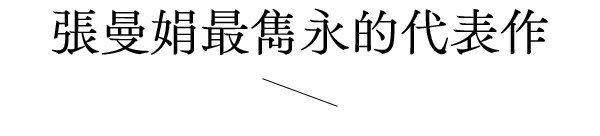


十七歲開始,她在報上執筆寫了一連串淺顯的文章,而如今,她決定寫一個離群海鳥千里尋家的兒童故事。專欄定名為「給小彤」,外甥小彤很乖,很聽話,但這些都沒有用,都阻止不了他的媽媽說走就走……一九八五年出版《海水正藍》,在華文世界奠定難以撼動的地位。而滄海桑田,張曼娟依然是一名擺渡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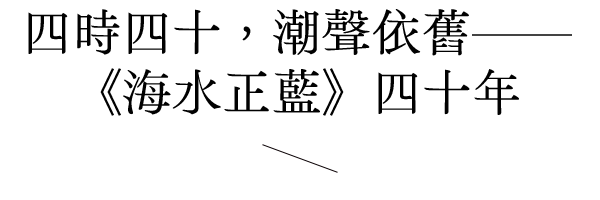
一九九○年,在《海水正藍》出版五年之後,中國時報舉辦了一個「四十年來影響台灣最大的書」讀者票選活動,最終有四十本著作上榜。《海水正藍》這本資歷最淺、作者最年輕的短篇小說集,竟然能與《汪洋中的一條船》、《異域》、《未央歌》、《冰點》、《天地一沙鷗》等重量級名著,並列前十名。沒有網路的年代,真的是讀者一票一票用郵寄的方式投出來的,我不知道一萬七千多張選票從哪裡來?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會將如此寶貴的一票投給我?我沒有歡欣鼓舞,而是原本就戒慎恐懼的心情,變得更加不安。 我盯著榜單,對自己說:「這只是幸運,沒什麼特別。如果四十年後還能寫作,還有讀者,那才夠特別。」 就這麼一年四時的寫下來了,就這麼安安靜靜的寫了四十年,當年曾經投票給我的讀者們,都已經是中年甚至老年人了。曾經的那些疑惑與不確定,歲月都給出了答案。 〈永恆的羽翼〉是這本書的開端,二十一歲的我將小說習作課的作業交給了張曉風老師,她批閱之後還給我,建議我修改投稿,看著作業上那行評語「有大作家的手筆」,我的心跳變得好快。於是,增刪潤飾,投稿到台中烏日鄉的《明道文藝》,參加第三屆「全國學生文學獎」徵文比賽,獲得了大專小說組首獎。從那以後,我的創作魂被點燃,成了一個可以為寫作廢寢忘食的上癮者,雖然我四處投寄的稿子不斷被退回,卻總有一個溫暖的地方接住我,那就是陳憲仁社長的《明道文藝》。陳社長細心的指導我小說的寫作規格,甚至幫我改正錯別字,收到每篇稿子,他都會回覆錄用書信,並對我的故事和文字表達肯定與鼓勵。如果沒有這位亦師亦友的貴人,我不可能成為作家。 〈永恆的羽翼〉也讓我體驗了小說的預示能力。故事裡的李父努力拉拔姊弟二人長大成人,甚至賣掉房子讓兒子、媳婦出國移民,然而,兒子背棄了承諾,捨棄父親不顧,李父只得依託女兒、女婿度過餘年。小說中的矛盾衝突,也就環繞著這個老人長照的主題展開。三十年後,當我成為一個獨力照顧者,擔負起老父母的長照,赫然驚覺,這一切早在我的心中演練過一回,而我的選擇也與當年的慕雲一樣,沒有遲疑和猶豫。 所謂命運,難道是我們自己書寫的嗎? 得到全國學生文學獎是大學畢業前夕的事,而後,我竟然接到了「皇冠出版社」平鑫濤先生的邀約,為《皇冠雜誌》撰寫一篇小說。即將進入碩士班就讀的那個暑假,我用鋼筆奮力在稿紙上,寫下一行一行深埋在心中的故事,有時候寫到痛哭流涕,把稿紙浸溼了,只能換一張稿紙重謄。就這樣,炎熱之夏,〈海水正藍〉這篇小說誕生了。 我的手骨本就軟綿無力,手腕韌帶過度使用而受傷,去跌打損傷師傅那裡貼了草藥,再把一層層的紗布包裹好。草藥遇熱融化,成為赭紅的殘漬,從白色紗布透出來,恰好是在手腕的位置,引起許多關注與猜測。「愛情這種東西啊,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妳還這麼年輕,千萬不要想不開。」「總有一天,會有一個好情人出現,愛妳一生一世。」 那時候並不知道,其實我命中註定的情人已經出現,「創作」永遠不會傷害我、背棄我,「創作」溫柔的一次次接住我,與我相伴一世。 《海水正藍》的出版,也是一場意外。出版社老闆在一位前輩作家的陪同下,帶著合約來到我面前。還在念研究所的我,對於坊間某些出版社,未經同意便盜版我的文章,感到束手無策。出版社老闆告訴我,只要與他們簽約,以後他們就會保護我的權益,加上前輩的軟硬兼施,我終於在合約書上簽字。回家一見到媽媽便哭了起來:「我已經簽約了。」原本暗自憧憬在三十歲的而立之年,才出版第一本書的我,竟然在二十四歲就出版了《海水正藍》這部短篇小說集。後來,這本書就瘋狂暢銷了。 名不見經傳的校園作者異軍突起,隨之而來的是文學界與評論界的各種批判謾罵,連幫我寫推薦序的曉風老師也被波及。我體驗到的是惡意與嘲諷,懷著愧疚的罪惡感和羞辱感,知道自己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徹底放棄,當作什麼事也沒發生;二是繼續堅持,迎接不可知的挑戰。是什麼讓我選擇了第二條路呢?除了血液裡流淌的那一點倔強,就是一直支撐著我的讀者了。 我的讀者是一群溫柔寬厚的人,他們不只是閱讀著我的故事或經歷,也閱讀著我的心。所以,我不容許自己不真誠;也不容許自己賣弄;更不容許自己有一絲驕妄,否則便對不起我的讀者知己。四十年來,我的初代讀者將《海水正藍》傳給了二代、三代;老師將我的書介紹給學生;孫子拿著阿嬤的藏書給我簽名;小女孩因為爸爸視我為偶像而來小學堂……我的讀者有些成為我的學生,有些成為好友,建立起宛如家人般的關係。他們喚我「曼娟老師」,並不是因為上過我的課,而是因為讀過我的書。 我感激這樣的相遇,感激改變了我的一生的《海水正藍》。 在《海水正藍》出版十年後,命運的轉折,讓版權回到「皇冠出版社」,而後,我的大部分作品都在皇冠出版。四十年並不是一眨眼,四十年發生了許多事,人生海海,我仍能聽見規律的潮聲,亙古的迴盪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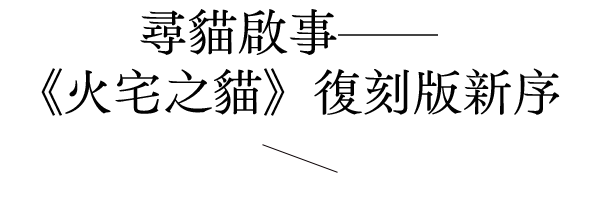
某天清晨,我被住家附近的火災所驚醒,烈火熊熊從舊式民房的二樓鐵皮屋焚燒起來,瞬間濃煙密布,天地變色。消防車與救護車鳴笛趕來,消防隊員拉起水管朝火燄噴灌水柱,火舌充滿能量的從窗戶裡舔出來。被波及的鄰居爬上隔壁的屋頂求援,驚險萬狀,令人焦慮不安。 「三界無安,猶如火宅。」我想到佛經中的這兩句話。有著愛、恨、貪、嗔、癡的我們,都曾身處火宅,受焚燒之苦。有人能矯健輕盈的跳脫而出;有人卻只能身心俱灰了。 《火宅之貓》最初是我短居香港時,應邀為《明報》撰寫的幾則短篇故事,後來發展為長篇小說,並在《自由時報》連載。那個年代,許多人的精神食糧是報紙副刊,在報上追著看小說連載,與現今追劇的心情差不多。我與副刊主編許悔之相約在咖啡館,慎重其事的討論小說走向,人物塑造與故事氛圍,能在報上連載長篇小說,是我創作生涯的一樁盛事。 一位謎樣的美麗女子亞咪,與心理醫生齊大夫之間的愛情故事。亞咪看似脆弱卻才華橫溢。因為過去不可知的創傷,她變得內縮,無安全感,卻對齊大夫產生莫大的吸引力。不溫不火的齊大夫為她瘋狂,想要保護她,他們終於成為夫妻。亞咪的夢想就是繪畫與創作,她不做家事,晝伏夜不出,全然沒有生活能力,齊大夫照顧她的生活起居,甘之如飴,就像嬌養著一朵玫瑰。直到某一天,亞咪憑藉著漫畫創作《貓的天堂》而爆紅,各式各樣擬人化的貓女角色,我行我素、自戀、標新立異、敏銳、多情,彷彿喚醒了女人內在的蠢蠢欲動,引爆全城。亞咪紅了,帶來無限商機,她被眾人簇擁,再也不是齊大夫的妻子。齊大夫仍然守著舊房子的小診所,聆聽病患們囈語的異世界。 曾經,亞咪是「齊太太」,如今,齊大夫是「亞咪的丈夫」。齊大夫自嘲的想:「『美麗又有才華的超級名女人的丈夫』,是我這一生擁有最長的,也是最顯赫的頭銜。」他被沮喪與猜疑所籠罩。亞咪則是既自戀又自卑,帶著隨時可能被拋棄的創傷與陰影,被伴隨盛名而來的患得患失所纏繞。往日的謎團像撥不開的濃霧,困住了他們,看不清彼此。回想起未成名時單純的快樂,炙烈的情愛,對比起現今的疏離,他們都不確定,是否還相愛?其實,愛情就是最懸疑的推理啊,多少曾經熱戀的人們,在解謎的路上一再失誤,最終失去了彼此。 感謝許悔之曾為此書撰寫推薦序:「張曼娟這部長篇小說描寫了情愛的多樣化(異性戀、同性戀、雙性戀),展現了心理分析式的奇譎魅力,探究了流行文化背後的集體潛意識,可謂豐厚駁雜了,尤其她對女性情愛自覺的詮釋,更駸駸乎為大眾小說提供了不同的可能。」我知道自己是把這個故事當成一齣戲劇在寫的,那些角色都很生動立體。 有幾件值得記下來的事:在《火宅之貓》之前,我是爬格子的手寫作家,因為這部小說的連載,我坐在電腦前一邊創作一邊練習打字,十餘萬字的小說截稿,我的打字技巧已經很熟練了。為了創作這個故事,我蒐集了許多資料,更向精神科醫師作家王浩威請教了許多細節,感謝他始終不厭其煩的為我解答說明。那時的我不知道心理諮商師與精神科醫師的差異,但因為這本來就是個虛構的故事,就保留了齊大夫「心理醫生」的這個身分。一九九七年寫作時沒有養貓,也沒想過有一天會養貓,我借用了公貓結紮的情節,來暗喻齊大夫被亞咪情感閹割。二十年後我領養兩隻貓,現在的我已經是貓咪結紮的擁護者,也不可能在自己被監視的情況下放貓咪去「逃生」。 我的貓絕不可以離開我(吶喊)。 但是,逃出火宅的本領,還是得向貓咪學習。身陷火宅般的苦惱焦煩之中,我們都得像貓咪一樣輕巧飛躍,才能獲得新生。亞咪失蹤了,她去了哪兒?還會不會回來?請開始閱讀這個故事,就像翻閱一張又一張尋貓啟事,展開一場奇妙的旅程。 二○二五年養貓人謹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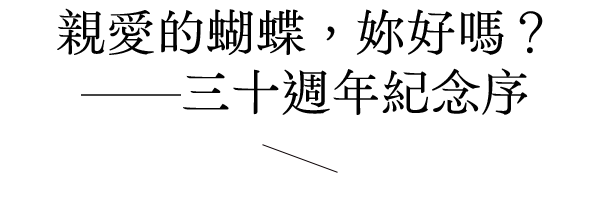
親愛的蝴蝶: 三十年沒見,妳還好嗎?現在的妳變成了什麼樣的人?身邊有人陪伴嗎?幸運的是,此刻的我還能寫信給妳,再過三十年就心有餘而力不足了。 《我的男人是爬蟲類》是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我大膽的運用了自身的形象與生活,作為基底,塑造出了妳。又用了單向的書信體,以一種綿長的傾訴方式述說故事,描繪心情的跌宕起伏,宛如一部「私小說」。總有人問:「蝴蝶就是妳吧?」也忍不住想知道更多,於是又問:「大蟲是你理想中的伴侶?還是已經在一起的情人?」小說是以開放式結尾告終,在經歷許多考驗之後,妳與大蟲依然是彼此生命中的渴求,你們願意用一條橋作為連結,「從我這裡,到你那裡。」看起來你們都義無反顧的選擇了與對方緊緊相繫。 相愛的人,都會這樣選擇的吧。 然而,此時此刻的你們,還能期待著一起去旅行,在京都感受侘寂之美?旅途與日常之中,還會有相視而笑的時刻?舉起手機捕捉景物時,會不知不覺拍下身邊人?哪怕對方只是蹲下身子逗弄貓咪,或是穿著一件半舊毛線外套,都覺得這個瞬間十分獨特珍貴?你們會期待對方滿足自己的心靈需求?還是他只要做自己就好?妳有能力自給自足? 又或者,你們已經分手了,各自展開新的人生? 這十九封信只有最後一封寄出,其餘都沒有寄。沒有寄出的信,其實是妳仍在探索的、不確定的情感與自我吧。我們都是在真正愛著一個人的時候,才會感到火燄燃燒般的思念與渴求,渴求著愛與被愛;渴求著被瞭解;渴求著內心被充滿;渴求著氾濫的給予;渴求著全然被接納。 我們在愛中誕生,重新再活一次。 像是妳的那幾位好友,都在愛中實踐了自我,活出另一種樣態。卓羚是個早熟的、敢愛敢恨的女子,她像狩獵一樣的愛上一個理想男人。這男人樣樣達標,可惜已婚。卓羚無意介入男人家庭,卻已無可避免的介入,她選擇了「見好就收」,懷著男人的孩子遠走海外。葛哥在學校玩社團時就暗戀春花,卻因為名花有主,只能壓抑心中情感,選擇當一個守護者,謹守朋友界線。春花則是全然投入於愛情,哪怕愛人從沒明確允諾未來;哪怕愛人常常對愛情不忠,但春花相信付出的青春與深情,總能守得雲開見月明。事實證明緊抱著殘缺的愛,只是狠狠傷害自己。在同婚還沒通過,同志之愛尚且隱密的三十年前,妳遇到了那個叫東山的男子,他與眾不同的溫文體貼,孤獨卻又善良,使妳忍不住向他走去,並沒有異性的情愫,卻是穩妥的倚靠。直到妳知曉了他的祕密,也感受他失去摯愛的傷痛。 妳和妳的朋友們也都依然安好嗎?算一算,卓羚的孩子都三十而立了呢。曾經,在愛中彷彿永遠不會老的你們,看著彼此的容顏,都是歲月的痕跡,無法遮掩,也不能逃避。 走過大半生的妳,如何評價那個男人大蟲呢?妳是完全蛻變的蝴蝶,他是有時變色的爬蟲類。大蟲有過一次婚姻,因為與一個善解人意的女子作伴的感覺很美好,而後某些情境改變,婚姻陷入低谷,於是分居,準備離婚。妳是在這樣的空窗期走入他的生命。妳的純粹與溫柔敲擊著他的孤獨之心,他的擅長等待與體貼使妳的心弦緊繃。那時的妳一心一意的向他走去了,哪怕心底明白對他來說,你可能也只是另一個善解人意的女子。這樣也就夠了,人生之中能夠遇到這樣的時刻,鼓起勇氣的迎向前去。 認識過愛的繁花似錦,心中永不荒蕪。 親愛的蝴蝶,妳是這樣想的吧?我也是這樣想的。許多覺得自己與蝴蝶如此相似的,披著蝶衣的女子,也和我們的想法一樣吧。來到這個人世,好好愛過一場,並被自己在愛中的模樣所魅惑,讚歎著:真美啊,無所畏懼的,深情一往的自己。 祝福 自在蛻變 曼娟 於二○二五/秋分剛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