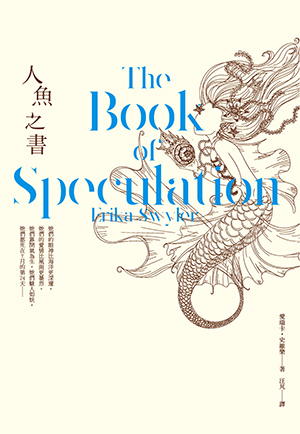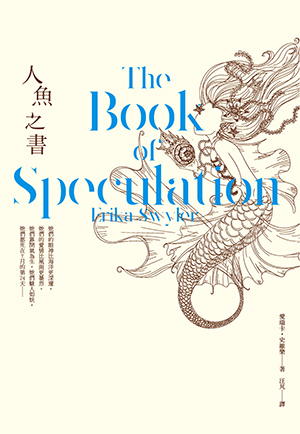1 六月二十日
海峽裡以六月來說算冰冷刺骨,但一下海,我便如魚得水,雙腳蜷起,牢抓一顆顆覆滿海藻的石頭,彷彿天生自然。浮標錨的鐵鍊使我慢下來,但法蘭克依然搖著船槳,維持相同速度。我一直走到海水及胸,淹上脖子為止。把頭浸入水中之前,我吐光胸腔的空氣,然後吸氣,正如母親在一個七月底的溫暖早晨教我的,正如我教妹妹的。
閉氣的訣竅就是讓自己感覺口渴。
「一口把氣用力吐掉。」母親在我耳邊輕聲說。在淺淺的水中,她濃密的黑髮如無數河流,在我倆四周冉冉流動。那年我五歲,她壓著我的肚子,壓得肌肉陷入體內,肚臍幾乎碰到脊椎。她使勁壓,我感覺尖尖的指甲刺著。「現在吸氣,要快,快、快、快,把肋骨張開,把思緒張開。」母親吸氣,肋骨擴大,鳥兒般的纖細骨骼一根根張開,直到肚腹渾圓如桶。她的泳衣在海中如一道明豔白光,使我瞇起眼看。她伸出一根手指拍拍我的胸骨,噠,噠,噠。「賽蒙,你把氣往上吸了,把氣往上吸就會溺水,往上吸就壓縮了肚子的空間。」一個輕觸,一抹淺笑。母親說,要想像自己很渴,乾涸空蕩,然後把空氣喝進去,張開肋骨,大口、深深地喝。待我的肚子鼓成一只圓胖的鼓,她低聲說:「很好,很好。現在,我們潛下去吧。」
現在,我潛下去。柔和的光線從法蘭克小艇的陰影四周流瀉而下。偶爾我會聽見母親的聲音在水中漂蕩,有時也瞥見她,在層層海草後,黑髮混雜在巨藻之間。
我吐出的空氣散成一片細霧,覆著肌膚。
我的母親波黎娜是馬戲團和流動遊藝團的表演藝人、占卜師、魔術師助手,也是一尾人魚,因為她靠閉氣謀生。她教我像魚兒般游泳。她令我父親微笑。她經常鬧失蹤,不是辭了工作,就是同時兼兩、三份差事。她有時在外頭旅館過夜,只為了嘗嘗睡在其他床上的滋味,我的父親丹尼爾是個機械操作員,也是她倦鳥的歸巢,他總守候家中,微笑著,等她回家,喚他一聲:親愛的。
賽蒙,親愛的。她也這麼喚我。
她走進海裡那年我七歲。我試圖遺忘那天,但那已成為我對她最鍾愛的回憶。她那天早上離開我們前做了早餐,全熟的水煮蛋,得在盤子邊緣敲破,用指甲剝,碎蛋殼會卡進指甲縫裡。我幫妹妹剝蛋殼,再替她切成方便幼兒抓著吃的小塊。蛋配上乾乾的烤麵包片,以及柳橙汁。在夏日清晨時分,暗影看起來更暗,人的臉看起來更白皙,凹陷處更有稜有角;波黎娜那天早晨極美,宛若一隻天鵝,與周遭格格不入。爸爸去工廠上班了,她和我們獨處,我替艾諾拉切蛋,她看著,點頭。
「你是好哥哥,賽蒙,你要好好照顧艾諾拉,以後她會想從你身邊逃開,你要答應我別讓她逃走。」
「好。」
「你真是個好孩子,對不對,我從沒想到。我根本沒想到會有你。」
咕咕鐘的鐘擺滴答敲。母親用腳跟輕敲油地氈,不打斷這安靜的時光。艾諾拉吃得滿身蛋和麵包屑,我邊吃東西邊維持妹妹身上乾淨,分身乏術。
一陣子後,母親站起身,將身上的黃色夏裙整平。「賽蒙,之後見。艾諾拉,再見。」
她親吻艾諾拉的臉頰,並親了我的頭。她揮手道別,帶著微笑離去。我以為她出門上工。我怎曉得那道別真是永別?艱難的意念埋藏在淺白的話語中。那天早上她看著我,知道我會照顧艾諾拉,她知道我們沒辦法跟著她,那是她唯一能走的時候。
不久後,當我和愛麗思.麥柯沃伊在她家客廳地毯上賽車時,母親便在海灣裡投水自盡。
我潛入水中,胸膛往前推,腳趾緊抓,走了幾步,放下一個浮標錨,錨發出噹啷悶響。我望向小艇的影子;法蘭克著急了,船槳在水面上拍打。把水吸進體內會是什麼感覺呢?我想像著母親扭曲的面容,繼續往前走,走到放另一個錨的定點,這才將肺裡的空氣吐盡,往海岸的方向移動,但腳仍踩著地──我和艾諾拉從前總愛這麼玩。一直到用腳走難以維持平衡,我才游起來,雙手規律划動,像法蘭克的船一樣,劃開海灣的海水。來到水深只到頭頂的地方時,我再度踩到地面。接下來的動作是為了法蘭克。
「慢慢來,賽蒙,」母親告訴我,「要把眼睛張開,會刺痛,出水比下水的時候還痛,但還是要睜開眼,不要眨。」鹽使眼睛灼痛,但她從未眨眼,在水裡不眨,眼睛重新接觸到空氣時也不眨,仿若一尊會動的雕像。「不要吸氣,就算鼻子已經離開水面了也一樣,太快呼吸會喝到滿嘴鹽水,你要等待,」她說出這詞,許諾般斬釘截鐵,「要等到嘴巴離開水面,然後用鼻子呼吸,才不會讓人覺得你看起來很累,絕對不能讓人覺得累。然後你就微笑。」她生得小嘴薄唇,笑起來卻如海般寬廣。她也教我該怎麼鞠躬致意:雙臂揚起,胸膛向前,如一隻起飛的鶴。「觀眾喜歡看很矮小和很高大的人,不要像演員那樣彎腰,那樣身體就截短了,要讓他們覺得你比實際身高還高,」她抬起雙臂,對我嫣然一笑,「而且你會長很高的,賽蒙。」她朝著看不見的觀眾點頭,沉穩有力。「還要彬彬有禮,永遠要彬彬有禮。」
我不鞠躬,不為法蘭克鞠躬。我上次鞠躬是教艾諾拉的時候,當時我們的眼睛給鹽刺得紅腫,看起來彷彿剛打過架。但我仍露出微笑,並以鼻子深吸一口氣,讓肋骨鼓起,肚腹灌滿空氣。
「還以為我得下去找你了。」法蘭克嚷道。
「我潛了多久?」
他瞟了他那皮帶龜裂的手錶,呼一口氣。「九分鐘啊。」
「我媽可以潛十一分鐘。」我甩掉頭髮上的水,手在耳朵上拍兩下,讓水流出來。
「我一直搞不懂她怎麼做到的。」法蘭克嘟囔著,把船槳從槳鎖上解開,扔進小艇,槳發出哐啷聲。我倆都沒說出口的問題是:一個善於閉氣的人得花多久時間才能把自己溺死?
我套上襯衫,襯衫沾滿了沙,這是海邊生活的必然結果,沙子會出現在頭髮上、腳指甲縫裡、床單上,無所不在。
法蘭克在我後頭上岸,拖著船,氣喘吁吁。
「你應該讓我幫你搬。」
他在我背上拍了一把。「我要不時逼自己一下,才不會老啊。」
我爬階梯走上去,沿途避開那些毒野葛,野葛在欄杆、懸崖上蔓生一片──沒人拔掉這些野葛;任何能在這沙地上落地生根的東西,無論有什麼害處,都值得留下。我穿越海邊草叢,走向我家。我家和許多納波沙的房子一樣,是不折不扣的殖民地時期建築,建於十八世紀末,先前大門旁還掛著一塊歷史學會發的牌匾,幾年前才給東北大風吹落。堤摩西.瓦貝希宅邸。白漆斑駁,四道窗戶歪斜失修,臺階傾斜,這屋子的年久失修和經費困窘一覽無遺。
在褪色的綠色前臺階上(之後得處理一下),打開的紗門夾著一個包裹。送貨員老讓門開著,我已經留過無數次紙條;我最不需要的就是重裝這道從落成以來始終歪斜的門。我沒訂購什麼,也想不到有誰會寄東西來,艾諾拉居無定所,頂多只寄明信片,還經常寄空白的來。
這包裹十分笨重,上頭地址是蜘蛛腿似的、纖長歪扭的老人字跡──我十分熟悉,因為圖書館的讀者普遍年長。說到這,我得記得問詹妮絲能不能從圖書館預算擠點錢來,如果我能把堤岸修補一下,情況或許沒那麼糟,不一定得加薪,單次的獎金也行,獎勵我多年以來的服務。包裹的寄件人我不認識,是一位住愛荷華州的邱奇瓦瑞先生。我將書桌上的一疊紙拿開,都是一些馬戲團和遊藝團的報導,我這些年來為了解妹妹生活而蒐集的。
箱子裡放著一大本書,包裝十分仔細。雖然還沒打開,光從霉味和微嗆的氣息已能聞出老舊的紙張、木頭、皮革和黏膠。書外面包著薄棉紙和白報紙,拆開後,映入眼簾的是一本深色的皮革精裝書,上頭畫滿原先應該十分細緻精美的漩渦飾紋,可惜泡了水。我體內竄起幾絲驚慌的感覺,這本書十分古老,不該徒手碰觸,但眼見書已經毀損,我就向那觸摸古物的無聲興奮屈服了。未泡水的書頁邊緣柔軟而粗糙。圖書館的藏書量驚人,我得以涉獵歸檔和修……
more